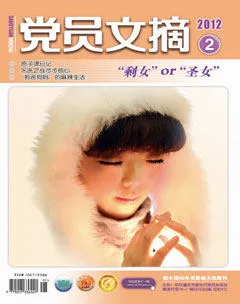云端的刀鋒之舞
姚憶江 徐秉君
低空盤旋,接著垂直躍升,然后低空大速度通場……最后一個動作是空中應急放油,航空煤油在大氣中被迅速分解,留下一條銀色的航跡……20分鐘后,飛機劃出一條輕巧的小航線,平穩降落在跑道上。
“報告首長:國家重點工程新型首架樣機試飛完畢,各項性能指標完全達到設計要求,請指示。”首席試飛員李國恩用洪亮的聲音報告。
新型樣機的總設計師早已忍不住沖上前來,流著淚,緊緊抱住了李國恩。
“戰機不僅是設計出來的,戰機更是飛出來的!”對于試飛員來說,在試飛生涯中能當上一次“首席”就已經十分難得,而李國恩則是“中國造”5型飛機的首席試飛員。
每一次飛行
都是一種快樂體驗
試飛員總是喜新厭舊的人。“就像賽車手喜歡F1一樣,試飛員都非常希望能駕駛性能更先進的飛機。“李國恩這樣介紹他對新飛機的感覺。
一款戰機,從樣機到最后裝備部隊,它的成熟往往需要十余年甚至更長時間。在這些不為人知的年月里發生了什么?試飛員的答案就是:戰機是研制人員智慧的結晶,也是試飛員“飛出來”的。
不過,和新飛機每一次親密接觸并不像李國恩的語氣那樣輕松。每一次臨界試驗,每一次極限挑戰,每一次重大險情……都仿佛是在死神注視下起舞。所以,每次試飛,李國恩從來不跟老婆孩子打招呼,他不想把緊張傳遞給家人。在家人面前,李國恩最自豪的事情,就是指著電視畫面里或者天上的飛機說,“這些飛機是我第一個飛出來的”。
飛機是新的,技術是新的,“新”意味著未知,把未知變成已知,就是試飛員的活計。當然,這活計需要相當的勇氣和技藝。這或許是李國恩當試飛員的原動力,“就像一個小孩玩泥巴一樣,喜歡玩,就會琢磨著怎么把它玩得好”。
1997年,一心想飛中國第三代戰機的李國恩,得知空軍作戰部隊要選拔一批技術條件好的優秀飛行員充實到試飛部隊,他立即報名,并有幸入選。
試飛,說白了就是要和新機型各種缺陷斗,而且還得贏。在14年的試飛生涯中,李國恩經歷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險情,但他對此輕描淡寫:“因為我追求和崇尚‘快樂飛行,所以每一次飛行都是一種快樂體驗,其中也包括戰勝風險的體驗。”
有時候,李國恩會想起剛飛行的日子。
1984年,李國恩在空軍某飛行學校學習。在訓練中,李國恩發現自己對汽油味過于敏感,并時常有嘔吐現象。克服特殊氣味影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在航醫的指導下開始了強化訓練,這就意味著在同等條件下,他必須付出超過別人數倍的努力。
李國恩終于闖過了地面訓練這一關,而真正的考驗卻在空中。
生死關頭的抉擇
熟悉航空的人都知道,“失速尾旋”、“空中停車”、“最大過載”是國際飛行界劃為死亡禁區的專業名詞:世界上失事的作戰飛機41%由尾旋導致:空中停車指飛行中飛機因發動機發生故障停車而失去動力:最大過載指飛行設計上能承受的最大載荷,該試飛項目極易導致飛機在空中解體。
一次,李國恩在西北某空軍基地執行科研試飛任務。飛機加滿了油,還加掛了3只副油箱和各種外掛武器裝備滿載起飛。
飛機在加力狀態下幾秒鐘就達到離陸速度,正當李國恩準備拉桿升空時,突然發現飛機出現右偏。此時,飛機的滑跑距離已經超過跑道的3/4,如果中斷起飛,飛機會因陡然剎車失控掉進機場旁的溝里。
在所有的飛行中,起飛和著陸階段情況處置余地最小,危險性最大。李國恩果斷決定繼續起飛。
飛機剛離陸,突然出現10~15度的右側偏,處理稍有不慎,試飛員連跳傘的機會都沒有。不容多想,李國恩迅即進行桿舵一致修正,同時保持飛機小角度右偏上升。
地面指揮員發現飛機狀態不正常,問道:“右發加力沒接通吧?”
“是的。”李國恩邊處理情況邊回答。
“保持好狀態。”
“明白。”
李國恩立即收起落架,同時將右發油門推到最大位置。當飛機爬升到100米左右高度時,右發動機突然“嘭”的一聲發出強烈爆音,飛機劇烈振動起來。
“右發停車!”盡管李國恩多次成功地處置過空中停車等險情,但在起飛過程中遭遇這種險情還是第一次。反應和處置的時間僅有幾秒鐘,稍微遲疑和一絲操作失誤就會導致災難性后果。
他兩次啟動右發動機點火開關,依然沒有成功。這就意味著,他必須要憑借一臺發動機在飛機滿載的狀態下返場著陸。
為確保新機絕對安全,李國恩決定投掉副油箱返場著陸。可是,這時飛機下正是幾家工廠和一片居民區,他立即改變空投方向,尋找無人地帶。
空中多停留一秒,就多一分危險。李國恩選擇在山脊無人地帶投掉副油箱后,飛機的重量仍然遠遠超過允許著陸的最大重量,右側發動機附件頻頻告警,沒有時間滯留在空中耗油減重了,必須保住新型戰機、新型發動機和各項飛行數據,以便事后查明導致故障的原因。
15點14分,李國恩在右發停車、極限超載的復雜情況下,駕機單發安全著陸在機場上。這時右發有關附件全部告警,發動機轉數及溫度旋即歸零,好險!
讓試飛助力
“跨越式發展之路”
首席試飛員是“王牌中的王牌”。面對不確定風險,良好的心理素質是試飛員必備的條件,同時還要具備良好的飛行技術、身體素質,要有強烈的創新意識。
近幾年,李國恩先后幾次出國進行學習交流,感到西方發達國家試飛機構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試飛員參與到飛機從設計到試飛的全過程。
“過去,中國試飛員大都是為工程試驗取得試驗數據。而俄羅斯試飛員與設計師、工程師有著通暢的溝通渠道,他們能夠很好地溝通交流,及時解決飛機試飛中的問題。美國波音公司和法國空客公司的一些高管都曾經是參與飛機設計的資深試飛員出身,使飛機的一些問題在早期設計中就可以得到解決。”
“要設計一個型號的飛機,試飛員必須通過自己的體驗,找出這種飛機的缺陷,要飛出這個型號飛機的極限。”在李國恩看來,“試飛就是在磨脾氣,再大的風險不過是一種體驗。”盡管面對的是科研院所的權威專家,還承受著科研進度的巨大壓力,但李國恩仍大膽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議。
“現在我們用幾十年的時間走人家發達國家幾百年走的路,國外全新的先進試飛理念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工程設計人員盡管能設計完美的飛機,但未必完全了解飛行員的駕駛習慣和感受,所以試飛員早期介入飛機設計,不僅可以使飛機設計更合理、更人性化、更便于操作,還可以盡早修正或彌補飛機設計缺陷,從整體上縮短飛機研制周期。
試飛,承載著更高的科技含量和更重的責任。話雖簡單,一個新機型要經過幾百架次試飛,如研究性試飛、調整性試飛、設計定型性試飛、定型性試飛、批生產試飛、轉場試飛以及戰術試飛。“比如中國自產的發動機,盡管有這樣那樣的毛病,但它是需要我們呵護的‘親兒子。”李國恩說。
如今,試飛一直處在航空工業的前沿,它與設計和制造并列為航空工業的三大支柱,是航空工業價值鏈中的重要一環,也是航空工業的核心能力之一。“我們必須要走跨越式的發展之路。我現在45歲,正是經驗豐富的時期,經過特許,還可以飛到50歲,能看到更多的新型戰機飛向戰場。”李國恩期盼著。
(邱寶珊薦自2011年12月15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