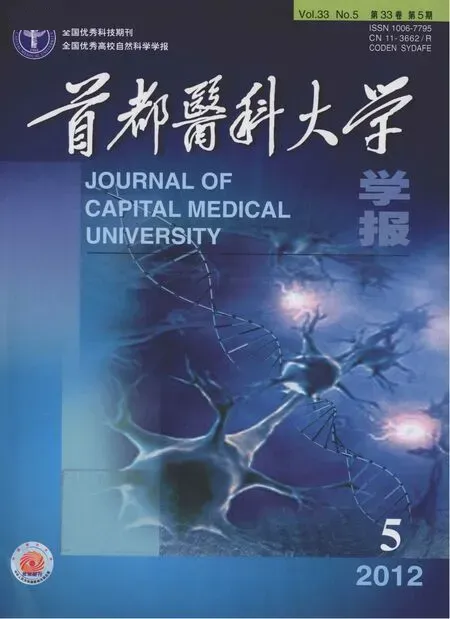細胞命運的逆轉:體細胞核移植與誘導多能干細胞——201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簡介
汪 璇 王曉民
(首都醫科大學神經生物學系,教育部神經變性病重點實驗室,北京腦重大疾病研究院,北京 100069)
2012年10月8日,位于瑞典卡羅林斯卡研究院的諾貝爾獎委員會宣布將201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共同授予John B.Gurdon(約翰·伯特蘭·戈登)和Shinya Yamanaka(山中伸彌)兩位科學家,以表彰他們在“成熟細胞可重編程而具有多能性”方面的重大發現。評委們認為,這兩位科學家發現成熟分化的細胞可以重新編寫發育程序,逆轉回歸成為能夠發育成機體各種組織的未成熟細胞。這一使細胞命運發生逆轉的發現顛覆了傳統意義上對于細胞或生物體發育程序的固有觀念。
盡管John B.Gurdon和Shinya Yamanaka兩位科學家在接到獲獎電話通知時都表現出異常驚訝和興奮的情緒,但他們的獲獎其實早有端倪。2009年,兩位科學家就曾分享有“美國諾貝爾獎”之稱的Albert Lasker基礎醫學獎;一些科學家也曾預言他們是近幾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最熱門的人選。
1 獲獎者簡介
1.1 John B.Gurdon
John B.Gurdon(圖1),英國發育生物學家,1933年10月2日出生在英國薩里郡韋弗利地區一個稱作Dippenhall的小村莊。1960年Gurdon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隨后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從事博士后研究。1962年他返回英國,就職于牛津大學動物學系,直至1972年進入英國劍橋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及后來的動物學系工作;曾任劍橋麥格達倫學院院長。1989年他參與創辦旨在資助細胞生物學和癌癥研究的劍橋(后成為英國)維康信托(Wellcom Trust)研究所,并任主席至2001年。2004年該研究所更名為Gurdon研究所;目前79歲的Gurdon仍工作于Gurdon研究所。1995年Gurdon曾被英國皇室授予爵位,因此他的名字也常寫成Sir John B.Gurdon。

圖1 John B.Gurdon(引自諾貝爾獎官方網站)
青少年時期的Gurdon曾在伊頓學院讀書,那時他的生物學成績很差,至今他仍可清晰地記得當時老師對他“成為一名科學家的想法非常荒謬”的評語,以至于Gurdon畢業后沒能直接步入科學的殿堂,而選擇了英國古典文學作為他的專業。但Gurdon并沒有因此放棄他的夢想,在牛津大學基督學院就讀時他獲準轉念動物學。1962年,Gurdon發表了關于體細胞核移植的重要論文[1],證實成熟體細胞的基因組仍攜帶向正常生物體發育所需的全部信息,從而開啟了人類對于細胞發育程序和命運逆轉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這項突破性的研究始于1958年,那時的Gurdon還僅僅是一名在牛津大學攻讀學位的博士生,他大膽挑戰“成熟細胞不可逆轉發育命運”的理論,設想成熟體細胞的細胞核仍具有重啟細胞發育的多能性。這個現在逐漸被公眾接受、并早已被寫進教科書的理論,在當時卻受到了來自包括權威科學家在內的多數人的強烈質疑。幾位發育學領域的權威得出了與Gurdon相反的結論,這給懷疑者們更加充分的理由,他們認為,相對于學界大師的實驗結果而言,一個研究生的“謬論”不值一提,他的數據一定是錯誤的。回憶起當年穿著隨意的毛衫,匆忙從實驗室趕赴面對全世界媒體的情景,Gurdon爵士在諾貝爾獎頒獎后的電話采訪中不無感慨道:“這就是科學研究的規律,一些新奇的發現總是需要先被沉淀下來,經過長期的論證再決定它們是否正確”。今年諾貝爾獎的頒布距離1962年Gurdon發表的那篇文章已長達50年之久。
1.2 Shinya Yamanaka
Shinya Yamanaka(圖2),日本醫學家,1962年9月4日出生于日本大阪府東大阪市。1987年,Yamanaka在神戶大學獲得醫學學位,開始在國立大阪醫院做整形外科實習醫生;但由于覺得自己缺乏成為一名外科醫生的天才,最終決定轉做基礎研究。1993年在大阪市立大學醫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后,Yamanaka于1993~1996年在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Gladstone心血管疾病研究所從事博士后工作,隨后就職于大阪市立大學醫學院及日本奈良科技研究院。目前是日本京都大學誘導多能干細胞研究和應用中心(Center for iPS Cel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Ci-RA)主任、Gladstone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國際干細胞聯合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tem Cell Research,ISSCR)的現任理事長。

圖2 Shinya Yamanaka(引自諾貝爾獎官方網站)
Yamanaka現年50歲,他出生的時間剛好是在Gurdon發表重要文獻的同一年(1962年)。因此,獲獎后的Yamanaka在提及這一時間上的巧合時,感到能與他敬重的Gurdon爵士一起分享201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是無比榮耀的事情。他認為,當初對于誘導多能干細胞的探索研究正是基于50年前Gurdon的實驗和理論之上。如果沒有Gurdon關于“成熟細胞遺傳物質具有多能性”的論述,也就不存在Yamanaka后來對于何種因子能夠決定細胞重編程從而逆轉發育過程的熱衷篩選。2006年,Yamanaka及其合作者經過了“接力式”的漫長尋找后,最終應用4種轉錄因子逆轉了細胞發育的進程,使成熟體細胞重新編程變為具有多能性的未成熟細胞,這一發現隨即被認為是發育研究的重大突破,這篇2006年發表在Cell上的論文[2]至今已被引用6000余次。憑此項成就及后來的研究,Yamanaka近年來獲得許多科學獎項和榮譽,包括與Gurdon分享的Albert Lasker基礎醫學獎(2009);Wolf醫學獎(2011);千年科技獎(2012);McEwen創新獎(2011);Gairdner國際獎(2009);邵逸夫獎(2008);Robert Koch獎(2008)等。2012年,Yamanaka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雖然科學認識上的巨大突破尚不能帶來既得的臨床應用價值,但以外科醫生開始職業生涯的Yamanaka教授始終認為自己肩負著醫生救治病患的天職。他在諾貝爾獎頒獎后的電話采訪中談到了他人生奮斗的目標:“我將盡我畢生的精力引領干細胞技術從實驗室走向臨床,使患者受益”。
2 主要科學貢獻[3]
胚胎發育早期的未成熟細胞具有形成機體各種組織細胞、并進一步發育成具有成熟個體的多能特性,這些未成熟細胞被稱為干細胞(stem cells)。隨著發育的進程,干細胞逐漸特化成能夠執行特定生理功能的各種組織細胞,如肌肉細胞、神經細胞、表皮細胞等。但與此同時,也是在這一功能特化的過程中,干細胞的分化潛能逐漸受限,多數細胞最后只能產生某一類型的組織細胞,而不再能分化出其他細胞種類,即失去了多能性。在成體某些部位,如骨髓、皮膚、中樞的嗅球和海馬等,雖然還存留有潛能受限的干細胞,但大部分體細胞都將進行完全的成熟分化。分化細胞的狀態十分穩定,以至于長久以來人們認為,從未成熟細胞向特化細胞發育的過程是單向的,細胞在成熟過程中發生循序的變化,它們一般不會轉分化(transdifferentiation)為其他類型的細胞或者逆轉回原始的多能狀態;利用外界的干預策略也很難逆轉細胞發育的命運。
2.1 體細胞核移植(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SCNT)
盡管成熟細胞發育程序不可逆轉的觀念根深蒂固,但總有一些科學家“異想天開”,試圖尋找將成熟細胞從終末分化的狀態解鎖,并使其逆轉回具有多能性的原始細胞的方法。193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德國科學家Han Spemann就曾在1938年提出細胞核移植的奇妙設想,即把分化細胞的細胞核轉移到一個去核的卵細胞中,以分析這個分化細胞核的發育潛能。1952年,兩位美國科學家Rober Briggs和Thomas King使Spemann的設想得以實現[4]。他們利用一種兩棲類動物—豹蛙,分別從其胚胎早期的未分化細胞和胚胎后期的分化細胞中取出細胞核,將它們轉移到去核的受精卵中。結果顯示,接受胚胎早期細胞核轉移的卵細胞最終發育出成體;而分化細胞的核移植則不能重啟卵細胞的發育進程。由此得出結論,分化細胞的細胞核已失去啟動發育的多能特性[5]。
1958年,為了驗證與上述“分化細胞核不具發育潛能”的結論不同的假設,牛津大學博士生John B.Gurdon選擇了另一種兩棲類動物—非洲爪蟾蜍進行核移植實驗(圖3)。今天,我們可能還清楚記得《細胞生物學》教科書中對這個經典的體細胞核移植(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SCNT)實驗的描述:通過紫外線照射去掉卵細胞的核;取出成熟分化的腸上皮細胞的細胞核,將其轉移到去核的卵細胞中;核的進入刺激卵細胞開始分裂,并啟動卵細胞的發育進程;最終這個卵細胞發育產出子代。Gurdon發現這些蝌蚪逐漸長大,且有少數蝌蚪具有正常功能特性,因此他認為這足以說明經歷了體細胞核移植的動物確實能夠發育成正常個體。Gurdon也在研究中改進了Briggs和King的核移植技術,通過連續注射,細胞核重編程的效率得到較大改善。Gurdon的結論是,分化體細胞的細胞核仍具有逆轉回多能特性的潛力,當將其移植到卵細胞中時,可啟動發育進程,產生全部的體細胞類型。
Gurdon的實驗首次證實,成熟分化的體細胞基因組仍攜帶向所有細胞分化的指令信息。這一發現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找到了研究受精卵發育全過程的突破口,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應用體細胞核移植技術,從發育早期階段入手,就可以對細胞的重編程規律、細胞分化過程中的變化等問題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從而為揭示人類疾病的發病機制提供重要指導。但由于隨后的一些體細胞核移植實驗失敗,以及始終無法在哺乳動物上復制出體細胞核移植產生的成體子代,因此Gurdon這一重大突破的學術價值多年來沒有獲得科學界的廣泛認可。直到1997年,Ian Wilmut等在Gurdon非洲爪蟾蜍工作基礎上,通過體細胞核移植技術將成體綿羊乳腺上皮細胞的細胞核轉移到去核的卵細胞中,產生出世界上第一例體細胞核克隆的哺乳動物—Dolly羊[6],才對Gurdon的結論給予了有力支持,使他成為后來各種生物克隆實驗的奠基人。隨著克隆羊的出現,體細胞核移植技術現已被用于包括小鼠、牛、豬、狗、山羊、狼、非洲野貓等大量哺乳動物物種的克隆。遺憾的是,至今仍沒有獲得人源體細胞核移植產生的原始多能干細胞。

圖3 Gurdon和Yamanaka的主要科學貢獻及價值(引自諾貝爾獎官方網站)
2.2 誘導多能干細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 cells)
體細胞核移植實驗需將細胞核取出,并進一步注射到去核的卵細胞中。這一過程步驟繁瑣,技術要求高超。若對細胞不加任何處理,即無需去核、取核和核移植,應用簡單的分子生物學技術,就能將成熟分化的體細胞完全誘導逆轉回歸成未成熟的多能狀態,這似乎更加不可思議。2006年,也就是在Gurdon進行體細胞核移植和細胞重編程實驗的44年后,Shinya Yamanaka在小鼠體內破譯了將體細胞重編程使其逆轉回原始干細胞的過程,這些重新編寫了發育程序、具有向機體各種細胞分化能力的未成熟細胞被Yamanaka命名為誘導多能干細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 cells)。
iPS細胞的實驗始于對胚胎干細胞(embryonic stem cells,ES cells)的研究。ES細胞來源于囊胚期的內細胞團(inner cell mass),具有分化出3個胚層、各種體細胞的多能特性。1998年,人ES細胞在體外培養成功[7],進而掀起了干細胞研究浪潮,Yamanaka也是其中的追隨者之一。但ES細胞可能會涉及到使用人類胚胎的倫理問題以及移植后的免疫排斥問題;Yamanaka也意識到ES細胞的局限性。故當人們對ES細胞的研究如火如荼之際,Yamanaka另辟蹊徑,他參考了Gurdon、Wilmut等前輩在體細胞核重編程方面的研究,設想一些維持ES細胞多能性的因子極有可能會誘導體細胞具有多能性,于是他開始嘗試尋找在ES細胞中特異表達或發揮關鍵作用的轉錄因子[8]。到2004年的時候,Yamanaka帶領他的團隊共獲得24個可能誘導多能性的候選因子,并將它們全部一次性導入小鼠皮膚的成纖維細胞,發現一些成纖維細胞確實呈現出與ES細胞非常相似的克隆形態、增殖能力和部分特異基因的表達(圖3)。之后,導入的基因數目逐個減少,最終確定僅用4種轉錄因子 c-Myc、Oct3/4、Sox2和Klf4的組合就足可誘導成纖維細胞轉變為iPS細胞,其中Oct3/4的作用最為重要。這些細胞在裸鼠體內分化出含有來自3個胚層不同種類細胞的畸胎瘤,顯示了其多能性。2007年,Yamanaka應用這4個因子成功誘導出人iPS細胞[9];在另一篇報道中[10]應用 Oct3/4、Sox2、Nanog和Lin28 的組合也誘導出人iPS細胞。這些人iPS細胞與人ES細胞在形態、基因表達及多能細胞特異基因的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性狀上都非常相似,它們能夠在體外分化出3個胚層的多種細胞類型,并在體內形成畸胎瘤。由于c-Myc屬原癌基因,考慮到其明顯的致瘤性,在以后的研究中去掉了這個因子,發現僅用Oct3/4、Sox2和Klf4也可同樣獲得功能正常的iPS細胞。而用Oct3/4和Klf4兩種因子甚至僅用Oct3/4一種因子就可誘導小鼠神經干細胞(neural stem cells,NSCs)重編程形成iPS細胞。隨后,猴和大鼠的iPS細胞也相繼被誘導出來[11]。
除了成纖維細胞,小鼠骨髓細胞、肝細胞、胃上皮細胞、胰腺細胞等也可產生iPS細胞;人iPS細胞可從皮膚的成纖維細胞、角質細胞、造血祖細胞等誘導生成;而終末分化的淋巴細胞和有絲分裂后的神經元[12]也可誘導形成iPS細胞。綜合看來,盡管不同細胞產生iPS細胞的效率可能大相徑庭,但似乎所有的體細胞都具有被重編程而變成iPS細胞的潛能。
iPS細胞與ES細胞具有高度相似性,且不存在倫理質疑和可能的異體排斥問題,因此一經發現就被研究人員賦予了巨大的臨床治療使命。如目前已從多種退行性疾病的患者體內獲得iPS細胞,包括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癥(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ALS)、脊髓肌肉萎縮癥(spinal muscular atrophy,SMA)、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脊髓損傷、黃斑變性等,用以進行細胞替代療法的研究。iPS細胞也非常適用于建立多種遺傳疾病的模型,來自疾病特異的iPS細胞不僅可模擬出單基因突變疾病的表型,還適用于遲發性多基因疾病,因而對分析疾病發病機制、探索新的治療方法等都有令人鼓舞的價值[13]。2010年,Kobayashi等[14]將大鼠iPS細胞注射入有胰腺發育遺傳缺陷的小鼠囊胚中,結果在小鼠體內發育出大鼠的胰腺,提示未來利用iPS細胞制造人類器官的應用前景。
3 問題與展望
一直以來iPS細胞受到的最大質疑就是它與ES細胞是否真正相似。雖然有部分結果顯示它們存在差異,尤其是在表觀遺傳學的修飾上有明顯不同,但大部分實驗數據還是提示兩者難以區分。出現不一致的研究結論可能與不同實驗室所用的誘導方法、培養條件、重編程因子的順序等不同有關。Yamanaka認為“這個問題并不重要,ES細胞不應成為判斷iPS細胞特性的金標準;研究者應更關注iPS細胞本身,而無需與ES細胞進行比對”。
iPS細胞技術的最大優勢就是簡單、可重復性高;但這一技術目前仍面臨諸多棘手的問題,如高度的成瘤性和轉基因的安全性隱患,甚至有人懷疑iPS細胞實際上是將成體組織中的干細胞轉變成了癌細胞,而非對成熟細胞的重編程。因此,如何改善iPS細胞產生方法、增加細胞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將成為今后iPS細胞研究的重點。普遍的觀點認為,使用的重編程因子越少,iPS細胞的安全性就越高,如應用Oct3/4一個因子產生iPS細胞;在攜帶基因的載體方面,與常用的反轉錄病毒或慢病毒相比,腺病毒或質粒可顯著降低整合到宿主基因組中的機會;若進行臨床和藥物實驗,選擇取材簡單、安全的體細胞也很關鍵,從臍帶血細胞分離獲得iPS細胞則可能更具實用價值[11]。近期的研究[15]表明,為了減低成瘤風險,甚至可跨越iPS細胞階段,直接從一種體細胞類型誘導分化成另一種體細胞,如應用Mash1、Nurr1和Lmx1a直接誘導人成纖維細胞轉變成多巴胺能神經元;而在組織原位直接進行細胞重編程的嘗試則更具前瞻性[16]。
Gurdon和Yamanaka兩位科學家在發育學方面前所未有的發現改變了人們對于細胞分化程序的理解(圖3)。雖然Gurdon認為他們兩者的研究實際上缺乏內在的聯系,但無論是體細胞核移植啟動發育進程還是導入多能轉錄因子產生iPS細胞都為研究疾病的發病機制提供了難得的契機。尤其是來自患者或疾病特異的iPS細胞,通過與健康機體細胞進行比較,可成為研究疾病機理、進行藥物篩選和毒性試驗的寶貴工具,也可能為未來的疾病治療提供新的策略。然而,包括Yamanaka本人在內的許多科學家謹慎認為,鑒于iPS細胞還存在大量懸而未決的問題,目前談及iPS細胞的臨床應用、特別是對其再生治療的價值進行評價還為時尚早。這將成為又一個艱巨的任務,希望攻克它不會再是半個世紀的等待。
[1]Gurdon J B.The developmental capacity of nuclei taken from intestinal epithelium cells of feeding tadpoles[J].J Embryol Exp Morphol,1962,10:622-640.
[2]Takahashi K,Yamanaka S.Induction of pluripotent stem cells from mouse embryonic and adult fibroblast cultures by defined factors[J].Cell,2006,126(4):663-676.
[3]Frisén J,Lendahl U,Perlmann T.Scientific background:mature cells can be reprogrammed to become pluripotent.The Official Web Site of the Nobel Prize.“The 2012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Advanced Information”.[EB/OL].(2012-10-13).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medicine/laureates/2012/advanced.html.
[4]Briggs R,King T J.Transplantation of living nuclei from blastula cells into enucleated frogs'eggs[J].Proc Natl Acad Sci USA,1952,38(5):455-463.
[5]King T J,Briggs R.Changes in the nuclei of differentiating gastrula cells,as demonstrated by nuclear transplantation[J].Proc Natl Acad Sci USA,1955,41(5):321-325.
[6]Wilmut I,Schnieke A E,McWhir J,et al.Viable offspring derived from fetal and adult mammalian cells[J].Nature,1997,385(6619):810-813.
[7]Thomson J A,Itskovitz-Eldor J,Shapiro S S,et al.Embryonic stem cell lines derived from human blastocysts[J].Science,1998,282(5391):1145-1147.
[8]Yamanaka S.Ekiden to iPS Cells[J].Nat Med,2009,15(10):1145-1148.
[9]Takahashi K,Tanabe K,Ohnuki M,et al.Induction of pluripotent stem cells from adult human fibroblasts by defined factors[J].Cell,2007,131(5):861-872.
[10]Yu J,Vodyanik M A,Smuga-Otto K,et al.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lines derived from human somatic cells[J].Science,2007,318(5858):1917-1920.
[11]Yamanaka S.A fresh look at iPS cells[J].Cell,2009,137(1):13-17.
[12]Kim J,Lengner C J,Kirak O,et al.Reprogramming of postnatal neurons into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by defined factors[J].Stem Cells,2011,29(6):992-1000.
[13]Yamanaka S.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past,present,and future[J].Cell Stem Cell,2012,10(6):678-684.
[14]Kobayashi T,Yamaguchi T,Hamanaka S,et al.Generation of rat pancreas in mouse by interspecific blastocyst injection of pluripotent stem cells[J].Cell,2010,142(5):787-799.
[15]Caiazzo M,Dell'Anno M T,Dvoretskova E,et al.Direct generation of functional dopaminergic neurons from mouse and human fibroblasts[J].Nature,2011,476(7359):224-227.
[16]Qian L,Huang Y,Spencer C I,et al.In vivo reprogramming of murine cardiac fibroblasts into induced cardiomyocytes[J].Nature,2012,485(7400):593-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