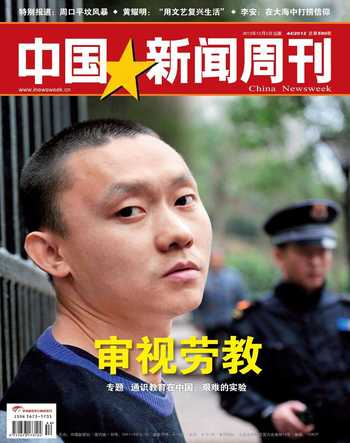另眼觀“通識”
薛涌
中國高等教育界呼喚“通識教育”已經有數年之久,“通識教育”的價值在哪里?我不妨先講兩個故事。
喬治亞理工學院的21世紀大學中心的主任理查德·A·德米洛是惠普公司前高管,非常務實。本世紀初IT產業泡沫破滅時,大量計算機專業的學生找不到工作。德米洛先生時任計算機學院院長,問某企業高層究竟需要什么人才,對方答:傳統的計算機技術人員不缺,但那種有講故事能力的人才特別稀缺,因為計算機游戲正熱,游戲需要精彩的故事結構。于是,德米洛先生鼓勵計算機學院的學生讀文學,同時敦促文科學生涉獵計算機,一夜之間,文學這個最“沒用”、最“不實際”的專業,成為計算機這一最“有用”、最“實際”的專業的救星。
谷歌元老桑托斯·賈亞拉姆曾被請到大學演講。他也出人意料地勸導學生們別總盯著技術,要珍視文學的價值:企業最需要的是能講故事的人,要把正在開發的產品講得仿佛已經存在了,市場會被煽動起來,天使投資就會急急忙忙找上門來了,再把技術細節交給軟件工程師們,就成功了。
這兩個故事,把“通識教育”的價值描述得繪聲繪色。但是,在這個“創新”口號喊得震天響的時代,“通識教育”在中國高等教育的道路依然障礙重重。最近幾年,中山大學的博雅學院、北大的元培學院、上海的復旦學院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嘗試,但似乎尚未出現令人信服的模式。學生或家長就讀大學或留學向我咨詢時,最普遍的問題依然是:應該選擇什么專業?似乎高等教育歸根結蒂還是個專業問題。
究竟“通識”與“專業”之間的關系該如何處理,中國高校該如何選擇改革的方向,或許還存在一些此前從未考慮到的誤區。
“歐洲范”與“美國范”
目前中國的通識教育體系和介紹,大量過度偏重美國的通識教育傳統,往往略過歐洲傳統,事實上,歐美如何培養社會適用人才的制度上,有著鮮明的不同。
歐陸教育體系的一個慣行是,中學階段就分軌,學業優異的進入大學準備課程,其余則經受類似技工學校式的訓練。德國就是一個典型:10到13歲的學生中,不到30%的學業優異者被選入“大學預科”,其他人則可在350多個技能中選擇專項發展,并有機會到工廠接受學徒式訓練,畢業后直接就業。
從美式教育的價值立場出發,這種過早專門化的體系,剝奪了孩子們的選擇自由。美國人總是鼓勵孩子:“你可以成為任何你想成為的人”。歐洲體系等于對這種平等精神說“不”,仿佛勞動階層不配上大學。 但歐洲體制的形成,和過去等級社會中的行會傳統密切相關,旨在保障各種技藝在人生固定軌道上的穩定發展和完善。這樣的專業教育,比起“通識”的理念來,確實并不適合人人平等、開放流動的現代社會。
但是,美國大學中的“通識”理想,其實也未必適合當今的平民化社會。它的背后,帶著強烈的精英傳統。在19世紀,承載著“通識教育”的常青藤,主要是從“大學準備學校”招生。這種“準備學校”,多是在新英格蘭地區的貴族寄宿學校,比起德國的“大學預科”來更為精英。即使接受了“準備學校”的教育,也并非所有人都適合常青藤的精英教育。哈佛大學前校長詹姆斯·布萊恩特·科南特在上世紀40年代就指出,現有學生中有一半根本不配上大學。
大學在戰后美國普及,這個問題似乎更嚴重。幾年前,以智商理論聞名的保守主義社會思想家查爾斯·默里在《華爾街日報》連續刊登三篇文章,直言不諱地指出,高等教育對智商提出了很高要求,適合讀大學的在同齡人中僅占15%,最多25%。可是,如今美國45%的高中畢業生去讀大學,自然會很多人跟不上,白白浪費教育資源。
默里的觀點代表了美國保守主義者對高等教育的批評。在他們看來,大學“通識教育”并不培養實用技能,只能針對少數精英,沒必要鼓勵年輕一代都去讀傳統意義的大學。近年來的大學泡沫、學貸危機,就是大學教育普及過度之惡果。他們進而強調實用性的技工式教育,鼓勵大學和企業接軌。今年初,佛羅里達的共和黨州長就針對州立大學的專業設置發表評論:“如果要我把公民的錢拿來投到教育上,我將用這些錢來創造工作機會,我要讓這些錢流向那些能讓學生找到工作的專業上。難道培養更多的人類學學生符合我們州的根本利益嗎?我不這樣認為。”
事實上,近年來美國一些傳統的四年制地方大學,已經開始與通用電氣等大企業合作,根據企業需要培訓技能,另一些低層級大學,也有走向專業技術教育的“歐洲化”傾向。
而歐洲體制也在“美國化”。隨著產業升級,經濟中的技術含量越來越高,德國大學教育早就突破了“大學預科”所限定的軌道。目前德國的大學生,非“大學預科”出身的已占一半以上。那些以美式的“通識”理想批評歐洲過早分科的人沒有看到:現代歐洲的教育體系已并非早早就把孩子固定在讀大學或當技工的軌道上,孩子們在證明自己的能力后可以從技工學校跳到大學預科,照樣可以上大學。這種體系所要求的不過是一種資格:不靠家門,不靠金錢,但必須靠能力,誰也不能拍怕腦袋就“成為任何自己想成為的人”。
美國的“通識教育”和歐洲的“專業教育”,歸根結底還是適用和服務于各自的社會經濟結構。
歐洲的福利制度為技術工人提供了穩定的職業軌道。在德國,企業無法隨意解雇員工,許多員工一輩子在一個企業工作,薪金優厚。有了這種安全感,一個中學生決定把自己的青春投入一項狹窄的技能訓練時,就不會感到太大的風險,動機也強得多。
美國以自由競爭的市場為主導,早早就鉆進那么窄的一領域,被解雇了怎么辦?所以,大家多少要成為“萬能膠”,好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
“通識”的未來,從精英到平民
以上簡單的厘清,或許有助于我們對“通識教育”的思考。首先,傳統意義上的“通識教育”主要針對精英階層,其根源大概可以追溯到柏拉圖的“哲學王”理想。社會各行各業的領袖,都需要具有宏觀的哲思能力,為追隨者提供一個方向。
不過,這種“哲學王”式的教育,側重的是訓練學生如何思想,而非灌輸具體的思想內容。讀《理想國》就知道,柏拉圖(或其中主人公蘇格拉底)在所討論的諸問題上究竟是什么立場,兩千多年來聚訟紛紜,至今仍無結論。這種經典注重展示的是思想過程,而非思想結論。而《論語》等中國經典,所傳遞的主要是思想結論,等而下之的四書五經式的教育,則走向了死記硬背,和西方意義上的“通識”其實大異其趣。
在我看來, “通識教育”未必就是讀經典、名著,更在于怎么讀,師生怎么互動。如果這方面的問題不解決,甚至拉出本土傳統的旗幟,大談所謂“文化認同”“傳統承繼”,難免流于灌輸,讓人們聯想起孔乙己,喪失“通識”的說服力。
第二,對“通識教育”最大的挑戰,恐怕還在于高等教育平民化。美國那種自由放任的體制,容易產生突變性的創新,回報則大部分給了少數精英,為普通人提供的高薪機會甚少。德國模式,有利于累進式的創新,即把突破性的創新不斷精華,需要大量普通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的參與,回報分布也比較平均。美國的“通識”和歐洲的“專業”,是在這兩種非常不同的“比較優勢”之下的教育戰略選擇。
當今中國的學生,不可能像我們那代人一樣,學好專業等著國家分配“專業對口”的工作,也不可能像德國技工學校的學生那樣,知道自己精熟了哪些手藝,就可以競爭進入哪些企業,踏入穩定的職業軌道。中國學生面臨的境況更接近于美國學生:市場瞬息萬變,今天不知道明天哪塊云彩下雨,面臨突如其來的挑戰必須什么都拿得起來。這就成為“通識教育”的理由。
不過,傳統意義的“通識教育”模式,針對的還是少數精英,死守傳統“通識”模式,很可能會培養出大量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這也是美國大學體制不斷尋求改革的原因。其中一個重要的思路,就是把“通識”的理想留給精英——藝術史仍然很熱門,美國仍然珍視喬布斯那種從書法課中獲得靈感來締造蘋果產品的天才。但是,各級政府的政策不斷向社區學院傾斜,力圖用兩年甚至更短時間,短平快地滿足市場的技能需求,同時發展學生們最基本的“可轉移性技能”或“適應性技能”。
幾年前我曾預言,隨著高中畢業生減少、城市中高產子弟留學比例上升以及大學擴張,中國大學將面對“空校危機”。走出這種死局的路徑,是高等教育的低層化,比如把四年制改成兩年制。未來二三十年,數億農民進城,形成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移民。中國的高等教育可以參照美國社區學院或德國技工學校的模式,以把這些農民工轉化為能夠適應全球化競爭和產業升級的現代技術工人為首要使命。在這個背景下,“通識教育”的目標就是最基本的“可轉移性技能”或“適應性技能”,保障學生掌握基本的文字和數理技能,以在一生中能夠不斷回到大學接受一兩年的新技術培訓。
從這種意義上說,“通識”不只是在大學期間學習足夠多的經典,而是培養一種能夠終身接受教育的能力。
(作者系旅美學者,在美國薩福克大學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