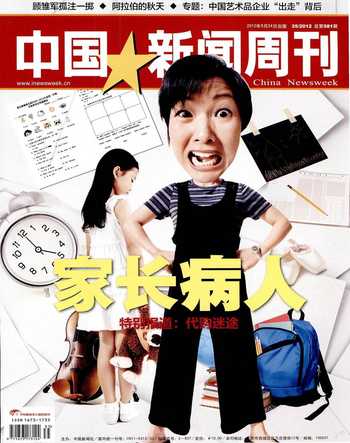《甲子園》內外的中國老人
萬佳歡
9月14日夜里,北京人藝60周年院慶大戲《甲子園》首演結束,后臺立即被各式輪椅擠得水泄不通。
90歲的朱琳和88歲的鄭榕直接坐著輪椅被推下臺,后面跟著拄著拐棍的藍天野和愈發消瘦的朱旭,他們分別是86歲和82歲。呂中和徐秀林算是演員里比較年輕的,72歲。“不累,還能演,”朱旭一邊卸妝一邊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甲子園》是人藝60周年院慶原創獻禮大戲。除了6位年齡加起來有490歲的老戲骨,王姬、雷佳、濮存昕等中生代和剛畢業的青年著名演員一齊登臺,可算“五代同堂”。開票當日,該劇就創下296萬票房、刷新人藝單日售票紀錄,最后不得不破天荒地加演9場。“藝術戰勝了政治”
2011年5月,新版《蔡文姬》演出結束后,曾為人藝創作出經典作品《天下第一樓》的劇作家何冀平主動找到導演唐燁,推薦了自己的一個歷史題材劇本。
而人藝方面則問何冀平,能否寫一個現代戲。“我們現在特別缺少關注當代生活的劇本,”唐燁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接觸了很多作家,一說當代,都不愿意寫。”
何冀平上世紀80年代末遷居香港,之后創作出電影《新龍門客棧》,電視劇《新白娘子傳奇》等作品。對于創作現代題材話劇,她十分顧慮——自己離開北京23年,對當下的北京并不熟悉。
2011年11月,北京人藝院長張和平找到何冀平,提出希望這個當代題材的劇本能參加獻禮大戲的遴選——年初,人藝接到北京市委的任務:為2012年院慶創作一出大戲,要求只有六個字,“原創,當代,北京”。
何冀平答應下來。她已經盯上了一批自己比較熟悉的群體——回北京定居的港澳臺及海外華人。而自己的母親就住在北京一家養老院里,這也給了她些許靈感。
更重要的是,她懷念老北京的生活,似乎那時候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跟現在不一樣。何冀平花了半個月寫出了故事大綱,一千字、一頁A4紙,但其中性格鮮明、背后都各有秘密的五個老人和三個年輕人的形象已經明晰。
她對導演唐燁簡要說了這個發生在一家養老院里的故事:一個海歸女孩因父親病故,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發現這里竟然變成了一家老人院。她希望盡快賣掉這個宅子、趕緊離開,沒想到被人利用,宅子差點被港商用來修建墓地,一場風波由此產生,在此過程中,每個老人的秘密也依次打開。
說完故事,何冀平忐忑地問唐燁,“你覺得行嗎?會不會不夠歌頌?”而這個故事被張和平一眼相中。
何冀平立即在20多天里走訪了兩家養老院,又采訪了20多撥年輕海歸,隨后便回香港趕劇本。《天下第一樓》她寫了三年,而現在必須在4個月內交稿。“如果有比我這個更好的劇本出現,一定讓它先上,”她對變著花樣催稿的唐燁說。
除了《甲子園》,當時的候選劇本還剩兩個。《甲子園》排名第二。接下來,人藝藝委會對這三個劇本進行審查和“排隊”:從政治上來說誰最好、從藝術上說誰最高?
“最后好像是藝術戰勝了政治,”唐燁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接到人藝書記馬欣電話,審查后《甲子園》變成了第一名。又過了幾天,馬欣告訴唐燁:告訴何老師,她的劇本已經變成唯一了。
“火葬場怎么還排隊啊”
2012年7月,進廳排練,劇本又改了4稿,其中包括兩次大幅度刪減。“有些是因為節奏,有些是因為年紀。老藝術家的戲就是很慢的。”導演之一的唐燁對年輕演員說:你們不需要判斷交流,這些老藝術家們來做,你們盡管拉(快)節奏。
90歲的朱琳飾演養老院里患老年癡呆癥的王奶奶。“哎,你們看,火葬場怎么還排隊啊?老伴兒唉,慢點兒走,過些日子我穿上你給我買的小牛皮鞋,來跟你做伴兒……”舞臺上,她洪亮但有些發顫地說出這句臺詞,她自己加上了“火葬場”一句,這是以前自己同樣患老年癡呆的老伴對她說過的話,臺下觀眾頗為動容。
何冀平萬萬沒想到,她原本只期望一兩位七十來歲老戲骨加盟,而最后《甲子園》竟然幾乎吸引了北京人藝的老藝術家們全員上陣。
“我一聽想法就覺得行,直到現在看這個劇本,我都還是很動情,”在一個休息日,主動來劇院加班的藍天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第一個確定加盟該劇,出演戲份最重的建筑師黃仿吾一角,并兼任該劇的藝術總監。
另一個重要的老人角色“姚半仙”滿口易經,大家一致認為朱旭是最合適的演出者。但朱旭一直患有肺部感染。直到今年6月初,朱旭在北京人藝建院60年一次活動現場,高聲朗誦了一段《嘩變》的臺詞,藍天野才又提出,“朱旭看起來狀態不錯,我們是不是再請一請他?”
院長張和平立即為朱旭夫婦擺了一桌“鴻門宴”。鄭榕夫婦、藍天野夫婦、《甲子園》的兩位導演任鳴和唐燁一齊上陣,說服朱旭先看看劇本。6月12日,唐燁在人民大會堂遇到朱旭,他拿著一本《易經》說:“小唐,你看,我已經開始學習啦!”
朱旭專門做了一個小抄,寫滿難背的詞,永遠放在上衣口袋里。他還有一個小筆記本,一邊寫臺詞,一邊寫此時自己的動作、心理。
鄭榕在劇中飾演一個老年癡呆、只記得戰爭期間事情的老戰士金震山。他接戲時有兩個要求,一要體驗生活,二是必須允許自己改動劇本。
“劇作家長期生活在香港,對某些人的生活不是那么熟悉,”他說,“我演的金震山整個兒全癡呆,上來以后只會講‘沖鋒,沒有思想,沒有交流。”
跟兩個老戰士長談、“引他們談到一些動心的東西,而不是單聊歷史”后,鄭榕在不改動戲份多少和劇本格局、并征得何冀平同意的前提下,把臺詞幾乎改換了一半。最后,糊里糊涂的金震山在舞臺上有了感覺,三次出場幾乎都成為笑點。
“9點半開始排,老藝術家們9點準到,”唐燁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而現在很多年輕人覺得,9點28沖進排練廳不也一樣么?”
無論如何,五位老藝術家的出演讓《甲子園》成為一次不可重復的歷史性演出。有人在觀劇后這樣留言,“這已經超出了戲劇的本身,簡直是來看人生。”
“我們雖然也有歌頌,但歌頌的是愛”
現代題材戲比歷史戲更難寫、更難排,這是何冀平面臨的一個大問題一觀眾就生活在當下,對于周遭生活,他們更有發言權。
何冀平的標準是“不能(跟現實)脫節”,劇中也由此涉及了“剩女”“穿越”等時下熱門話題。
而作為一個現代題材話劇,《甲子園》也關注到了一些當下社會中的矛盾。鄭榕第一次看劇本,就覺得里面有“金子般的臺詞”。比如女主角愛林最后形容房子,“這不是我的,我不能賣”——現在能有多少人能說“這不是我的”?大家都搶著說“這是我的”。
“這些年現代戲誰也不碰,都不愿意寫,”鄭榕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戲好在哪?賣樓給香港資本家蓋祖墳,就是針對現在社會上房地產問題的。人離不開社會。”
《甲子園》還簡單涉及了文革。當建筑家回憶到父親被紅衛兵打倒、爺爺在樹下上吊的情節時,導演在一旁打出字幕:“你是人,我也是人”。
然而,這部劇目看上去還是十分溫和。它結局光明,將主題定位于弘揚“大愛”。
“我們雖然有歌頌的東西,但我們歌頌的是愛,”唐燁說。“它不是那種‘有點讓人受不了的獻禮的感覺。我們希望能排出一部能留世的東西,不想應景。”
《甲子園》全劇結束在這樣一個具有希望的場景中:一個小女孩騎著女主角陳愛林兒時的小車出現,兩人一同望向正前方。
“女主角看著小女孩,后者可以是她的過去,也可以是她的孩子,也可以是在甲子園玩的某一個孩子,”導演任鳴說,“這個語匯象征,甲子園是屬于未來的、是一代代傳下去的。”
這個表現主義、現代主義風格的場景并非人藝傳統的純現實主義風格。出現在《甲子園》里的類似場景還包括藍天野和王姬的“隔空對話”。
“我們可以吸收合適的表現主義、象征主義等各種優秀手法,使現實主義更豐富,”導演任鳴說,“北京人藝的現實主義是發展的現實主義,不是保守的、博物館式的。”
而仍然有評論指出,該劇的故事和表現方式有些陳舊。“我覺得不管用什么方式,你總要說人話、演人的事,把一個能看得懂的故事帶給觀眾,”唐燁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對年輕觀眾來說不會乏味,但你要是抱著想來笑、來發泄的心態,可能這部分觀眾會失望。”
“高僧只說家常話。深入難,淺出更難,”任鳴說,“不能說總追求高深。我們尊重現實主義、尊重觀眾,但不代表我們沒有主張、追求;最大的本事是讓別人能懂得你的追求,而不是拋開觀眾、讓他們聽不懂并拒絕交流。觀眾看不懂證明你(導演)水平低,只有看懂才能產生共鳴。”
“為什么我88歲了還要來演?我愿意在現實主義的回歸中出一把力,”鄭榕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另外,我們過去的現實主義表演方法現在還靈不靈?我想現在再試驗一下。就這兩個動力。”
“這個題材特別人藝,這么多老藝術家參演又展現了人藝的精神,”任鳴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現實主義還是應該薪火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