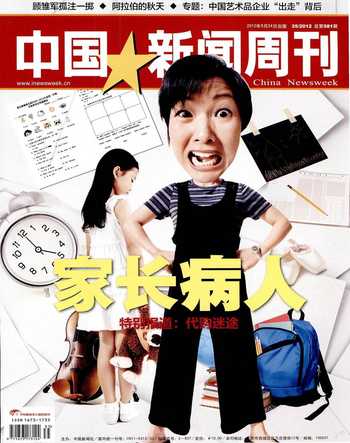伊斯坦布爾的帝國斜陽
黃玉
奧斯曼帝國瓦解后,世界幾乎遺忘了伊斯坦布爾的存在。我的出生城市在她2000年的歷史中從不曾如此貧窮、破敗、孤立,她對我而言一直是個廢墟之城,充滿帝國斜陽的憂傷。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出生于伊斯坦布爾的作家帕慕克如此寫道。
土耳其語中,“憂傷”音為“呼愁”。背負著帕慕克的沉沉“呼愁”,我乘坐的飛機從北京起飛,穿越古老的亞細亞,掠過連綿數千里的古老絲綢之路,向伊斯坦布爾飛去。
抵達伊斯坦布爾時,已是凌晨。睜開睡眼往舷窗外看,頓時涼艷:伊斯坦布爾如一朵晶瑩奪目的巨大胸花,別在一塊密密實實的黑絲絨上。那明滅的燈光,沿著海岸線高低起伏、疏密有致地閃爍著,遠處,馬爾馬拉海漆黑如暗夜,偶爾有幾艘歸家的快艇飛馳而過,竟仿似顆顆流星劃過夜空墜入燈海。
入住的賓館在伊斯坦布爾老城,從客房窗戶望出去,圣索菲亞教堂和藍色清真寺在夜色中并肩而立。海就在不遠處靜靜地躺著,對岸似乎是個國際碼頭,大貨輪的汽笛聲隱約可聞。此刻,夜色將盡,星月熹微。
伊斯坦布爾是一個有著2700年歷史的城市。它橫跨亞歐大陸,黑海、愛琴海和地中海將其環抱。這個城市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也有著輝煌與挫敗交織的滄桑歲月。對過往的輝煌的不舍和對融入西方世界的渴盼,曾經讓它在掙扎與糾纏中,被憂傷浸透。
進入本世紀,伊斯坦布爾大張旗鼓走上復興之路,各種修復和重建計劃逐步推行,往日的勃勃生機重現,自信與從容也重新回到了伊斯坦布爾人的臉上。只是,城市的氣質更趨于內斂沉穩。
土耳其是一個穆斯林人口占98%的國度。在伊斯坦布爾街頭,能看到許多蒙著頭巾的婦女閑閑走過。土耳其的絲很有各,土耳其婦女的頭巾也花樣百出,色澤鮮亮。頭巾下露出俊俏的五官,那睫毛不是一般的長,忽閃之間,如顫動在風中的蝶之翼。尤其是腳踏锃亮的黑皮靴、全身裹在黑袍中的女子,走過時衣袂生風,眉宇間別有一種帥氣。
土耳其的男子五官英俊自不必說,耐熱能力亦是一流。八月的街頭,艷陽高照,土耳其男子一身西服筆挺,不疾不徐地走在熱力四射的街巷中,那份從容淡定,著實令人驚嘆。
令人驚嘆的,還有滿大街自在穿行的貓。不知是不是土耳其人特別喜歡貓,總之貓在伊斯坦布爾隨處可見,不知是家貓還是野貓,但都有一個共同特征,身瘦腿長。看來貓隨主人啊。
唯一令我難以接受的是這里的飲食。幾天吃下來,發覺每餐都一樣,黃瓜、西紅柿、洋蔥、檸檬汁、薄荷葉合成一道沙拉,配上一筐面包,一盤奶酪、果醬,客氣點的給上塊烤肉,偶爾有個煮雞蛋,餐后送來一杯土耳其紅茶或者咖啡。
為了能吃頓好的,我毫不猶豫答應主人的邀請,去參加當地人家的婚禮。誰曾想,婚禮宴席上仍是老幾樣。但是,入夜之后,對對男女攜手前來,男子大多西裝革履,女子則清一色的晚禮服,衣香鬢影,淺唱低吟,風情無限。
既然混不上好吃好喝,我只好一有空就穿街過巷去看風景。
有人說,伊斯坦布爾就像一個巨大的露天博物館,收藏了土耳其的歷史。它曾長期是中東地區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又是絲綢之路亞洲部分的終點,東西方文化在這里融合。一大批薈萃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風格的建筑在這里經風歷雨,從容佇立,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圣索菲亞大教堂。
得益于工作之便利,我曾參訪過不下10個名叫圣索菲亞的教堂,唯有伊斯坦布爾的這座教堂,令我感慨良多。
據說,當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第一次踏進教堂時,他如此感嘆:“光榮屬于上帝,他讓我創造了這樣一個奇跡。啊,所羅門,我終于勝過你了!”1400多年后的今天,踏足這座圣殿,我深深感到,查士丁尼所言不虛。
進入大教堂,很容易被那直徑32米、20層樓高的巨大穹頂震撼。不靠任何支柱,整個穹頂就那么浩浩蕩蕩、莽莽蒼蒼地懸罩于半空中。中國的《敕勒歌》中說“天似穹廬”,這里卻是“穹廬似天”。各色人等站在這片天空下,無不自覺渺如塵煙。
有人說,世界宗教史其實是一部血腥屠戮史。也許言之過甚,但圣索菲亞大教堂的歷史又似乎印證了這一點。
史載,圣索菲亞大教堂是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在位時修建的,于537年完工,給羅馬帝國的輝煌添上了華彩的一筆。當時,它是基督教世界最宏偉的教堂。
1204年,圣索菲亞大教堂遭十字軍洗劫,君士坦丁堡主教也被剝奪神職,取代他的是拉丁主教。
1453年6月,奧斯曼土耳其蘇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終于走進了他朝思暮想的圣索非亞大教堂。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將教堂內所有拜占庭壁畫用灰漿遮蓋,將所有基督教雕像搬出。大教堂改為清真寺,四周立起了清真寺喚禮塔。
17世紀,土耳其蘇丹艾哈邁德一世下令,在離圣索菲亞大教堂百步之遙,建造了藍色清真寺,來與之一較高下。不知是不是為了表示其地位尊于大教堂,藍色清真寺未遵守只有圣城麥加的清真寺才能建六根喚禮塔的規矩,逾矩建了六根喚禮塔。而圣索菲亞只有四根,且顏色不一,三根灰色,一根褚紅。
1953年,圣索非亞大教堂改為博物館。2008北京奧運火炬傳遞,這里是伊斯坦布爾的起跑點。
千百年滄海桑田,歷經政權更迭、宗教興替,終至凝成圣索菲亞大教堂今日之驚世氣韻。就如混血兒一般都聰慧可愛,由于融匯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元素,今日的圣索菲亞教堂有著非同一般的華麗炫目。
懸掛在墻上的6個直徑約10米的大圓盤上,均用金子刻著阿拉伯文的“萬物非主,惟有真主”。圓頂上的基督像、半圓壁龕中被大天使簇擁的圣母抱嬰像,以及耶穌遇難十字架的殘片真品,全都籠罩在金色光芒中,耳邊仿佛有“哈里路亞”的圣歌飄過。大教堂地面由刻有百川歸海條紋的大理石鋪就,墻上是正紅、金黃、翠綠、湛藍等艷色鑲嵌出的基督教主題畫作,精美的石柱深具伊斯蘭風情,基督教的圣壇和清真教的經壇并立,看上去不僅不覺其突兀,反而有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之感。
兜兜轉轉,在圣索菲亞教堂里盤旋一天,仍是未識全貌。教堂外,藍色清真寺喚禮塔的喚拜聲已破空而來。穆斯林們一群群步入清真寺,一些正在街邊勞作的人們也放下手中活計,入得內室,鋪開拜毯,虔誠禱告。
清真寺外廣場正中的大楓樹下,一位老奶奶手持經書,披一身夕陽閑閑安坐。落葉墜落,游人嬉鬧,她都不視不聞,仿佛世間只此一卷。
海風颯颯拂面。席地而坐,仿佛慢慢跌入伊斯坦布爾的深處。馬爾馬拉海中倒映著古羅馬帝國的殘陽,海岸邊,剪影般的斷壁殘垣如此蒼涼。千百年前的血雨腥風,此刻竟似觸手可及。
“美景之美,在其憂傷。”這是帕慕克在諾貝爾頒獎典禮上的感言。這一瞬間,我被一種突如其來的巨大悲涼,淹沒在異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