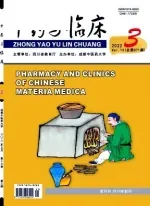中藥連作障礙防治的微生態研究模式探討
嚴鑄云,王海,何彪,劉敏,王光志,陳新,萬德光
中藥連作障礙是指同一藥用植物或近緣種連作后,在正常管理的情況下,產生產量降低、品質變劣、生長發育狀況變差的現象。隨著中藥材需求量不斷增加,由于耕地的限制、耕作制度的改變、經濟利益驅動和種植條件等因素的限制,中藥材生產中出現連作和復種連作的面積越來越大。連作常常導致中藥生長發育不良,產量和質量降低,甚至不能生長[1]。絕大多數中藥忌連作,如人參、西洋參、丹參、黃連、川明參、地黃、三七等常用中藥均不能連作。隨著人們環保意識加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質量和數量方面對中藥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連作障礙已成為我國中藥材生產中亟待解決的一個突出問題。雖然大豆和一些蔬菜連作問題的研究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對其機理研究正在成為植物微生態研究的焦點之一,已經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
從藥用植物微生態系統的角度研究連作障礙機理是重新理解連作障礙的新思路。以前許多學者對連作障礙進行過多方面的研究,但未揭示連作障礙產生的實質,因而至今仍缺乏有效的防治措施,已有研究常僅針對連作障礙產生的某一方面,如養分、蟲害、病害、化感物質等問題。對“植物—土壤—微生物”組成的藥用植物微生態系統缺乏整體的研究。因此,應用微生態學的理論重新思考和探討連作障礙產生的機制及影響因素,并提出相應的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1 中藥連作障礙及其危害
我國是一個中藥生產和消費大國,可栽培生產的中藥材中大部分品種忌連作。如吉林省是我國人參、西洋參的主產區,但栽過一茬人參或西洋參的土壤在幾年甚至幾十年內不能再栽種人參或西洋參,否則人參、西洋參須根會大量脫落,病害非常嚴重,用老參地繼續栽種人參,根腐病、疫病、立枯病、猝倒病、菌核病、黑斑病、細菌性軟腐病等土傳病害也嚴重[3]。人參連作后其根周皮爛紅色、長滿病疤,致使人參地上部分死亡,有的地塊幾乎全部絕收[2]。百合隨著連作年份的增加,產量和品質下降、病蟲害加重[4]。我們在調查中觀察到,川明參連作后植物長勢差,根腐病嚴重,產量減少40%~60%;丹參連作后植株矮小、根結線蟲和根腐病嚴重,根表面瘡斑較多,產量減少50%~70%,部分地區甚至絕收。
我國中藥材出口呈現日益增加的趨勢,許多國外商家都要求提供傳統道地產區和按GAP生產的藥材。我國耕地面積有限,特別是傳統道地產區面積更有限,由此引起的道地產區重茬栽培中藥現象已十分普遍。由于前茬土壤再植同種中藥出現植物生長衰弱、根系生長不良、病害加重,具有時間和空間上的持久性。增加肥料和農藥的使用,以期獲得較大的經濟回報,出現“道地產區生產非道地藥材”已為普遍現象。可見連作障礙已成為一個廣泛存在、危害嚴重的中藥材生產,特別是道地藥材的生產問題。由此,將危害中醫藥事業的健康發展。
2 連作障礙的機制

圖1 植物微生態系統物質、能量、信息流動示意圖
植物與土壤相互作用形成了一個以植物共生體系為中心,植物根際為界面的植物微生態系統。該系統的能量流動、信息流動、物質流動異常強烈(見圖1),這種強烈的相互作用結果使土壤物理、化學和生物環境發生了明顯變化。其中,土壤物質化學行為特征的變化引發的植物共生體系改變,可能是引起中藥連作障礙的重要機制。土壤化學物質的變化主要是根際分泌物、地上部分的淋溶物和微生物的代謝產物等不斷進入土壤,一方面使植物根際微生物種群結構改變,一些原來非優勢種群成為優勢種群,特別是致病菌和病原蟲成為優勢種群,同時植物生長過程中產生的大量次生代謝產物,使蟲卵孵化、群體數量增加,增加浸染植物的機會;另一方面改變植物根系對物質的吸收狀況,引起植物代謝庫的改變,從而改變植物內共生和表共生體系;此外部分進入土壤的植物分泌物和微生物的代謝產物,能抑制、破壞植物根際的細胞分裂生長,從而給植物造成嚴重傷害。連作對土壤物理環境產生改變。一方面植物根系改變了土壤氣、液、固三相的比例,使土壤微粒結構、Eh、pH、土壤酶活性等發生變化;另一方面植物生長過程會存在養分的偏耗,同時向土壤中分泌的一些自毒物質,影響細胞膜透性、酶活性、離子吸收和光合作用等,這些因素對植物的生長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由此可見,中藥連作障礙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主要表現為病害、蟲害、化感作用和改變共生結構等幾個主要方面。
2.1 病害危害
植物根分泌物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植物病原菌,主要是抵消了土壤的抑菌作用,誘導病原菌繁殖和萌發,也可能抑制了病原菌拮抗微生物的生長。任何生物的、物理的、化學的和機械的因素都可以通過刺激和抑制作用來影響植物的生理代謝活動和功能,從而影響根分泌物質的種類和數量,以及根際微生物的種群結構。藥用植物病害發生必備的條件有:①感病植物品種;②植物體表面有足夠的病原繁殖體或接種體密度;③繁殖體迅速萌芽和浸染植物所需的信息物質和營養物質;④適合病原菌活動的生物、物理和化學環境。特定條件下,普通根際微生物能變為病原菌,能夠產生抑制植物或促進病原菌定植的物質,誘導植物發生病害。如Pseeudomonas sp.屬細菌對菜豆就是機會致病菌。
植物根系起到選擇性培養基的作用,凡營養需求與“天然選擇培養基”成分吻合的微生物,則在根際土壤中大量繁殖,成為該特殊區域微生物區系中的優勢類群(數量最多),其他微生物數量相對減少;若上述大量繁殖的微生物為有益菌,則促進作物生長;如為病原菌,則侵染作物根系,導致作物發病。在同一塊地中連續種植某一種藥用植物就會建立起專化性病原群體,根系分泌物可誘導厚垣孢子、卵孢子和菌核的萌發,以及休眠菌絲的活化。根際分泌物對某些致病菌有趨化作用[5]。如大豆重茬后危害較嚴重的病害主要是根腐病,重茬越久患病越嚴重;大豆連作3年以上,土壤微生物數量與組成發生改變,細菌數量減少,真菌成為優勢種群,重茬較正茬增加18.0%~35.5%,并以青霉菌、鐮刀菌、立枯絲核菌占多數[6]。植物病原微生物侵染根部,導致碳水化合物、氨基酸、蛋白質、脂類和核酸等物質代謝的改變,使根的分泌作用加強,根際周圍微生物種群數量也增加,病原菌侵染根部,破壞了細胞膜透性,使細胞內化合物以擴散方式釋放至根際[7~8]。可見,根系分泌物和根際微生物與連作障礙之間有著明顯的相互關系。
現代中藥農業的最大特點是單一品種的大面積種植,這給病原菌在土壤中的富集提供了適宜而豐富的營養物質,并在寄主衰亡后在植物殘體上繼續繁殖,藥用植物連作更加重了這已趨勢。
2.2 線蟲危害
中藥栽培中的蟲害種類較多,其中線蟲種類多、分布廣、寄主范圍廣、適應環境能力強、繁殖快,對作物具有較大的危害作用。部分植物的根系分泌物有促進線蟲繁殖的作用,大豆根系分泌物可促進孢囊線蟲的孵化,重茬越久孢囊線蟲病和根前蠅的患病越嚴重[6]。常常連作后導致線蟲種群數量急劇增加,加劇了對植物的危害。據FAO保守估計,全世界每年因線蟲在21種作物上的危害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就達777億美元。寄生植物的線蟲可以引起許多重要的植物線蟲病害,如大豆胞囊線蟲病、花生根結線蟲病、甘薯莖線蟲病和水稻干尖線蟲病等[9]。我們在調查中觀察到,全國8省26個產地的丹參均有不同程度的根結線蟲危害,尤以河北、四川、山東、河南較為嚴重,其中山東部分傳統丹參產區由于孢囊線蟲病危害,無法再生產丹參,而改種桃樹。此外,有些線蟲還能傳播真菌、細菌和病毒,促進它們對藥用植物的危害。
2.3 化感作用
“化感作用”是指植株向環境中釋放某些化學物質,影響周圍其它植株生理、生化代謝及生長過程的現象,具有化感作用的物質稱“化感化合物”。Candolle.D[10]認為作物連作減產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根部分泌有毒物質并積于土壤所致。其作用機理可概括為:一種植物產生的生克物質滲入到其它植物體內,影響受體植物細胞膜的透性、營養元素的吸收和運輸、有機物質的代謝、光合和呼吸作用,以及植物解剖結構、植物體內酶的活性和激素平衡的變化等等。如抑制種子萌發和幼苗生長,抑制萌發過程中的關鍵酶,阻礙萌發過程;抑制蛋白質合成及細胞分裂,抑制光合和呼吸作用,抑制酶活性,影響水分代謝和營養的吸收等。揮發作用、淋溶、植物體分解、根系分泌是克生物質產生克生效應的幾種重要方式。化感作用物質的產生與作用程度,取決于植物生長環境、植物組織年齡、品種等不同因素。營養不良、土壤缺氧、干旱等不利條件,會使某些植物的毒素抑制劑增加。在多雨或溫度高的地區或年份,溶解在雨水或露水中的植物克生物質的作用顯著增強。近年來植物化感作用研究已成植物保護學、生態學、植物學、農學和林業學等相關領域研究的熱點問題。
藥用植物連作后生長不良,產量下降,是一種適應性的自我抑制,是植物對環境脅迫條件自我調節以減少能量消耗方式。但從自然選擇和植物種類演化來看,自我抑制是非常必要的,具有重要的生態學意義。
2.4 共生結構的改變
植物是由植物與其共生微生物(內生菌、表共生菌和菌根菌)組成植物共生系統(又稱超有機體)[11],這種共生系統決定了植物的生長、發育、繁殖和生態適應過程。微生物與植物協同進化,形成了共生關系,微生物參與植物的一切生命活動,包括吸收、分解、合成、生長、發育、患病和死亡[12]。其中內生真菌具有促進植物的生長發育、提高植物的抗逆性、產生與宿主相同或相似的化學物質、產生具抑菌活性的物質、促進宿主某些代謝產物的形成和生長[13]。同時植物共生系統結構決定了其生態位,如美國黃石公園地熱源的高溫地帶上生長的一種耐高溫植物Dichanthelium lanuginosum,其驚人的耐高溫特性與其植物共生系統中的菌類Curvularia protuberata相關[14]。同時,同一種植物生長在不同環境[15~16]和不同生長年限[17]內生真菌的種群結構也不相同。藥用植物連作后,內生細菌、放線菌和真菌的結構發生了改變,如川明參連作后土壤根際真菌菌落數增加、放線菌和細菌數量減少,植物內生真菌、內生放線菌數量增加,內生細菌數量減少[18]。由此可見,藥用植物連作后共生結構的變化引起植株生理、生化代謝及生長過程改變,是連作障礙發生的重要因素。
2.5 其他因素
土地高度集約化利用現狀下,過量使用氮肥使土壤產生次生鹽漬化和土壤酸化,也成為連作障礙的重要原因,部分可以通過客土的辦法解決,但需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其成本也較高。此外,單一品種長期連作,忽視了均衡施肥導致土壤中某一元素的缺乏也會引起連作障礙。
綜上可見,連作問題是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見圖2)。雖連作障礙中不同時期不同土壤條件下各種因素所造成的抑制程度不盡相同,但植物微生態系統的失調,可能是連作障礙發生的主要原因。首先,植物生長中向土壤排泄(淋溶或根分泌)了大量的物質,其中可能包含自毒物質;根系分泌物可誘導厚垣孢子、卵孢子和菌核的萌發,以及休眠菌絲的活化,刺激線蟲等害蟲卵的孵化,引起蟲害增加。其次,根系分泌物不僅為根際微生物提供所需的能源,而且不同根系分泌物直接影響著根際微生物的數量和種群結構,這些微生物分解植物殘茬產生大量分解產物,一方面繼續影響土壤微生物的種群結構,另一方面也可能部分為自毒物質,這些物質一直持續到下茬植物生長周期或更長。多年連作情況下,土壤中已積累的和當茬分泌的自毒物質會抑制植物生長。

圖2 連作障礙發生的微生態過程示意圖
同時根系分泌物可能刺激土壤有害微生物增加,土傳病蟲害加重,作物根系分泌物和植株殘體腐解物給病原菌提供了豐富的營養和寄主,從而使病原菌數量不斷增加,而有益細菌的種類和數量隨著連作年限的增加而減少;機會致病菌和土壤線蟲等浸染植物,導致植株生長受到抑制,產量降低等連作障礙現象。
3 連作障礙的防治策略
藥用植物微生態系統是由植物—土壤—微生物及其環境相互作用形成的特殊生態系統,協調三者的關系可能是解決連作障礙問題的關鍵。連作障礙“起因于生態失衡,要終結于生態平衡”這是中藥連作障礙微生態防治的中心思想。目前連作障礙的防治通常采用生物措施和化學調控的辦法加以解決,其中化學防治措施是植物本身,而生物防治措施則是通過調控植物共生體系與其生長環境來減少連作障礙的危害,與其他措施相比微生態調控措施的優勢更為明顯。目前主要的防治措施有:
3.1 利用抗病品種和嫁接技術
抗性育種是解決中藥連作障礙問題最有效、最經濟的途徑,但至今沒有發現對再植病有全面免疫力或較高抗性的品種。此外,可利用嫁接的方法來防治根系病害,如通過嫁接減輕了設施黃瓜連作障礙[19]。根分泌物組成和含量的變化是不同生態型植物對其生存環境長期適應的結果,特異性根分泌物作為一個重要的遺傳性狀,在植物營養遺傳改良中已受到人們的日益重視[20]。因此藥用植物的育種中應關注抗性品種的選育。
3.2 接種微生物
化學農藥對連茬土傳病害防效差,尋找新的防治途徑已成為相關研究者面臨的重大課題。連茬種植土傳病害防治的經驗教訓啟示:連茬種植土傳病害:“起因于微生態失衡,要終結于微生態平衡。”利用拮抗性微生物,通過“以菌治菌”的生態學方法控制土傳病害是一種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思路。目前針對大豆根腐病篩選出了病原菌拮抗菌株[21]。可見,篩選有益菌,人工大量繁殖有益菌,將有益菌接種到作物根區,抑制病原菌生長繁殖,調整失衡的微生物生態,將病害降低到不影響生產的程度。
3.3 降解作物自毒物質
自毒物質是引起植物生長受限的主要因素,采取微生物技術,將根系分泌、作物殘體腐解形成的有毒有害物質分解掉,解除自毒物質的抑制作用[20]。如何利用有益微生物的分解機能消除自毒物質、解決自毒問題是目前正在進行的課題,也是連作障礙防治技術研究的熱點。
3.4 物質調控
化學調控包括元素補給和生長調控兩方面。植物對某些元素具有富集性,長期連作易造成缺素癥,針對性補充單一種植造成的某種營養元素的缺乏,有利于緩解障礙的發生。同時,連作障礙表現出根系發育不良的情況,采用植物生長調節劑調整植物株型,可增加植物根系生長,能增強植物的抗逆性,減少減產。
3.5 增施有機改良劑
各種土壤生態因子平衡發展是種植出高質量藥材的重要因素之一。土壤增施有機改良劑,改善土壤生態環境,調節土壤酶活性。施生態有機肥能改善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提高連作土壤中微生物群落的代謝能力和功能多樣性,達到控制病害和恢復土壤健康的效果;同時能改良土壤結構,改善土壤微生物的營養條件,提高土壤微生物多樣性,降解有毒物質的積累。
3.6 其他
采用生物農藥、低殘留農藥和間套作在中藥連作障礙防治方面均有一定效果[22]。但實行輪作、輪作休地、休耕等傳統措施,可以從根本上防治連作障礙的發生。
4 展望
化學農藥防治藥用植物連茬土傳病害效果差,生態危害大,同時危及產品安全性,尋找新的防治途徑已成為相關研究者面臨的重大課題。連作障礙防治的歷史經驗教訓啟示:連作障礙“起因于微生態失衡,要終結于微生態平衡。”利用微生態學的理論和研究模式,以“損有余而補不足”,“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為策略,調整土壤失衡的微生態環境,將病蟲害降低到不影響中藥材生產的程度,是中藥連作障礙微生態防治的思想精髓和基本模式。
[1] 苗淑杰,喬云發,韓曉增.大豆連作障礙的研究進展[J].中國生態農業學報,2007,15(3):203.
[2] Dae-Hui Choetal Park Root Development of 2-year old Ginsend Caused by Cylindro-carponde tructansin thecontinuous cultivation field [M].Koren J.Ginsend Sci,1995,19(2):175.
[3] 曹志強,金慧,宋心東.參地土壤改良及永續栽參[J].人參研究,2002,14(1):29.
[4] 喻敏,余均沃,曹培根,等.百合連作土壤養分及物理性狀分析[J].土壤通報,2004,35(3):377.
[5] 魯素云.植物根際生態學與根病生物防治進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208.
[6] 汪立剛,沈阿林,孫克剛,等.大豆連作障礙及調控技術研究進展[J].土壤肥料, 2001(5): 3.
[7] 江修業,王建國,王光華.關于大豆重迎茬問題的探討[M].哈爾濱:哈爾濱工程大學出版社,1995:92.
[8] 朱麗霞,章家恩,劉文高.根系分泌物與根際微生物相互作用研究綜述[J].生態環境,2003,12(1):102.
[9] 陳書龍.農作物線蟲病害防治措施、問題及發展方向[J].河北農業科學, 2005,12(4): 69.
[10] 孔垂華,胡飛.植物化感(相生相克)作用及其應用[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1:125.
[11] 康白,袁杰利.微生態大循環是生命發生發展的根本條件[J].中國微生態學雜志,2005,17(1):1.
[12] 王元貞,潘廷國,柯玉琴.微生物與植物共生關系的研究及其利用[J].中國生態農業報, 2003,11(3):95.
[13] 龐蕾,嚴鑄云,梁俊玉,等.內生真菌在中藥中的應用[J].時珍國醫國藥,2005,16(3):242.
[14] Luis M.Márquez, Regina S.Redman, Russell J.Rodriguez,Marilyn J.Roossinck,A Virus in a Fungus in a Plant: Three-Way Symbiosis Required for Thermal Tolerance[J].Science,2007,315:513.
[15] 嚴鑄云,龐蕾,羅靜.銀杏內生真菌菌種分離及鑒定[J].華西藥學雜志,2006,21(5):425.
[16] 汪楊麗,嚴鑄云,郭曉恒,等.川芎內生真菌的分離與鑒定[J].中國中藥雜志,2008,33(9):18.
[17] 嚴鑄云,張琦,馬云桐,等.不同生長期川貝母內生真菌的多樣性[J].華西藥學雜志,2008,23(5):521.
[18] 萬德光.中藥品質研究——理論、方法與實踐[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288.
[19] 呂衛光,張春蘭,袁飛,等.嫁接減輕設施黃瓜連作障礙機制初探[J].華北農學報,2000,15(增刊):153.
[20] 解文科,王小青,李斌,等.植物根系分泌物研究綜述[J].山東林業科技,2005, (5): 63.
[21] 陳宗澤,王旭明,梁開巖.連作大豆土壤病原菌拮抗菌株的篩選及其生物學特性研究[J].吉林農業科學,2003, 28(2): 35.
[22] 成志軍,趙光輝,肖軍,等.不同藥劑處理對曬黃煙連作田主要病害的防效[J].湖南農業科學,2004, (3):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