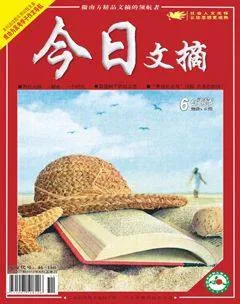反思抑郁
魯伊
你最近總是悶悶不樂(lè),不是晚上睡不著,就是早上起不來(lái);你經(jīng)常沒(méi)有食欲,吃什么都味如嚼蠟,但間或也會(huì)一口氣吃掉一大罐冰激凌;你不想上班,不想完成手頭的工作,不想跟人打交道;你發(fā)現(xiàn)自己總是愛(ài)走神,一整天在電腦前反復(fù)刷新頁(yè)面,卻不知道看了些什么;你開(kāi)始自問(wèn),這么辛苦地活著到底是為了什么,一了百了是不是更好……
如果你對(duì)一名精神科醫(yī)生講述這些癥狀,十之八九,你會(huì)被當(dāng)場(chǎng)診斷為抑郁癥。但是,如果坐在對(duì)面的是埃里克·邁瑟爾,他會(huì)立即告訴你:“去他的鬼扯的抑郁癥。你只不過(guò)是不快樂(lè)!”
邁瑟爾是美國(guó)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名執(zhí)業(yè)心理醫(yī)生和多本暢銷通俗心理學(xué)著作的作者。在他的新書(shū)《反思抑郁》中,邁瑟爾對(duì)現(xiàn)代社會(huì)中的“抑郁癥診斷泛化”現(xiàn)象進(jìn)行了激烈抨擊。
根據(jù)美國(guó)疾病控制預(yù)防中心公布的數(shù)據(jù),9.1%的美國(guó)成年人符合當(dāng)前的抑郁癥診斷標(biāo)準(zhǔn)。在北京進(jìn)行的一項(xiàng)抽樣調(diào)查顯示,15歲以上人群中,抑郁癥終身患病率為6.87%。但在邁瑟爾眼中,被定義為抑郁癥的這種精神障礙很可能根本不存在。“我并不是說(shuō)你所經(jīng)歷的那些痛苦并非真實(shí)存在。我也不會(huì)用一句‘振作點(diǎn)兒來(lái)敷衍了事。我更不否認(rèn)生理上的那些變化,”邁瑟爾寫(xiě)道,“但我想指出的是,當(dāng)下對(duì)這種特定人類現(xiàn)象的命名與診治方法存在根本性的謬誤。”
邁瑟爾表示,生活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中的人們的確面對(duì)更多的挑戰(zhàn),更容易不快樂(lè)。但不快樂(lè)不是一種必須靠醫(yī)學(xué)手段才能解決的疾病。把不討人喜歡、不符合社會(huì)主流價(jià)值觀的那些問(wèn)題定義成疾病,然后指望用某種靈丹妙藥根除這些不想要的特性——內(nèi)向、不合群、效率低下、厭倦工作——這才是最大的問(wèn)題。
邁瑟爾引用眾多文獻(xiàn)指出,對(duì)精神障礙的定義很大程度上受時(shí)代的影響。一個(gè)世紀(jì)以前,人們認(rèn)為不服從丈夫權(quán)威的女性患有歇斯底里癥,不過(guò)十幾年前,同性戀還被當(dāng)成一種心理變態(tài)的反應(yīng)。如今被診斷為抑郁癥的那些人,有多少不過(guò)是不適應(yīng)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冷漠、疏離、復(fù)雜、不確定性和工作壓力?毫無(wú)疑問(wèn),因此而導(dǎo)致的不快樂(lè)會(huì)帶來(lái)一系列生理變化,但這就像在沙發(fā)上呆坐一個(gè)月會(huì)變得肌肉無(wú)力、看一部傷感電影會(huì)讓人流眼淚一樣。然而,現(xiàn)行的抑郁癥診斷標(biāo)準(zhǔn)常常混淆了兩者之間的因果關(guān)系。
“你的手變粗糙了,可能是因?yàn)榈昧似つw病,也可能是因?yàn)槟闶莻€(gè)砌磚頭的泥水匠。抹點(diǎn)藥膏可以緩解粗糙的癥狀,不管這癥狀是怎么引起的。”在邁瑟爾看來(lái),近20年來(lái)大行其道的抗抑郁藥就像是潤(rùn)滑皮膚的藥膏——對(duì)一部分“抑郁癥患者”確有立竿見(jiàn)影的效果,但卻無(wú)法從根本上解決問(wèn)題。2001年的一項(xiàng)大規(guī)模研究顯示,抑郁癥患者停止服用抗抑郁藥物一年后,復(fù)發(fā)率高達(dá)80%,但接受認(rèn)知行為療法(一種心理治療手段)的患者復(fù)發(fā)率僅為25%。此外,2010年1月發(fā)表在《美國(guó)醫(yī)學(xué)聯(lián)合會(huì)雜志》上的一項(xiàng)研究表明,對(duì)于輕到中度抑郁癥患者,抗抑郁藥的作用與安慰劑并無(wú)分別。更重要的是,已經(jīng)有大量研究揭示了抗抑郁藥物的種種風(fēng)險(xiǎn):嗜睡,體重增加,自殺傾向……
在邁瑟爾看來(lái),對(duì)于絕大多數(shù)人來(lái)說(shuō),拒絕“抑郁癥”這一病理定義是通往建設(shè)性解決方案的第一步。關(guān)注不快樂(lè)本身,尋找非藥物的解決辦法——多和家人朋友聊聊天,多出門走走,甚至哪怕是換一份工作。因?yàn)椋八幬锘蛟S可以‘治療你的抑郁,但不能治療你的人生”。
(龔光坪薦自《三聯(lián)生活周刊》)
責(zé)編:katsu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