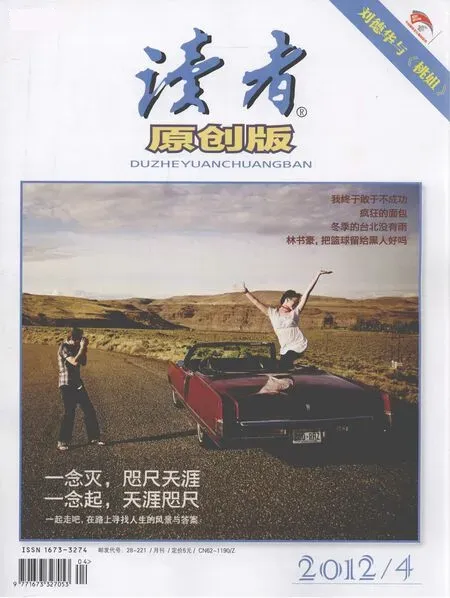瘋狂的面包
文 _ 王瑩瑩
這里是位于北京市朝陽區黑莊戶鄉蘇家屯的一家精神病托管中心,它隱藏于安靜的村莊中。紅色的大鐵門緊鎖著,出入需要登記,因為這里的病人都處于精神疾病康復期,仍然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礙、分裂乃至缺損。
院內非常整潔,四四方方的天井,陽光暖融融地灑入。基本每天上午,病人們都會在院子里做早操,接受種種康復訓練,比如零件組裝、食堂幫廚,還會學習刷牙、洗臉、穿衣等基本生活技能。
上午9點半,多數病人已經回到房間里休息,整個小院安安靜靜的,但是有一個角落卻格外忙碌。伴隨著陣陣喧鬧聲,滿滿一爐面包新鮮出爐,那來自生活的濃香如同陽光,不偏不倚地溫暖了這個偏僻的角落。
我們這里有點不一樣
娜塔莎和伊萬早已經到了面包制作間。操作臺上擺著幾個大簸箕,里面盛著數十個新出爐的面包。
這里一共有5位面包師,他們的另一個身份是精神病患者,但此時此刻,看不出他們有任何異樣。從早晨6點鐘到現在,大家一共做出69個德國麻花。根據娜塔莎帶來的訂單,大家先把面包一一裝進紙袋,然后把訂戶信息寫在袋子上并仔細核對姓名、電話、住址、面包品種等,最后再封上面包標簽——CrazyBake。
Crazy在英語中只有一點點精神病的意思,更多的是瘋狂、激情,好的意思居多。伊萬解釋道,這個名字很好,很像我們!
伊萬是瑞士人,說話快而有力,1994年跟隨中國丈夫來到北京。十幾年來,她的西方式獨立與中國式傳統漸漸取得一種平衡,同時她也從一名心理醫生成為精神疾病志愿者,日子過得堅定而明朗。
娜塔莎是一名德國家庭主婦,有3個孩子。相比伊萬,她顯得安靜而溫和。自從開始做 瘋狂面包 ,她的生活就忙碌了許多,不僅要教患者們做面包,還負責送面包。比如今天是星期五,她要送50多個面包,從早上11點出發,真正回到家里休息,恐怕得到下午4點鐘了。
隨著物價上漲,瘋狂面包 的售價也從每個15元漲到25元,但相比北京的其他外國面包,這個價位只是中檔。春節期間,伊萬回瑞士探親,驚訝地發現中國的面粉、白糖、雞蛋、食用油居然比瑞士還貴。怎么可能? 她到現在也不明白。除了物價,她不明白的東西還有很多。比如,8年來她們一直試圖找人幫忙送面包,但總是沒有人答應,大家都說 我很忙。所以直到今天,瘋狂面包 基本都由伊萬和娜塔莎完成每周兩次的送貨上門。北京的天氣陰晴不定,烈日、狂風、驟雨、沙塵暴……這些都沒有影響面包的送達。
懷孕期間,伊萬照樣挺著大肚子教大伙做面包,生完小孩才兩周便用提籃提著寶寶來面包房工作。娜塔莎也一樣,懷孕、生育沒有耽誤面包房一天的工作。孩子學習爬行時,就在面包房里滿地爬。“她們真的很了不起!”護士長楊云說,并且調侃,“她們和我們不一樣,身體也不一樣。”
“怎么不一樣?”伊萬大聲糾正,“身體一模一樣,只是想法不一樣。”
誰比誰更瘋狂
的確,不同的想法決定了不同的人生。
伊萬在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心理學專業畢業后,成為一名心理醫生。因為長期與精神病患者接觸,所以伊萬來到北京后也自然而然地走入精神病患者這個圈子,并與他們交上朋友。“剛開始在醫院里接觸到患者,有時我晚上回到家里會哭,”伊萬說,“因為我感覺自己的生活太好了,我有丈夫,有孩子,有住房。可是他們什么都沒有……”
娜塔莎的先生也是一名精神疾病工作者,受國際殘障組織的邀請,來到北京精神病托管中心教授英語。為了幫助患者恢復勞動能力,他們在托管中心開辟了一個菜園,帶領大家一起種菜,但種菜受季節限制很大,如何幫助大家實現有規律的、持續性的勞動?他們想到了做面包。
“剛開始提出這個想法時,患者覺得我們比他們還瘋狂。”伊萬說,“他們從沒做過,也沒有興趣學,更認為沒人會買他們的面包。”
“因為他們很多年沒干活了,認為自己是病人,是來休息療養的,怎么可以干活呢?”楊云說,“但我覺得非常好,因為手指運動對他們的大腦恢復非常有幫助。”于是她開始做大量的說服工作。
盡管質疑聲不絕于耳,娜塔莎還是向親朋好友發出郵件,希望獲得愛心捐助。50歐元、100歐元……她們共收到近20筆捐款。于是大家把托管中心的一間舊廚房改造成面包操作間,購置了兩臺大型烤箱,還定做了操作臺及基本工具。伊萬還找到一位設計師朋友,在一小時內完成了“瘋狂面包”的標志設計,“因為他只有一小時是免費的,容不得我們有太多思考。”
隨著“瘋狂面包房”雛形初現,一些堅決反對的患者也終于同意試一試。你可以設想那時起步的艱難:和面、醒面,學習如何加入黃油、如何刷雞蛋、如何掌握烘烤時間及溫度……即使是能夠熟練做饅頭的楊云也不得不承認:“做面包比做饅頭難幾十倍。”
以最簡單的德國大麻花為例,四股面如何漂亮地編織成形且不黏滯,如何均勻地刷上蜂蜜、蛋清……剛開始的產品總是失敗的,要么烤煳了,要么硬得像石頭,但伊萬和娜塔莎總是鼓勵大家:“還好,還好!”當然有顧客抱怨。每每此時,娜塔莎只好笑著說:“這次免費好了,下次我們送給你更好的。”當然,這樣的打擊她們沒有告訴患者。為了避免浪費,她們始終保持以銷定產的訂單方式,同時,出于對品質的考慮,她們把面包的產量定得很低,哪怕一天只做幾個。
關于贏利,她們不會考慮太多。因為做“瘋狂面包”的目的不是銷售,而是通過手指與四肢的運動幫助病人恢復健康。所以在面包制作過程中,除了教授,她們更重要的一個工作是觀察病人的情緒,每當碰到病人情緒焦躁,她們會立刻讓他停下來休息。
石師傅是一名嚴重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從“瘋狂面包”成立起便一直在面包房工作,當然中間也有數次犯病的時候。有一次楊云發現他怎么也團不好面團,情緒越來越緊張,差點和旁人打起來,于是強迫他停下來。休息治療一段時間之后,石師傅找到楊云說:“護士長,我還想做面包。”
高興從里面來
終于,他們喜歡上了做面包。
終于,“瘋狂面包”越來越漂亮、香甜。在日復一日的規律勞動中,這些精神病患者也漸漸建立了自我認知,不僅意識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而且也建立起自己是個面包師的自我認知。“當這兩種認知同時存在時,他們便建立了社會責任感。”楊云說,“這個認識是病情恢復非常重要的指標。”
2007年8月,利用“瘋狂面包房”的贏利,娜塔莎和伊萬在托管中心附近租了一處獨幢別墅。托管中心經過專業的衡量,認為幾位面包師恢復良好,可以出去生活了。搬家那天,大家一起熱熱鬧鬧地去市場買來水盆、水桶、鍋具、飯碗……一起去菜場買菜,一起擠在廚房里做飯。“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喜歡什么就買什么。”一位患者快樂地說,“真是太棒了!”
石師傅的弟弟一直在德國生活。因為牽掛哥哥,他總是定期過來探望。最近一次探望,他驚訝地發現哥哥變了許多,不再像以前那樣懶散了,暴力傾向也減輕了許多。臨走時,他買了一個“瘋狂面包”,嗅著哥哥親自烤制的面包,他開心地告訴楊云:這是我離開時最欣慰的一次。
從2004年至今,瘋狂面包 已經瘋狂 傳遞8年了。8年時間,在浩瀚的北京城里可以發生多少事情?但是在 瘋狂面包 的操作間,娜塔莎和伊萬始終以志愿者的身份手把手地教會一個又一個精神病患者做面包,并且開著小貨車、踩著自行車風雨無阻地穿行在北京的車水馬龍中,把 瘋狂面包 一一派送出去。又或許,這不僅是面包,更是一份濃濃的關愛。
許多人覺得她們瘋狂。但什么是瘋狂?伊萬用力揮了一下手,說:我們一點也不瘋狂,我倒感覺花那么多錢買一輛捷豹的人更瘋狂!而娜塔莎的解釋是:因為我們生活得很好,我是一個家庭主婦,不是很忙,又不喜歡做美容、做頭發,那么就幫助大家做面包好了。
這樣的理由簡單得令人失望。或許公益真的不需要煽情的理由,不需要背負宏大的使命,或許公益就是量力而行、身體力行、舉手之勞。
作為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伊萬和娜塔莎注意到中國人的房子越來越大,車子越來越高檔 可是大家真的高興了嗎?她們時常懷疑。什么是高興?發自內心的高興才是高興,如果你的生活好了,你應該去幫助別人,讓別人也好起來,只有這樣你才會高興。伊萬說著,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因為高興是從里面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