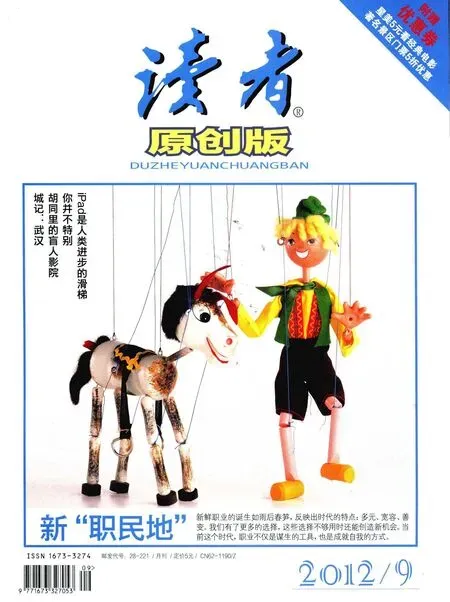武漢的市井
文 _ 南在南方
一個朋友說,武昌是個火車站;另一個朋友說,漢口也是個火車站。挺有意思的兩句話。對于旅人,許多時候武漢是用來路過的,是北上或者南下繞不開的一座城。
長江帶著許多河流奔涌至此,像是迎接;漢水帶著許多河流奔涌至此,像是投奔。然后,相攜滾滾東去。
一個城市有兩條大江,或者說兩個流域滋養著一座城,武漢像是得了上蒼的眷顧。長江把江南劃成漢北和武昌,漢江再來把江北劃成兩片——漢口、漢陽,武漢三鎮就有了輪廓。
在南岸嘴,看漢水入長江非常有風情。它們都不舍晝夜奔流而來,大敞襟懷,像赴約會。交匯處,長江半迎過來,漢水半撲過去,搖擺出一道半明的水線,豐盈時尤其好看,這城立馬陷在嫵媚里。此外,高山流水知音相遇的古琴臺和楚辭的韻歌又給這座城打下了溫軟的底色。
沿著水岸,時有碼頭,硬朗,還有著名火槍 漢陽造 ,又給這城添了剛硬。
滿街的小吃,公共汽車上是端著早餐并且能夠滴水不灑的男女老少,隨處都有的生意,又帶給這座城市一種入骨的市井味兒。
我喜歡這城市的市井味兒。市井 不是讓人生厭的詞,就是活生生的生活、活生生的人情。
我從陜西來,在這座城市里待了很多年。很多時候我喜歡西安的方正,喜歡那里老大一碗面條,更要緊的是從那里出發幾個小時就能回到老家。可離開武漢,我聽到武漢話卻感到莫名親切,下意識地動一下喉嚨,像是有芝麻醬的香氣。如果不及時收住想法,眼前還會出現很多食物,離垂涎三尺不遠了,很不雅觀。
也許一個地方能讓人留戀,味蕾的記憶是差不了的。武漢小吃眾多,總結出四大名吃:老通城豆皮,小桃園煨湯,蔡林記熱干面,四季美湯包。都是老店,并且相距不遠,我曾有幸坐在這四家老店里吃了個美。之所以說有幸,是因為除了小桃園之外,其余三家都已相繼拆了。
說到煨湯,食材眾多,最好的還是排骨藕湯,湯汁如藕色,恨不得用上國色天香來形容了。有朋友喝過之后,請教師傅如何煨得這般好湯,答曰:很多地方的蓮藕都是11個眼兒,食之清脆,獨楚地有一種藕只有9個眼兒,短圓,食之粉面。朋友買了粉藕回家,也肯下工夫,文火煨了五六個小時,湯色暗紅,藕也暗紅 原來,他少了陶罐,藕待在鐵鍋里不變紅才怪呢。另外,得有幾根棒骨增加湯的潤澤。前一陣兒《舌尖上的中國》里提到湖北藕湯,一老頭兒撇嘴說,那一鍋暗紅藕湯,實在掉底子。掉底子 是方言,意思是丟臉。
擁著兩江,自然少不了魚。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 ,這句詞讓武昌魚成了名魚。其實,這魚自古就有名氣,唐代詩人岑參寫過 秋來倍憶武昌魚,夢魂只在巴陵道 的詩句。吃過很多魚,似乎味道差不多,這自然要遭美食家的反對,大約我跟李逵類似,他在潯陽樓上說:這宋大哥便知我的鳥意!吃肉不強似吃魚? 后一句甚合我心。一次在巷子里看一老頭兒吃三寸長的小魚,吃得屏聲靜氣,旁邊放著骨架,像是標本,大為艷羨。
這大約與武漢人的性格有關吧。不似上游成都的閑適,不似下游南京的安穩,武漢不慌不忙,不要多快好省,一天就當一天過,但它依然充滿了夢想。如同英國作家伊恩·麥克尤恩所說,一部小說和一座城市之間存在著某些相似之處。小說不僅僅是一本有封面有內頁的書,它還是一種特殊的精神空間、一個考察人性的所在;城市也不僅僅是建筑和街道的聚合,它是一個夢想之地。
早晨,我經過一條小巷子。小巷子總是熱氣騰騰,揭開籠蓋的包子的小麥味,剛下鍋的油條眨眼工夫膨大,泛著紅油的米粉好像暗示我這是好的一天。然后,我走到車站,等到一輛車,開過漢水橋。早晨的江面安靜,陽光灑在上面,并不動蕩。等到下班回來,看著江面,卻是漂亮的床單,讓人有些倦。
時常和妻兒去江邊轉一圈,陪朋友走一回長江大橋,偶爾到歸元寺聽晨鐘暮鼓,去長春觀吃一回素餐。這般庸常的生活,實在再舒心不過。
有個朋友想來武漢工作,問我武漢到底如何。我跟他說,這城市熱情得像一位嫂子,只要你想留,她必然收留你。如同城里常常可見的湖面,它映照你的面容、你的愿望,它有機會要給你。如果這里鋪不開你的理想,北去北京,南下廣州,方便極了。如果想浪漫,順江而下就到上海啦。再遠一點,就是太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