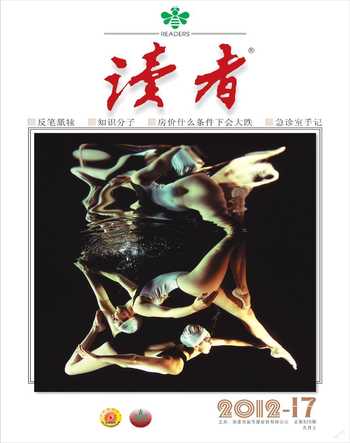排場與器識
清風慕竹

公元28年,盤踞在天水的軍閥隗囂不知道是該投靠在洛陽登基的劉秀,還是在成都稱帝的公孫述,便派馬援為使者,去近距離地觀察誰更有帝王氣象。
馬援先奔了成都,因為他和公孫述既是同鄉,又是“發小”。在他的想象里,兩人見面后雖不至于“執手相看淚眼”,但也一定會分外親熱。然而,等待他的卻是另一番場景。
公孫述身穿耀眼的龍袍,高坐在金鑾寶殿之上,兩旁武士林立,戒備森嚴。禮賓官引導著馬援,依照宮廷禮節參拜,沒說上幾句話,就將他送到賓館休息。公孫述下令給馬援趕制布質的平民服飾,隨后,在皇家祖廟中召集文武官員,并命人在皇帝座位旁邊特別設置老朋友的座位。等到一切就緒,公孫述的御駕才從皇宮出發,盛大的皇家衛隊之前,由天子專用的繡著鸞鳥的旗幟、驅逐妖邪的騎士作為前導。全城戒嚴,公孫述在御車之上,不斷向左右屈身恭迎的官員點頭示意。之后開始的宴席與文武百官的陣容都極為盛大。
馬援的隨從們還從沒見過如此大的排場,瞪大了眼睛,臉上寫滿羨慕之情。公孫述對老友還是很夠意思,當即要封他為侯爵,擔任大司馬。馬援的隨從們大喜過望,馬援卻笑著說,他還有使命在身,當官的事以后再說吧。
馬援的第二站是洛陽,劉秀的實力遠在公孫述之上,他不知道這個皇帝會弄出什么把戲。等了很長時間,才來了一個宦官引導他入宮,既看不見威風的武士,也見不到助陣的大臣,甚至劉秀連工作服——龍袍都沒穿,僅用布包頭,像接見一個多年不見的老朋友般,在宣德殿走廊下笑臉相迎。
馬援說:“我跟公孫述是同鄉,自幼交好。可是我到成都時,公孫述高坐在金鑾寶殿上,戒備森嚴,然后再傳喚我進去。現在我遠道而來,陛下怎么知道我不是刺客,竟這樣簡樸地跟我見面?”
劉秀笑著說:“你不是刺客,只是一個說客。”
兩人相顧大笑。
劉秀說:“先生遨游在兩個皇帝之間,今天看到你,我很慚愧。”
馬援拜謝道:“這不奇怪,當今之世,不但主上選擇臣子,臣子也選擇主上。”
劉秀深為贊許,對馬援也非常賞識,大有相見恨晚之意。馬援在洛陽待了很長時間,劉秀接見他數十次,每次談話都非常輕松,有時竟會從早談到晚,沒有絲毫厭倦。
第二年,馬援回到天水,隗囂詢問他的觀感。馬援回答說:“現在天下一片混亂,勝負未定,公孫述不知道‘一飯三吐哺,不急切地招募天下的人才,排場雖大,器識卻小,我看他不過是井底之蛙,似一個人形玩具罷了,不會有什么作為。劉秀不拘小節,對人開誠布公,不高高在上耍弄皇帝的威嚴,我看他心胸坦蕩,器識宏大,前世君王沒有人能跟他相比。”
公元36年,公孫述兵敗身死,劉秀卻復興了漢朝,史稱“光武中興”。
當一個人需要外在的排場為自己撐起臉面和威嚴時,排場越大,越顯現出他的器量狹小和見識短淺;而越是能謙卑地低下頭顱的,背后所蘊藏的,往往是恢弘的器量和深遠的見識。宋代學者劉摯說:“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個人的器量與見識,決定著其成就的大小,甚至事業的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