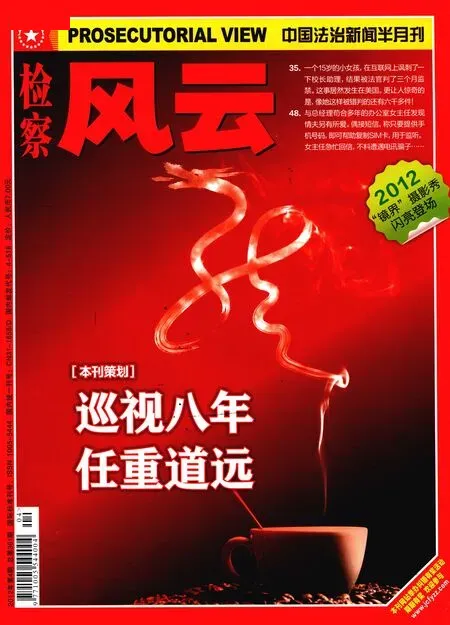“乞討村”背后的故事
文/馬進帥
“乞討村”背后的故事
文/馬進帥

他們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在城市的繁華地帶都能看見他們的身影,車站、廣場、天橋、地下通道……更是經常的聚集地。
他們的名字叫乞丐。
利益催生乞討職業
沉寂了一段時間后,在甘肅蘭州的大街小巷、馬路邊、商場門口、小吃市場、中高檔酒店門口等,不時能見到一個個跪在地上乞討的婦女,有老有小,年齡參差不齊。
據了解,這些乞討者大都是來自西北某縣,不光在蘭州,他們的腳印已踏遍全國各地。
西北某鄉是有名的“乞丐鄉”,這里的人們大多都有過外出乞討的經歷。
為什么會形成這樣的現象?是什么原因讓他們背井離鄉走上了這條為常人所不齒的道路?帶著這些問題,筆者日前經過連續跟蹤、觀察并走近他們,對他們的生活及他們的靈魂深處,進行了一次全面而深刻的揭示,逐漸揭開了這個乞討族神秘的面紗……
偏僻落后的西北小村(化名)成了全國各媒體關注的焦點,是因為一個令當地人羞于啟齒的現象——乞討。
盡管如此,乞討似乎成了這些人的生存習慣和手段。
在城市流浪乞討的人群,他們流浪乞討的原因是多樣的,但這些乞討團的目的卻很純粹,他們的回答十分簡單——我們就是來掙錢的。雖然他們長相不一,討要的手段也千變萬化,但他們給人留下的印象卻是一樣的,他們已成為一個符號——磕頭伸手。
在人們的印象里,乞丐大多是老弱病殘、衣衫襤褸,因生活所迫才不得已走上乞討之路。然而,當下穿行在蘭州街頭的乞丐卻大多是四肢健全的中年婦女、孩童和老人。
蘭州究竟有多少乞丐,恐怕無人能做出精確的統計。但不能否認,這個特殊的群體似乎無法再用弱勢去界定,利益的驅動至少讓他們無法拒絕伸手討錢的誘惑。
在討要前,這些乞討者總會刻意偽裝打扮一番,然后在街頭巷尾四處漂泊。當他們拉著路人的衣角,伸出像炭一樣黑的手時,眼里流露出的神情似乎無比復雜。乞丐幾乎逐漸成為一種職業化、幫派化的集體,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已經成為了一種職業。他們拒絕被政府救助,拒絕被敏感地盤問。
而這些職業乞丐,無一例外地把孩子當成了討要的工具。當大多數同齡的孩子們正在學校里汲取著知識的營養,享受著童年的無限快樂時,這些孩子卻為生活而放棄了尊嚴四處奔波,讓本應美好的童年在大街上乞討中度過,直至長大成人。
乞討所受到的道德壓力越來越小,對于大部分乞丐來說,乞討不再是不得已的“活命”手段,而是成為與打工、種地一樣的致富手段。在他們中間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城里磕頭,回家蓋樓。”這實際上是他們價值觀最直接的體現,因而他們的討要方式也變得五花八門,各盡所長。
他們討要的背后也有很多行規,比如,絕對不準在自己所住的地方行乞,無論在外邊如何的臟,但回到住所必須穿干凈衣服,洗干凈臉,堅決不準和非行乞人員說話過多(包括說假話)。他們每個人也都是通信員,如果其中一人遭遇意外,其他人則迅速奔走相告。
謊言和貧窮并不是真正的討要理由,他們大部分的境遇并非是悲慘的。他們家庭的生活現狀,以及其真偽和現實的精神狀態到底如何?
別跪了,站起來活出尊嚴
2011年10月18日,筆者從蘭州乘班車出發來到了西北某縣,休息了一個晚上后,在第二天再乘車從縣城向西南方向行駛一個小時,然后順山溝再步行一個小時,就是被外界稱為“乞丐村”的小村。再走五公里上到半山腰,就是外出乞討人員最多的水村(化名)。
這里除了溝邊樹影的緩慢移動能證明時間在推移外,時間在這里幾乎是停滯的,毫無意義的。土坯房和磚瓦房夾雜著,錯落有致而又局促地擁擠在半山腰上,村口幾個老人蹲在地上默默地抽著旱煙,個別人家的臺階上坐著無所事事的大男孩。
蘭州究竟有多少乞丐,恐怕無人能做出精確的統計。但不能否認,這個特殊的群體似乎無法再用弱勢去界定,利益的驅動至少讓他們無法拒絕伸手討錢的誘惑。
這里像一個被遺落在大山深處的棄兒,只有一條狹長而破敗的土路,顯示出它與遠方的現代文明還沒有完全失去聯系。這里既貧瘠又富有、既落后又先進、既寧靜又喧鬧……似乎是個復雜的矛盾結合體。
“這里家家戶戶都有衛星電視天線,幾年前就有人安裝了,能接收上百個頻道呢!”村民常彥虎的語氣中帶著得意,但又摻加著一點警惕。
的確,每走進一個院落,無論房屋好壞,在院子角落,或者房頂上,都有一個直徑一米大小的衛星電視“鍋”。摩托車在村內幾乎得到普及,即便在一些土坯房院內,也會停著一輛摩托車。在小村中部的一條商業街上,“中國移動小村指定專營店”的牌匾分外醒目。“小村幾乎每戶村民家中都有一人或幾人有手機。”專營店工作人員稱。不過相比小村,水村多少顯得有些蒼涼,盡管如此,但站在半山腰放眼看去,被包裹在綠樹中間的村落并不冷清。
在一戶村民家的房頂上,幾位村民正在加緊鋪蓋新的瓦片。旁邊堆放的是被拆下來的腐朽木椽和瓦礫。一陣風過后,灰土騰空而起,遮蔽了現場。“等會再蓋吧,休息會!”一老者笑臉相迎。緊鄰的另一座土坯房,三四個人站在還沒拆完的房頂上,高舉大錘拆著房子。而在不遠處的小村,村民李義家的二層洋樓里,上初中的女兒正在上網聊天。時代好像與這里的人開著玩笑,花花綠綠的“現代化生活”信息瞬間可得,可在當地,提倡種藥材、種馬鈴薯致富的做法似乎無法讓村民們的錢包迅速鼓起來。
當地的整體致富途徑,遠遠被全球化的信息傳播速度甩在后面。而正是在這種“心急”的心理狀態下,整個小村幾十年“乞討傳統”的積淀,直接影響了“丐幫”的形成。深厚的“乞討文化”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仍然在村民們的心里牢固地植根。在水村,已經有一半的討要者被多次遣返。但包括村領導常玉合以及普通村民,無一例外都將外出乞討的原因歸結為兩個字——貧困。盡管沒有一個人愿意承認,但討要來錢快是他們最大的誘惑。“說實話,乞討比種莊稼輕松多了,而且來錢還快。”包相中說。
在小村村口“掀牛”的老人說,如果是討要的“淡季”,能看到另一番景象:很多窗口里會傳出搓麻將的嘩啦嘩啦聲,有些窗口會傳出卡拉OK的歌聲,很囂張的音量。如果舉辦摩托車比賽,很多人都喜歡把摩托車騎出來,即使只是從村東頭到村西頭。小賣店里的啤酒白酒賣得飛快,不像現在小賣店里最繁忙的只是村里僅有的幾部“能打長途”的電話——多半是外出乞討的人向家人“匯報工作”。其實多數村民每年最多出去三四十天,“夏天跑東北,冬天去南方,兩頭不受罪”。在他們看來,能依靠討要弄回三五千元,保證家里一年的基本生活,就很知足了,剩下的時光更多靠玩牌打發。不過像賈玉科這樣長年都在外帶孩子乞討的人為數不少,他們出門前大都約好同伴,組成一個團體相互照應。
隨著時間的推移,嘗到甜頭的乞討者認識上也發生了轉變,乞討者幾乎由少數到多數,由全村到全鄉,成為了當地人一種謀生的手段。
無論是在小村還是水村,情況大體相似,有70%的人有過乞討經歷。
當地村民們說,他們也嘗試過通過自己的勞動掙錢,出去打工,但最后得到的結果往往不是被黑老板所騙,就是收入很少,除去路費也就所剩無幾了。同時不愿打工的原因還與村民們普遍缺乏一技之長,只能靠雙手出賣勞力有關。
政府的根治與尷尬
對于已經把討要作為生存職業和手段的乞討者來說,他們帶給當地政府的不僅是尷尬,更是無奈。即使是政府產業的調整,扶貧政策的傾斜,仍不能阻擋他們討要謀生。在日漸職業化的乞討團面前,政府的根治手段似乎是徒勞的。或許需要解決的并不是讓這些人富起來,而是如何真正轉變已經扎根他們心底的討要觀念。
經過多天的采訪,筆者得到了一個答案,小村人乞討的真正原因不是貧困,而是乞討已成為他們的習慣,討要思想已扎根在他們的心里。慣于乞討的人,成了村里先富起來的人,對那些拒絕討要的家庭,構成了某種潛在的挑戰,甚或嘲笑。
在小村,那些沒有過乞討史的家庭有時候也會表現一下優越感,只是這樣的優越感流露得非常有限。包海忠曾是小村的村支書,家里的條件看起來比普通村民好一些,但還是不如靠討要致富的人家。包海忠20多歲的兒子說:“我們家就沒想過出去討要,丟不起那人。現在這樣不也挺好嗎?花正常勞動掙的錢,心里踏實。”
相比討要的家庭而言,他們有些尷尬,雖然偶爾可以對討要現象說幾句風涼話,得到心理上的優越感,但是眼看著人家個把月就掙回幾千塊錢,內心還是有些掙扎的。
探究這些村民堅持不討要的精神力量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沒有人會對自己的堅定做出精神層面的解釋。比如,沒有人會拿這片古老土地上傳統文化的積淀來說事,沒有人能說出“不為五斗米折腰”之類的典故,也沒有人把討要生活和“不勞而獲可恥”聯系起來。
一個人是有靈魂的,一個村子也是有靈魂的。而小村人的靈魂已經因為村民對尊嚴的踐踏變得卑微了。這種跪著生活是沒有尊嚴、沒有出路的,僅僅依靠輸血式的救助,也是沒有希望的。小村人必須進行自我精神救贖。但誰才能真正智慧地去挽救這些已經扭曲的靈魂呢?
順著山溝進村,一路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各種勸阻討要的標語,這其中就不乏:“別跪了,站起來,活出尊嚴!”
因為勸阻乞討,小村曾出過一個名人,他就是李玉平。這個畢業于湖北荊州國土資源職業學院的大學生,試圖通過上大學的方法選擇一種腳踏實地的生活。童年的乞討經歷,給李玉平留下了恐怖的記憶。他一度在網上發帖勸阻父老鄉親放棄乞討,他甚至在暑假回家的時候,每家每戶勸說村民不要出去乞討了,但等待他的卻是各種各樣的嘲諷。

“討要經歷很長的孩子,會給心靈留下更多的創傷,或是造成畸變。村里有些孩子一旦和父母生氣,偷出家里的幾百塊錢就敢出走。他們從小形成了一種思維,覺得憑著要錢生活很容易。”小村初中的李平校長為家鄉的前途感到憂慮。
“只能先從教育抓起,只有讓孩子們好好學習,將來考上大學走出去,看看更文明的生活。那也許對放棄乞討有強大的拉力!”李平說。這兩年,當地中小學校在寒暑假前都會進行“禁討教育”,鄉政府甚至希望以罰款的方式阻止村民們外出乞討,但這些措施只是部分地取得了效果,當適合討要的夏季來臨時,還是有村民三五一群甚至幾十個人結伴外出。
按照當地人的說法,比起揭不開鍋的那段日子,小村如今的生活雖然依舊清苦,卻并不至于連生計都難以維系。以李平校長為代表的一些人堅持認為,對村里人尤其是學生進行人格教育,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小村人跪著生活是沒有尊嚴的,僅僅依靠輸血式的救助也是沒有出路的,繼續靠天吃飯?還是難以改變命運。于是李平近乎執拗地相信,只有讓孩子們玩命學習,考出去,小村才有希望。
但實際上,從外界到當地政府,越來越多的人在為使小村人完全站起來而付諸努力,不過現在看來還是一項沒有時間表的工作。
“乞丐村”名聲在外,輿論壓力空前,當地各級政府不得不面對并重視這種乞討現象。可是面對人們日夜浸沒其間的職業化討要風氣,拒絕乞討者不得不承認,自己屬于弱勢的一方。他們的呼吁和勸說總是顯得蒼白無力。
李平回憶說,當時那封《致全鄉中小學生的信——別跪了,小村人,站起來!》曾在鄉初級中學校報《清泉》上發表過,并在校園里引起強烈反響,許多學生紛紛寫作文表達自己的決心:要做個堂堂正正的人,決不向命運屈服,永遠告別乞討的陋習,靠勤勞的雙手創造幸福的生活。李平希望這種用呼吁和教育的方式來復蘇家鄉的尊嚴!
可是現在,這種悲劇還在延續。小村還有很多孩子被父母帶出去乞討。
針對日益嚴峻的乞討之風,縣政府相繼出臺了一些優惠政策和禁討措施。比如,為了改善自然條件,發展經濟,擺脫貧困,縣政府采取將部分村子外遷甘肅玉門就是一條主要的措施。可是,外遷工作開展已有五六年了,效果還是不盡人意。
如何根治小村等村的討要之風,當地政府一直在思考原因,為此也開出了許多良方,甚至還專門成立了由縣長親自負責的“勸討治理小組”。縣委宣傳部一位人士說,政府這幾年為了根治乞討,花費了巨大的財力、人力。不僅如此,為杜絕討要現象,政府一再整合當地的致富項目,籌措資金,通過經濟項目建設,綜合治理,幫助小村群眾改善生活條件,以徹底杜絕外出討要現象。
但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仍然有大量乞討者涌出,流向外面的城市。
小村和水村的人均耕地不足兩畝,僅靠種地來供給他們所需的物質滿足顯得有些單薄。也許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不僅要關心弱勢群體的吃飯穿衣,也要關心他們的尊嚴,關心他們人格的健全和精神上的富有,以及他們內心深處的乞討思想,才是真正禁討的最有效手段。
然而,答案似乎復雜而詭異——這一久負盛名的“乞丐村”,什么時候才能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
編輯:程新友 jcfycx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