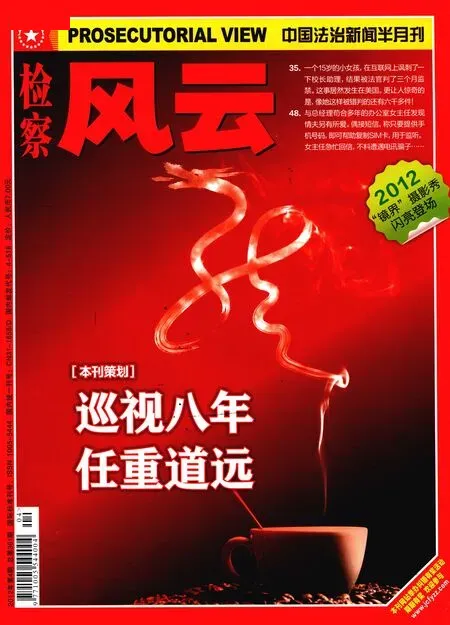天使在人間
文/胡建君
天使在人間
文/胡建君

敦煌飛天
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有四種文化流傳最廣、輝耀古今,即希臘文化、印度文化、伊斯蘭文化和中國文化。這四種偉大的文化竟在同一個地方煊赫交匯過,這就是敦煌。敦煌是神駐之地,十六國時樂僔和尚西去求法,路過此地,發現鳴沙山上有普照的佛光,遂在此開鑿了第一個石窟。而敦煌壁畫中無處不在的飛天,在洞窟創建的同時就出現了。
我們在一個大風的日子抵達敦煌。在樊景詩院長和徐建融先生的帶領下,仿佛在遠古的時空中穿梭。從魏晉南北朝走向隋唐宋元,幾乎每一窟都有飛天。這些天龍八部之中最快樂、最長袖善舞的天神們,棲身于花叢、飛翔于天宮,游走在大型經變畫、說法圖中,藏身于窟頂藻井、佛龕、四披之上。想到張大千曾經零距離地描摹過那些夢一般的形象,著實令人羨慕。
飛天有著最美的身體和舞姿、最輕松自由的精神和力量,一剎那彩云飄浮,香花紛落,一剎那又卷起漫天的黃沙迎接我們。在風停沙靜的鳴沙山上,我們分明聽到絲竹管弦的聲音,那些手持箜篌、琵琶、橫笛、豎琴的飛天,似乎從不曾遠離。一只腋下血紅的沙漠蜥蜴好奇地停下來、斜視著我們。我赤腳走近它,俯身按下快門之后,它搖曳著長尾,穿過一片荊科植物叢,倏忽而去了。那樣體迅飛鳧、飄忽若仙,直讓人懷疑它也是飛天的化身。后來聽得附近的人們說,那是沙漠上劇毒的四腳蛇,如果無意中踩到傷害了它,被咬一口幾乎是不治的。玫瑰有刺,情花有毒,那精靈般的美麗生命,卻同時是致命的。
我還曾到過河南的鞏義石窟,見過那些身形清瘦而造型圓滿的飛天。那是北魏皇家開鑿的大型石窟之一,是帝后禮佛的場所,如今人跡罕至。我尚記得第一眼看到那些飛天的驚喜。尤其是第三、四窟中的飛天,有著明暗的光影,翩若驚鴻,婉若游龍,身下圍繞著古拙而精美的裝飾紋樣,如云彩,似水波。那種若行若止的遠古的完美,仿佛與《洛神賦圖》同出一脈。
鞏義處中原腹地,黃河與洛水于此間交匯。當年失意的曹植抱著甄妃生前的金縷玉帶枕,途經洛水,夜宿舟中,遙見甄妃凌波而來,一驚而醒。無限唏噓間,便就著蓬窗微弱的燈光,寫下了那篇千古傳頌的《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的洛水女神從曹子建的文字中走出,神采畢現于顧愷之的《洛神賦圖》中,飄游在那些意象稚拙的驚鴻、游龍、荷花、山水之間,又影印在了鞏義石窟的龕楣之上,如一聲亙古飄揚的嘆息,那么遙遠,不可追尋。

鳳凰傳奇
佛經中,有一種樂伎,叫“迦陵頻伽”,這個琳瑯的讀音是印度古梵文的音譯,意思為妙聲鳥或美音鳥。《慧苑音義》記載:“此鳥本出雪山,在殼中即能鳴。其音和雅,聽者無厭。”誰能抵擋歌聲的誘惑?佛經故事說,當年釋迦牟尼為弟子傳經說法時,迦陵頻伽從四處飛來,環繞在佛祖身邊,且歌且舞,聲情并茂。敦煌壁畫中的迦陵頻伽形象,常作人首鳥身狀,頭戴童子冠或菩薩冠,形似仙鶴,彩羽繽紛,雙腿細長,自在輕盈地立于蓮花或樂池平臺上,有的展翅引頸歌舞,有的抱持樂器演奏,一片歌舞升平的歡喜景象。




我查了一些資料,“迦陵頻伽”這種類飛天的形象其實來源于古印度的神話傳說,與印度音樂的起源一脈,印度人視其為音樂之祖師。傳說在高加索山上棲息著一只神鳥,嘴上有七個音孔,能吹奏美妙的曲調,此曲只應天上有吧。神鳥有千歲的壽命,臨近死亡則進入狂喜狀態,在四周堆集易燃物,于極樂狀態中繞圈跳舞,最后從容投入火中寂滅。不久,在溫暖的灰燼中孕育出一個蛋,進而孵出一只名叫Dipak-Lata的鳥。死即是生,再度輪回。無獨有偶,前5世紀古希臘神話中亦有類似的神鳥出現,即福尼克斯(Phoenix)——鳳凰鳥,到年老時燃火自焚,復從火中再生,這也是我們熟悉的“鳳凰涅槃”的傳說,中原漢代畫像石中也出現過羽人的形象,其傳說故事相類。
身世迷離,不如歸去,歸哪個故鄉?中外學者對迦陵頻伽的起源問題一直眾說紛紜,也有人認為,迦陵頻伽不屬于飛天,飛天亦不與鳳鳥相類,三者歸屬不同。但我固執地認為它們穿越于神話,徜徉于虛空,其自由之體態,歡樂之精神,死生之永恒,同出于一脈,都是真正意義上的自在歡喜的“飛天”。在裝飾紋樣中,特別是金銀器中,真正人身的飛天形象不太多見,或在高古件如簪釵等金銀飾品中偶有見到。但華麗的鳳凰形象,倒是被民間一再使用,并被賦予各種吉祥與喜慶的寓意,深受人們喜歡。
從飛天、迦陵頻伽到鳳凰,感覺一步步從天上走向人間。鳳凰比飛天深入民心,像是天使來到了人間。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清泉不飲,寓意欣喜、安寧和高貴,也是天下太平的象征,古人認為時逢盛世,便有鳳凰來儀。漢代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鳳凰“出于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見則天下大安寧”。在甲骨文中,“鳳”與“風”相同,代表具有風一般無所不在及靈性力量之意;“凰”即“皇”字,為至高至大之意。從而衍生為高潔、美滿的情愛。“鳳兮鳳兮歸故鄉,遨游四海求其皇”,那燦爛的毛羽紛披于紛繁的人間,從此世上多了賞心悅目的良辰美景,更多了因緣際會的傳奇故事。

鳳舞九天與鳳穿牡丹
與龍一樣,鳳也源于圖騰文化,而且是東方各氏族部落圖騰的結合。在《史記·殷本記》中記載了開山祖簡狄吞下玄鳥之卵而生契(殷的始祖)的故事。殷商甲骨文中的“鳳”字,也具備了鳥的特征,看上去就像一只孔雀,有冠,有羽,甚至有端麗的長尾。
人們在鳳凰身上傾注了無數華美的想象與祝愿,如民間“鳳舞九天”、“鳳穿牡丹”等傳統圖案,其中昂揚自信、富貴吉祥的寓意,成為人們最美好的訴求。
清風收藏的銀鎏金鳳凰與燒藍銀胎鳳凰最具有“鳳舞九天”的昂揚意態。鎏金鳳鳥翅羽高舉,神情端莊高傲,卓爾不群,甚至保留著一種野性的不羈之美,鏨工細膩利落。鎏金的過程是將汞、金混合物涂于器物表面,待高溫加熱后汞蒸發、金便留存在器物表面。鎏金的好壞,和金水本身的成色和鎏金層數都有關系。舊時的好器物,如中國畫的三礬九染一樣,甚至有鎏九遍金的,而鎏一遍的工序,可以在A4開本的書上密密麻麻寫滿九頁。汞揮發時釋放的有毒物質,非常折損壽命,如此說來,鎏金的工人也具有涅槃的非凡勇氣呢,雖然他們沒有重生的幸運。
相比之下,銀燒藍鳳鳥更具有一種喜慶祥和的樣貌姿態,更接近世俗人間。藍綠黃褐色的釉彩是燒藍的經典搭配,在我收藏的銀燒藍福建工鳳凰麒麟帽飾上也可見一斑。銀燒藍工藝是13世紀末的意大利工匠發明的,以透明、半透明的琺瑯釉料施于銀胎花紋上,經過500到600攝氏度的高溫多次燒制而成。經過百年歲月洗禮,原先鮮麗的色彩漸漸沉淀下來,脫略浮華,有了蘊藉古典的內斂氣質。
老銀累絲鑲寶鳳凰帽飾也是我的收藏。“累絲”為古代金工傳統工藝之一。是將金銀拉成細絲,然后將其編成辮股或各種網狀組織,經盤曲、掐花、填絲、堆壘等手段精制而成。此件累絲鳳鳥脖頸處鑲一琉璃,琉璃被譽為中國五大名器之一(金銀、玉翠、琉璃、陶瓷、青銅)與佛家七寶之一。《西游記》中的沙僧就是因為打破一只琉璃盞而被貶下天庭的。傳說中最早的財神聚寶盆,也是用琉璃做的,所以琉璃被認為是聚財聚福的財神信物,與鳳凰的吉祥富貴含義也是相得益彰的。

清代福建工銀燒藍鳳凰麒麟帽餓(筆者藏)
“鳳穿牡丹”圖案在老銀飾中的使用更加廣泛。手頭就有好幾件該圖案的老銀小物。那件鑲寶的鳳穿牡丹帽飾鑲嵌的也是琉璃,仿的是藍碧璽,水漾通透。外圍飾以草綠色琉璃珠,用銀絲編串,使簇擁著兩朵牡丹的鳳鳥更具有富麗堂皇的寶氣。另一件帽飾上的牡丹開得華美絕艷,回頭鳳與雀鳥偃仰相對,構圖舒展大氣,儀態萬方。銀鎏金鳳穿牡丹簪子為楊銓老師所贈,牡丹花開正好,鳳鳥端雅嫻靜,構圖飽滿、疏密得當,也是富貴人家的小物。斜刻鳳穿牡丹鎖片是清風的藏品。斜刻工多出于江浙地區,使物象有了明暗與層次,很顯格調。回頭鳳穿行于云霓、山川、草木、牡丹之間,底下甚至有熊熊的火光,帶著涅槃重生的神秘氣息,讓人有《山海經》故事的聯想。
西方的天使與東方的飛天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飛天是佛教的形象,是供養佛的天人。而天使是西方如猶太教、基督教中代表圣潔、良善的上帝的使者,受差遣服侍、信奉上帝的信徒。手頭的 “羽人天使”手鏈是來自美國的古董首飾,大概是上世紀40年代的,天使尺寸僅為2厘米左右。材質為純銀加彩金,背后有品牌標志Gorham 和純銀sterling的標記。“Gorham ”銀器是由藝術品大師Jabez Gorham與 Henry L.Wesbter于1831年在美國羅德艾蘭州創立的品牌。在美國銀器的鼎盛時期,也就是1850—1940年代,Gorham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白宮曾經使用他們生產的銀器。首飾上的羽人天使短發、長裙,氣定神閑,朋友說感覺像我,本來就是我的收藏嘛。真希望像那首歌中所唱的,給我一對隱形的翅膀,無論做天使,還是鳳凰,周游天際,遠離紛擾。
編輯:沈海晨 map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