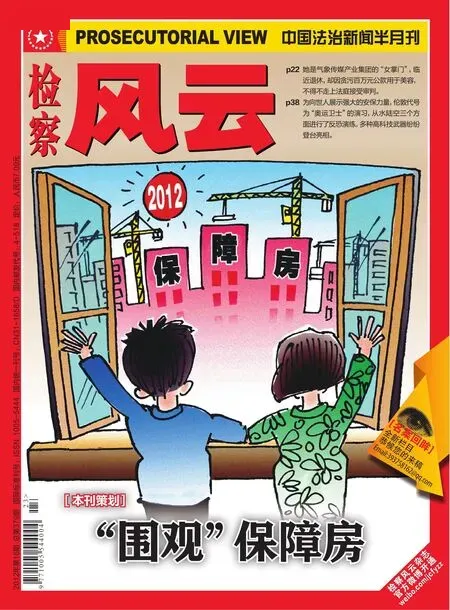運河瓷枕賞析
文·圖/王紅五
運河瓷枕賞析
文·圖/王紅五
瓷枕,是古陶瓷收藏生活用具大類中的一個小門類。過去,由于考古發掘的局限性,墓葬中發現的瓷枕數量很多,曾把它歸為“冥器”一類。因怕忌諱,收藏者不多,近年在被戰火毀滅的古城遺址的床(炕)上也出土了大量瓷枕,才把瓷枕從冥器中界定出來,人們開始關注瓷枕。但歷史的錯誤認識將瓷枕列為“冥器”,著實使它損毀嚴重,存世量也由此減少。
瓷枕作為一種寢室用具,是相當私密的物件,卻始終長伴主人思考與解惑。高古瓷里的瓷枕一類,從形制上先來說,枕面和四面的枕墻上,通常繪刻有大量的紋飾、詩詞、書法和畫片,承載著大量的歷史文化信息,有著豐富的考古研究價值。由于瓷枕上還能體現出不同朝代、不同窯口的工藝特征和裝飾特征,又具有較高的收藏價值,因此瓷枕逐漸成為藏家熱捧的門類。
然我從“運河瓷”中,遴選了一些不同朝代和窯口的瓷枕代表作品,以饗讀者。隋唐大運河博物館(原淮北市博物館)收藏了隋唐大運河柳孜遺址考古發掘的全部文物,是隋唐大運河遺址上,到目前為止唯一出版了正式“考古發掘報告”的一次考古發掘,所以彌足珍貴。出土的一座宋代石砌碼頭,其中發現的八條船只,推測是唐代以前的沉船,現已打撈四條,同時發現大量精美的隋代至元代之間八個朝代的1650件古陶瓷,被文物界譽為隋唐大運河柳孜遺址的“三大發現”,成為1999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之一,本文所選部分瓷枕便來源于該館藏品。
無論是皇家,還是博物館,追根究底,它的藏品都是來自民間、又回歸民間,周而復始,無限輪回。正是:山外山、天外天,博大精深一個緣;緣分在誰誰收藏,這是不可強求的。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文物征集經費不足,故大量精品文物散失在民間,在鑒賞瓷枕時也絕不能忘記采擷這部分民間藏品,它們往往讓人愕然叫絕。
瓷枕賞析

1.唐鞏縣窯三彩十字花紋枕(隋唐大運河博物館藏)
高6厘米 長13厘米 寬12.8厘米
該枕為陶質三彩釉、扁方形。枕面為方形,上刻十字花紋,枕面及四面枕墻施綠、褐黃、白三彩釉,融合自然,有流動感。胎色白中略泛紅、含沙質,為鞏縣窯三彩較為典型的胎質,釉面開魚子紋片,釉色溫潤,做工規整,器型中規中矩,符合唐代陶瓷枕的器型特征,艷而不俗、莊重典雅。收藏界有一俗語“一方等于十圓”,由于方形器制作難度大,因而具有較高的價值。

2.唐鞏縣窯絞胎紋枕
高6.9厘米 長14.5厘米 寬10.4厘米
此枕為安徽省宿州市西關運河遺址考古發掘出土。
長方形,四角抹圓,枕墻上有一圓形氣孔,枕面與枕墻采用絞胎貼面的工藝制作,褐白相間的瓷土疊合絞扭,形成花卷似的兩色相間的紋理,枕面為“團花紋”紋飾,花瓣與花蕊的紋理清晰、規整、自然,體現出了嫻熟高超的技藝功力;枕墻飾以“水云紋”,狀如行云流水、自然典雅,波起浪涌,遐思無窮;絞胎貼面外罩黃色透明釉,釉面及棱角磨損老到、開片自然,此類絞胎枕為唐代鞏縣窯的標準器、典型器。


3.唐鞏縣窯三彩獅形枕
高10厘米 長13.5厘米寬9.5厘米
枕面如“如意云”狀,內刻如意云形開光,再套刻三層云紋及連珠紋;枕身巧妙地塑成一尊東南亞較流行的卷鬃獅子造型,威武的雄獅承托著云朵般的枕面,寄托著護佑主人安然入夢的祝福。造型新穎、祥瑞,富有強烈的唐代美學取向,通體施綠褐白三彩釉,開片自然,彩釉熔融均勻,淺淡的磨蝕痕極其老到,極具藝術感染力。

4.宋磁州窯三彩銜葉虎形枕(隋唐大運河博物館藏)
高11.8厘米 長36.7厘米
枕取虎形,一般是男性主人的寢具,寓意虎子、虎將,虎頭虎腦、虎虎生風;襯托出雄健陽剛的氛圍,兼有辟邪安寢的功用。此枕與其他虎枕略有不同,少了一些粗獷霸氣的虎威,透出一種溫順狡黠的睿智,虎口銜一扇夸張的青葉,借以隱藏虎身,又巧作實用的枕面;葉面施淺淺的嫩綠釉,而不是蒼翠的碧綠釉;與后面的“金磁州窯黃釉繪黑彩虎形枕”相比較,反映的審美情趣顯然迥異,在虎頭的刻畫、虎身的釉色彩繪上,也多了一些細膩與溫潤,前者較靈動、后者較生動,有虎將與儒將之分。
該枕品相老舊,綠黃黑三彩融合自然,寶光四溢,形神兼備,藝術價值極高。

5.宋吉州窯綠釉刻花“郭家記號”款枕(隋唐大運河博物館藏)
高9厘米 長25.5厘米
枕面為八角長方形,枕墻內凹,面、底與枕墻交界處出檐,檐口抹角,枕面篦劃出八角形開光,開光內刻牡丹團花紋,枕墻的八楞塑成竹節狀;枕墻的方框開光中刻錢紋,底部有戳印“郭家記號”字樣。
除底面外,通體施綠釉、釉色溫潤。該器使用了刻、劃、印、塑多種工藝,力求盡善盡美,還打出了“郭家記號”的品牌,體現了創優的市場意識。


6.宋吉州窯白釉鹿紋銀錠枕
高10厘米 長18.7厘米 寬13.4厘米
銀錠枕又稱元寶枕,是宋代較為流行的一種枕式。牙黃色的厚白釉是吉州窯宋—元時期的特色品種之一,鹿紋亦是吉州窯特有的典型紋飾,因此,在宋代生產白釉的眾多窯口中,我們把它斷識為宋代吉州窯的作品。
該枕的枕面光素無紋,前后枕墻上在印花的席紋開光中,模印臥鹿花草紋;左右枕墻上為印花的連珠紋開光中,加飾繁縟的花草紋。“鹿”與“祿”諧音,有“官祿亨通”的吉祥寓意,又結合元寶狀的枕式,可以心滿意足地做一個升官發財夢了。

7.宋三彩束腰長方形枕
高11厘米 長18.2厘米 寬11厘米
長方形束腰枕,四面劃刻出粗線條的束腰形開光,開光內滿布雙線長六角形紋飾,似席紋效果;通體施醬黃綠交融的三彩釉,清爽而溫潤,四季皆宜。
該枕釉光潤澤,胎釉結合完美,幾乎沒有釉面剝脫的現象;棱角圓潤、磨損老到,品相極佳,釉中有細碎的開片,斜出微翹,文而不武,隱于釉面之下,具有隋唐大運河水土環境中出土瓷器的典型開片特征。

8.金磁州窯紅綠彩葉形枕
高9.5厘米 長17.7厘米 寬16.6厘米
枕面為葉形,枕座為五方形,白胎細膩、白釉潤澤,開片細密,白釉上用紅綠黃三色釉彩繪出葉形開光,開光內繪魚藻紋。因金代紅綠彩為早期的“釉上彩”,極易脫落,故目前釉面殘存的魚藻紋雖彩釉盡失,但紋痕仍十分清晰。這種金代紅綠彩瓷器鑒定的特征,是紅綠彩瓷經歷近千年歲月后,形成的鮮明特色,此枕上的魚藻紋畫工灑脫、老辣,紋飾布局疏密有致,剝脫痕跡自然老到。
葉形枕造型新穎、枕托舒適,制作工藝難度較大,不宜保存、存世量少,因而在瓷枕藏品中屬精少之列,有較高的收藏價值。

9.金磁州窯黃釉繪黑彩虎形枕
高12.2厘米 長36厘米 寬13.7厘米
枕為臥虎、作蹲伏狀,虎視眈眈,昂首盤尾、躍躍欲試。虎背巧作枕面,鼻孔巧作燒制時的出氣孔。該類枕為脫模印制,在制作模具時,可以潛心設計、精雕細刻,因而成品逼真有神、造型威猛。但施釉中卻要全憑功力,黃釉黑彩,契合虎皮斑紋色彩,寥寥幾筆黑彩的點畫,線條流暢、瀟灑絕妙,淋漓盡致、神采盡現。
黃釉繪黑彩虎形枕是金代磁州窯的典型產品,上海市博物館館藏的一件同類作品,出土時上有墨書“大定二年”的年款,據此該類作品斷代為“金”。

10.金磁州窯金三彩妙音鳥紋腰形枕
高8.4厘米 長26.3厘米
主題紋飾鮮見新穎,彩繪的形態神采飄逸。先用劃花工藝在枕面劃出佛教的伽棱頻迦(梵語意“妙音鳥”)神像,再施以褐黃藍三彩釉加以渲染,用金代罕見的藍釉彩,勾出腰形開光。“伽棱頻迦”為人面鳥神像,酷似莫高窟的飛天造型,磁州窯有使用伽棱頻迦神紋飾的記載;筆者在福建泉州始建于宋代的開元寺大殿廊檐斗拱上,也見過大量使用伽棱頻迦的造型,這對于考證宋金時期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及影響,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枕壁的綠彩潑灑得隨心所欲,釉面剝脫自然,胎釉之間使用了淡粉色化妝土,楞線磨損可見歲月之痕。
(本文作者為隋唐大運河博物館名譽館長)
編輯:沈海晨 map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