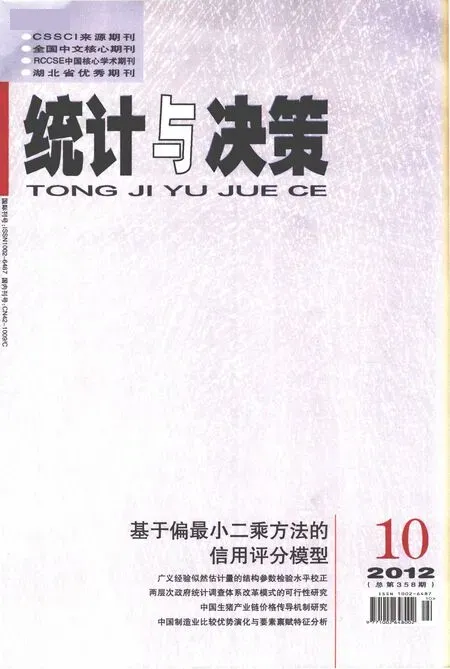中國制造業比較優勢演化與要素稟賦特征分析
馮 梅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制造業憑借勞動力、土地等資源稟賦的優勢,以及勞動力價格和政策環境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并獲得較快的發展,支撐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全球化進程,“中國制造”也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步入“十二五”,中國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勞動力無限供給成為歷史,勞動力價格大幅上漲,土地日益稀缺,對外資的優惠政策也已退出。同時,制造業技術水平、出口結構出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中國制造業面臨轉型升級的壓力。如果能夠將中國制造業比較優勢績效指標與比較優勢的來源進行回歸分析,分析中國制造業比較優勢提升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如何通過改善要素稟賦結構、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動要素稟賦升級推動比較優勢的提升,進而推動中國制造業出口結構和國際分工地位重要意義。
1 中國制造業比較優勢演化和要素稟賦回歸分析
1.1 中國制造業比較優勢績效的變化
對比較優勢績效指標的度量,運用最廣泛的莫過于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最初由巴拉薩(Balassa,1965)提出,是指一國某類商品出口額占該國總出口額的比重相對于世界上該類商品出口額占世界總出口額比重的大小,該指標反映了一個國家某一產業或產品的出口與世界平均水平的相對優勢,在進行國際競爭力比較時被廣泛采用。

式中,RCAij表示i國 j類產品的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Xij表示i國 j類產品的出口額,i=1,2,……,m;j=1,2,……,n;分子表示i國 j類產品出口額占i國總出口中的比重,分母表示世界總出口中j類產品的出口額。
一般而言,RCAij>1,表示i國 j類產品處于比較優勢,RCAij<1,則處于比較劣勢,RCAij值越大,則比較優勢越強,RCAij≥2.5,表示i國 j類產品具有極強的比較優勢;1.25≤RCAij<2.5,表示i國 j類產品具有較強的比較優勢。
為綜合考察中國制造業在國際貿易中相對份額的變化,即比較優勢績效的變化及趨勢,本文選取中國工業制成品出口額在貿易出口總額中的比重相對于世界工業制成品出口額相對于世界貨物出口額比重的大小來度量,即:

經過計算得出中國制造業RCA值(見圖1)。總的來說,中國制造業RCA>1,中國制造業在國際分工中處于比較優勢地位。比較1995~2009年的數據,除了2003~2004非典期間中國制造業RCA持平和2008~2009金融危機期間,制造業RCA呈現一定程度的下降,總的來說,中國制造業比較優勢呈不斷加強的趨勢,這反映出伴隨我國工業化不斷推進,中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

圖1 1995~2009年中國制造業RCA指數
中國制造業RCA指數反映了中國制造業在世界市場上份額不斷提高的現象,但具體各行業的情況可能各不相同,本文有代表性地選擇鋼鐵、化工品、機械與運輸設備等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以及紡織和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進行分別考察,以進一步細分中國制造業比較優勢的變化趨勢:

經過計算,得出各行業RCA值(見表1)。總的來說,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例如鋼鐵、化工、機械和運輸設備制造業的RCA指數均小于1,而勞動密集型產業例如服務和紡織的RCA遠大1,其中RCA中國服裝業>2.5,中國服裝業在世界市場上具有極強的比較優勢,而1.25<RCA中國紡織業<2.5,中國紡織業在國際上具有較強的優勢,說明中國制造業比較優勢主要還是來源于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勞動力價格低廉且無限供給,有力支撐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出口,到目前為止,這一優勢并未得到根本改變。

表1 主要年份中國制造業各行業RCA指數
然而,從各行業RCA變化趨勢看,鋼鐵、機械和運輸設備的RCA指數呈現不斷增大的特點,說明中國鋼鐵、機械和運輸設備行業的比較優勢不斷增強,體現了我國資本和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在國際貿易中的份額不斷提高。具體各行業來看,機械和交通運輸產業的RCA值表現強勁,呈逐年提高的趨勢。鋼鐵行業RCA值先降后升,中國鋼鐵業在國際貿易中呈現出一定的波動性。化工品的比較優勢一直處于較弱的地位,且有下降趨勢,近年來維持在0.34左右。服裝行業比較優勢不斷下降,從2000年的3.9一直下降到2007年的2.79,近年來穩定在2.8左右。而紡織行業的RCA值一路走低,從2000年2.23下降到2007年的1.97。
1.2 中國制造業比較優勢的要素稟賦回歸分析
RCA指標直觀地顯示了一國各產業在國際分工中的相對地位和比較優勢,但是該指標是從貿易結果來考察比較優勢的,即考察的是比較優勢績效,不能說明一國的各產業要素稟賦和技術創新情況。鋼鐵、化工品、機械和運輸設備、紡織、服裝等資本、技術以及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在國際貿易中相對地位的變化不僅反映了中國制造業出口結構的變化趨勢,從中隱約可見我國制造業比較優勢來源的變化,不過,詳細考察我國制造業比較優勢的變化趨勢,還需要將制造業的RCA值與中國要素稟賦情況進行回歸分析,即對比較優勢的來源指標進行分析。
李嘉圖認為比較優勢源于勞動生產率和技術水平的差異,而Heckscher-Ohlin模型則認為相同技術水平情況下,比較優勢源于相對要素稟賦的差異,其后的國內外學者雖然研究方法和觀點各異,也大多從沿著這兩條線探索比較優勢的演化和國際產業分工。因此,本文將制造業比較優勢來源的測度指標分為兩類,一類側重于要素稟賦,包括資本要素(K)和勞動力要素(L)和外資注入(FDI)。另一類則體現技術水平差異,包括體現產業技術水平的勞動生產率(T),體現產業管理水平的資產利潤率(P)幾個方面來確定。
RCA=β0+β1K+β2L+β3FDI+β4T+β5P+ε
其中,RCA=制造業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標,具體數值前文已算出,這里直接應用。
K=制造業資產總值,資產數據采用各年度《中國統計年鑒》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資產總值,其中1995-1997年采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資產數據。
L=中國制造業從業人員數,從業人員數據采用《中國統計年鑒》中分行業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全部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其中1995~1997年數據缺失。
FDI=制造業三資工業企業總產值,總產值數據采用各年度《中國統計年鑒》三資工業企業總產值數據,其中1995~1997年數據采用獨立核算三資工業企業總產值數據,三資是指港、澳、臺投資企業和外資企業。
T=制造業全員勞動生產率,運用各年度《中國統計年鑒》中工業增加值與從業人員之比算出,其中1995~1997年度數據缺失。
P=中國制造業資產利潤率,運用各年度《中國統計年鑒》中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利潤與總資產之比計算出,其中1995~1997年度數據缺失。
通過SPSS統計軟件對1995~2009年共15年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得出中國制造業RCA值與制造業總資產、從業人員數、三資工業企業總產值、勞動生產率以及資產利潤率之間的關系,探討中國制造業比較優勢演化中的要素稟賦特征,計量檢驗結果見表2、表3、表4。

表2 Model Summary(模型摘要)

表3 ANOVA(方差分析表)
從表2中我們可以看出,R2達到0.992,說明線性回歸擬合優度高,模型中的自變量能夠很好地解釋因變量。表3中的F值是233.442,顯著性概率達到0.000,回歸極顯著。
由于資產總值、從業人員、三資工業企業總產值、勞動生產率和資產利潤水平率等各項指標的量綱不同,為更好的反映各要素對RCA指數的貢獻,本文用標準化后的回歸系數,即用Beta值來比較各個要素之間的絕對作用或者貢獻的大小。
由各要素的Beta值可以看出,中國制造業RCA值與制造業資產總值、三資工業企業總產值和勞動生產率三項指標呈正相關,與從業人員數和資產利潤率負相關。說明中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與改革開放之初已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以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獲得世界市場份額的局面正在發生改變,資本(包括內資和外資)、技術成為推動中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因素,這與前文中中國制造業各行業的RCA值的變化相一致。

表4 Coefficients(回歸系數)
具體各要素來說,外資對RCA的貢獻最大,這與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制造業引進外資步伐加快以及國際制造業加速向中國轉移有很大的關系,而且中國制造業出口中有許多是外資企業在國內生產的產品,例如電子信息產品制造業外資比重和出口比重都較高。
另外,制造業資產總值和勞動生產率對RCA值有一定程度的貢獻,但數據顯示貢獻有限。事實上,從前文中鋼鐵、機械與運輸設備制造業的RCA指數看,雖然逐年提高,但總的來說,RCA值依然小于1,說明中國制造業比較優勢中技術水平依然有等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代表中國制造業管理水平的資產利潤率與制造業RCA值負相關,說明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模式依然是以粗放經營為主。伴隨制造業產業規模和出口規模的不斷擴大,相應的利潤水平卻不斷降低,中國是制造業的生產大國,但并非強國。
2 中國制造業要素稟賦升級與比較優勢提升
比較優勢是產業國際分工的基礎,決定一國產業的國際地位,反映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中國制造業RCA指數的不斷提高(反映為中國制造業國際市場相對份額的提高)得益于資本的積累、外資的引入和本土充裕的勞動力資源的結合。不過,現階段中國制造業面臨要素成本上升的壓力,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人民幣不斷升值帶來資本價格的上升,外資優惠政策的終結等等,要素豐裕度和密集度不斷發生改變。要素稟賦條件的改變必然影響未來RCA的走勢。通過要素稟賦結構的不斷升級推動中國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的升級,重視商品出口數量增加的同時更加重視商品價值量的提高是提高中國制造業比較優勢的重要途徑。
2.1 豐富和完善要素稟賦結構
一般來說,要素稟賦豐欠程度的差異性決定了該要素市場價格的高低,相對豐裕的要素價格相對低廉,稀缺要素的價格相對較高。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對豐裕要素的不斷應用,會改變要素稟賦的豐欠程度,從而導致其市場價格的相應變化,進而影響著經濟體中要素稟賦的結構變動。不過,如果能夠拓展新的要素稟賦并密集使用這種要素,比較優勢也會發生較大的變化,例如新能源的開發應用以及價格的不斷降低會引起各國生產方式的變革以及制造業比較優勢的改變。
從中國制造業發展來看,傳統的勞動力要素曾經推動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至今勞動力依然是中國制造業比較優勢的重要決定因素。如今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終結帶來勞動力要素成本的上升,對中國出口的比較優勢形成較大的壓力,雖然資本和技術在一定程度上不斷成為中國制造業比較優勢新的重要來源,但是,從各行業來看,中國這樣制造業出口大國,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的RCA指數都沒有能夠大于1。因此,在立足現有勞動力密集的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如果能夠發掘新的影響因素并密集使用這種要素,可以拓展新的比較優勢的來源,扭轉中國服裝業和紡織業在世界市場比較優勢下降的趨勢。一種比較可行的方式是增加文化創意元素、時尚元素來豐富和完善中國紡織業和服裝業的要素稟賦結構,通過創意和時尚等要素提高服裝和紡織業的附加值,進而提升中國制造業比較優勢的績效。
2.2 提高要素稟賦配置和使用效率
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生產結構和出口結構,然而,即使要素稟賦結構相同的國家,由于專業化以及要素稟賦配置效率的不同進而內生出許多比較優勢。要素稟賦的配置和使用效率的提高實際上是一個發展方式轉變的過程。
要素稟賦配置效率的提高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生產的專業化程度,包括結構多樣化、產業分工的細化以及區域分工的有序化。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生產的專業化和產品的多樣化有利于分工的深化。生產的專業化有利于要素稟賦效率的改善,降低要素價格升高帶來的不利影響。區域有序分工也有助于避免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事實上,中國制造業在生產的專業化程度上還有待提高,例如鋼鐵產業大量小企業的產品結構和生產規模相似,鋼鐵產品以粗鋼居多,精品鋼材的產品相對較少。另外,制造業各地區重復建設的現象十分嚴重,例如近些年來各地盲目上馬新能源項目,風電、太陽能光伏等產業未能產業化卻已經產能過剩等等。
二是要素配置機制的改善。要素配置機制改善其實是一個激勵、競爭和市場機制的完善過程。由于專業化分工往往帶來交易費用的增加,完善的市場機制有利于減少交易成本,增加要素的流動性,推動要素價格的均等化。同時,對于中國這樣經濟結構、企業結構復雜的大國,資源配置不均的現象比較突出。例如,雖然經過多年的積累,中國制造業的總資產不斷上升,2009年度達到49萬億,相比1995年的7.9萬億增長6倍多。從宏觀看2010年中國人民幣存款余額達到71.82萬億、外匯儲備余額28473億美元。從要素稟賦看,中國制造業應該密集使用資本要素。然而,具體到行業、企業,資本要素的配置不均衡,資金集中在大型企業,中小企業資金不足問題十分突出,處于創業期的高新技術企業資金也面臨不足的問題。另外,要素配置機制的改善,也包括減少行政化和壟斷化等等方面的內容。
2.3 推動要素稟賦結構不斷升級
從眾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實踐來看,單純依靠經濟體自我的力量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稟賦結構升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通過政府的適度干預彌補市場的失靈以及通過政府的推手解決經濟中要素短缺問題,進而推動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是一條行之有效的途徑。推動要素稟賦升級實質上是一個制度的完善過程。
一是通過公共服務、公共基礎平臺建設推動中國要素稟賦結構升級,包括對教育的投入、對勞動力的再培訓等實現人力資本的改善和專業化水平的提高。通過基礎研究的投入、技術共享平臺的建設推動知識的創造、傳播和共享,通過科技成果轉化等機制的完善提高技術創新對比較優勢的貢獻度等等。
二是企業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實現要素稟賦對比較優勢的貢獻。從中國制造業比較優勢的要素稟賦特征看,資產利潤率對比較優勢的貢獻為負,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在完善的市場經濟中,企業之間的競爭有利于推動企業管理水平的提高。不過在中國由于許多資本密集型產業,例如鋼鐵產業、裝備產業等以國有企業居多,中國國有企業的效率不高不僅僅是一個市場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通過國資國企改革,提高企業管理效率也是要素稟賦升級的重要途徑。
三是對外部資源的引入來實現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例如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引進大量的外資快速改善了中國資本短缺的瓶頸,將外部資本要素與本國勞動力要素相結合,推動要素稟賦的升級,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出口優勢的迅速提高。當前,中國最缺的要素莫過于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通過不斷引進創新創業型人才,可以有效解決產業升級中對高端人才的需求。
[1] Davidson,W.H.Factor Endowment,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R].Krklos,1979,(32).
[2] Vernon,R.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6,(2).
[3] 王瑞祥,穆榮平.三種優勢理論及政府在產業發展中的作用[J].研究與發展管理,2003(4).
[4] 林毅夫,李永軍.比較優勢、競爭優勢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J].管理世界,2003,(7).
[5] Grossman.G.M.,Helpman.E.Quality Ladders and Product Cycle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106).
[6] Balassa.B.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J].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65,(33).
[7] 林毅夫,李永軍.比較優勢、競爭優勢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J].管理世界,2003,(7).
[8] Arrow Kenneth J.The Economic Implication of Learning by Doing[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