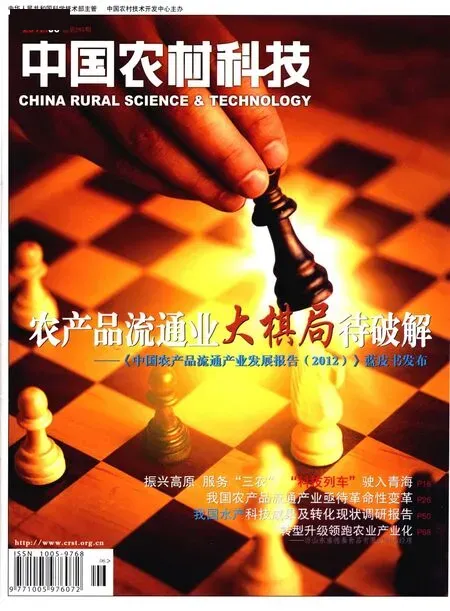我國農產品運銷業發展為何如此緩慢?
■翟留栓 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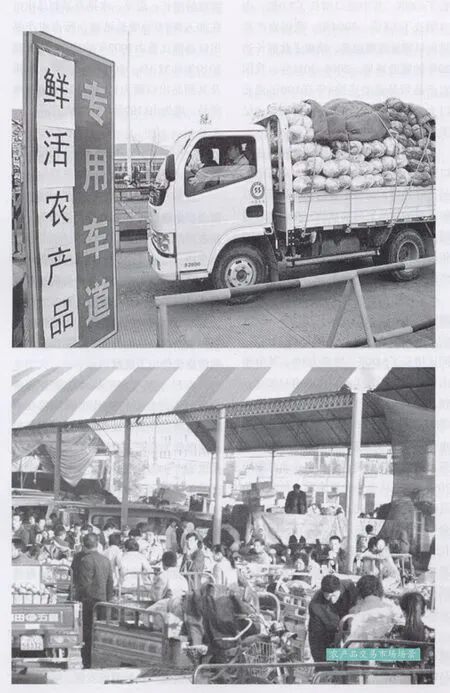
農產品運銷指的是將農產品從生產地移至消費地,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的種種活動。這一過程不僅僅指農產品運輸與銷售,還包括了農產品離開產地一直到消費者手中為止的各項活動,如產品的集貨、分級、包裝、加工、倉儲、運輸、銷售以及市場資訊的收發等活動。因此,農產品運銷是一個非常廣泛的范疇,既包括倉儲、加工、包裝(工業包裝、商業包裝)、裝卸搬運、運輸、配送等物流活動,也包括了收購、銷售等商流活動,是物流和商流的綜合體。
當前,我國農產品運銷體系的一個嚴峻現狀:一方面,我國農產品運銷體系承擔著世界上最繁忙、最復雜的運銷任務,另一方面,承擔這一運銷任務的運銷體系卻是最原始的。農產品運銷發展為何如此緩慢?社會虧欠這個行業太多,它實在“傷不起”。
(一)從2011年的流行語看農產品運銷的“困境”
2011年被認為是農產品運銷年,農產品運銷受到人們的空前關注,這要“得益于”近幾年的流行語。從前幾年的“豆你玩”“蒜你狠”到后來的“姜你軍”、“糖高宗”、“蘋地起”,再到2011年的“蒜你賤”,這些流行語一次次地將質疑的眼光投向了農產品運銷。而2011年的另一個流行語,“菜賤傷農”“菜貴傷民”更是使農產品運銷幾乎在一夜之間成為兩頭受氣的“眾矢之的”,受到社會的質疑,對物流成本過高、環節過多等方面的譴責,似乎已經上升到了“人神共憤”的地步,人們甚至開始懷疑農產品運銷領域是不是存在“暴利”?鋪天蓋地的質疑最終引起了全民大討論,當年5月份中央電視臺組織策劃的《聚焦中國物流頑癥》系列節目,更是將這一討論推向了高潮,國家的各種支持政策隨之密集出臺,農產品運銷一下從幕后走到了“舞臺”的前面。隨著討論的深入,各界基本形成了一個共識:這是一場誤會,農產品運銷是在替人背“黑鍋”、是只“替罪羊”。
一個行業如此被誤解,史上少見,值得深思。
(二)引導農業支持政策向流通領域傾斜
1.適時調整生產導向型農業政策的緊迫性
“蒜你狠”、“菜賤傷農”“菜貴傷民”等流行語的出現,其實是對這一運銷體系脆弱性的集中反映。它表明農產品運銷體系盡管仍在“高速運轉”,但是“疲態”已現,低水平、原始的運銷體系已經無法有效銜接產銷、調節供求。由于長期忽視農產品運銷主體的培育與支持,該領域一直處于一個眾多參與主體低水平過度競爭的隨機狀態,農產品運銷基于四大效用的供求調節功能、產銷銜接功能嚴重退化,致使在豐收—跌價、減產—漲價的輪回中,農民每次都因缺乏運銷的有效引導而滯后于市場的脈動,永遠“踩不準點”,加劇了價格波動。同時,由于缺乏政策扶持,農產品運銷主體(農戶、經紀人)在整個流通鏈條上處于最弱勢的地位,不但無法分享農產品從田間到餐桌的“位移”所產生的價值增值,而且還替“最后一公里”背了“黑鍋”。
上述流行語的集中出現,為生產導向的農業政策敲響了一次“警鐘”:農業發展的“瓶頸”正在從生產領域轉向流通、運銷領域,如果生產導向型的農業發展政策不適時調整,農產品運銷的脆弱狀態得不到根本改觀,“蒜你狠”、“菜賤傷農”“菜貴傷民”就會成為常態。
2.重新定位農產品運銷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農產品運銷的意義不在于自身,而在于其連接的“兩頭”:生產農產品的農戶與消費農產品的消費者。
首先,從農產品的生產者——農戶角度看,我國面臨的主要是“三農”問題。“三農”問題關乎我國現代化建設和社會穩定發展的前途和命運,如何破解這一問題成為我國農業發展政策的終極目標。多年來,社會各界一直在從不同的角度探索破解“三農”問題的途徑和方法,但始終沒能跳出生產導向的政策取向。誠然,生產導向的政策在農業增產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在農民增收方面卻遇到了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農業先天的產業屬性所決定的生產比較利益較低(即使是農業已經高度產業化和現代化的國家,也要給予農業巨額財政補貼)。而如果通過價格補貼增加農民收入,盡管可以提高其積極性,增加產量,但并不一定會最終增加其收入。因為我國農產品市場的賣方(農民)接近完全競爭,而買方(收購商)卻形成相對壟斷。再加上農產品生產由于顯著的自然屬性和漫長的生產周期而導致供給彈性很小,這一彈性特征進一步強化了買方的壟斷勢力。補貼只會擾亂正常的供求關系,導致價格更大波動,最終農戶能否獲得“好處”并不確定;而且,農產品屬于“上游產品”,其價格上漲必然以逐級放大的形式在工業品價格體系中傳導,導致工農產品價格的輪番上漲。這不僅無助于農業與非農業收益差距的縮小,而且會使價格運行陷入惡性循環,最終可能帶給農村居民更大的生活負擔。
其實,理論與實踐都已經證明在農村的三次產業中,二、三產業的附加價值高于一次產業,其中農產品運銷產生的附加價值尤其明顯。只要能改變目前“散、亂、盲”的運銷組織方式,提高農產品運銷體系的效率,就可以為農民增收作出事半功倍的貢獻。而且,如果考慮到我國目前農產品運銷體系的主體仍然以農民為主,支持運銷體系發展其實就是支持農民,這本來就是“三農”政策的題中之義。
另外,生產導向的農業政策還有一個被忽視的缺陷:該政策只注重了農村、農業的價值生產、價值增值,卻忽視了“價值留存”。對于解決“三農”問題來說,僅重視農業生產的價值增值是不夠的,價值增值部分有多少留在了農村、留在了農戶手里才是至關重要的。近年來,對農業生產的支持力度有目共睹,但是城鄉差距不但不見縮小,且有擴大趨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生產發展帶來的價值增值并沒有“留存”在農村,而是通過“最后一公里”被城市拿去了。而要將價值增值“留存”在農村,縮小城鄉差別,有效的方法就是構筑一個包含有利益分享機制的現代農產品運銷體系——因為農產品運銷是聯系城市與農村、農民與市民的最主要的紐帶。
其次,從農產品的消費者角度看,我國面臨的最主要問題是農產品的安全供應問題,既包含質量安全,也包含數量安全。近幾年由于食品安全事件頻發,質量安全引起了各界的普遍重視,各地加強了食品質量安全追溯制度的建設。但是,如果農產品運銷體系仍然延續著原始的方式,這些制度、措施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食品安全?不得不打一個問號。
農產品供應的數量安全問題同樣令人擔憂。我國目前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最迅速的時期,一方面,城市消費規模不斷上升;另一方面城市郊區農產品種植面積不斷減少,蔬菜生產基地從大城市郊區逐步轉向外地農村,運銷半徑不斷擴大。現有脆弱的運銷體系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應對運送半徑、規模的不斷擴大帶來的挑戰,令人擔憂。
以北京為例,2007年時,北京市每年消費的蔬菜中有30%來自于郊區生產,70%來自于外地。而到了2010年,通過對北京市蔬菜來源分布情況的描述可以看出,即使在本地蔬菜上市的旺季七八月份,北京市自產的蔬菜也只占到其消費總量的17%左右,在12月至翌年4月的冬春季節,這一比例甚至只有6%左右,也就是說,2010年北京市蔬菜供應的對外依存度平均達到了80%以上。如果從蔬菜的儲備來看,狀況更加嚴峻。2011年北京市的蔬菜儲備來看,全市每天的蔬菜需求量為2萬多噸,但全市日常蔬菜儲備量僅有1萬噸,只能保證半天用量。粗略計算,一旦發生雨雪或其他地質災害,導致外地蔬菜不能進京,北京儲備的蔬菜只能保證供應學校和醫院等重點單位,普通市民做完兩頓飯后可能就無菜下鍋了。蔬菜供應的數量安全問題顯露無遺。
不僅北京市,各大消費城市的基本情況也都不樂觀。為了確保城市農產品供應安全,各市都在加緊與周邊地區共建蔬菜供應基地。但是,這些基地的蔬菜最終還要靠運銷體系才能來到餐桌上。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是隨著城市化發展、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內地消費城市正在崛起,這些消費城市的崛起必然對現有農產品產銷版圖產生沖擊,引起各蔬菜供應圈之間的競爭,對我國現有的農產品運銷體系構成了挑戰。
3.農產品運銷支持政策的方向建議
農產品運銷的弱勢地位及其后果表明需要政府政策的大力扶持;農產品運銷之于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意義表明它是一個公益性很強的領域,政府政策有理由扶持;而農產品市場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過渡、消費結構開始決定生產結構,市場控制權已經由生產領域轉向流通領域,流通在引導消費和延伸生產增值方面的作用日益強化的背景,則為政策支持提供了絕佳的“時間之窗”,支持政策的巨大效應可期。
那么如何支持農產品運銷體系呢?
運銷支持政策必須結合我國農產品運銷的現狀、“三農”問題、農產品安全供應問題來綜合考慮。
本篇提出兩個支持方向:
一是支持農產品運銷的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產品運銷的投資環境,將運銷增值的隱性地位“顯性化”,吸引民間資本的進入,形成良性循環,從根本上改善我國農產品運銷的硬件環境;
二是扶持農民運銷主體的發展壯大,從根本上改變農產品運銷“散、亂、盲”的狀況。立足于現狀可以發現,農產品運銷體系的主要主體是農戶、農村里的經紀人,也就是農民。農產品運銷體系中的諸多弊端盡管來自于此,但是,不能因此把他們排除在扶持對象之外,反而應該以他們為扶持的主要對象。只有當這些主流的草根主體在激烈的競爭中不斷壯大起來,才能從根本上改變我國農產品運銷體系的脆弱性。而且,只有把農戶、經紀人作為主要扶持對象時,才能實現運銷增值的分配對象“農民化”,從而才會促進“三農”問題的解決。實際上,從農戶、經紀人發展壯大起來的專業化的民營運銷企業在全國已有很多,不少企業已開始在全國各地設點布局,構筑全國性的運銷網絡,根據編寫組走訪的結果看,他們現在呼聲最高的要求就是政策支持。
目前,針對農產品運銷體系中的種種弊端,不少部門已出臺了不少支持政策,如著力培養大型的農業龍頭企業、推動“農超對接”等,都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是,從改善我國整個農產品運銷效率角度看,其作用不應被夸大,畢竟在農產品運銷領域“主角”是農民,龍頭企業只是“配角”,這點與其他領域不同,政府制定扶持政策時需要考慮。
由于本篇的主要任務是對我國目前農產品運銷狀況進行描述,因而只是基于現狀描述對未來政策的支持方向進行了簡單探討,期待各界做進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