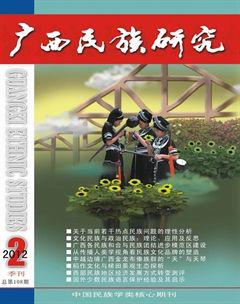中國“民族”內涵及民族研究范式應有之轉變:以壯族為例(二)
[摘要]本文以西方族群和民族理論為觀照,對中國族群觀、“民族”的“塑造”過程及其內涵作一考察,在重新認識中國“民族”的基礎上,對轉變民族研究范式提出建議。
[關鍵詞]民族;民族研究;范式
[作者]李富強,廣西民族大學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兼壯學研究中心主任、碩士生導師、博士、教授。南寧,530006
[中圖分類號]C95.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54X(2012)02-0022-008
二、中國的民族(nation)建構及“民族”概念內涵的確立
古代中國人常以“族”、“部”、“種”、“類”等稱謂區分不同族群。因古代中國非民族一國家,故所有這些稱謂均非與“民族”(nation)等值的概念。古籍中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族”乃指“宗族”,而非“民族”。學者們在我國浩如煙海的古代文獻之中“大海撈針”,雖亦偶而發現“民族”一詞,但多不具現代民族的含義。2004年,邸永君在搜檢史料時,發現《南齊書》卷54《高逸傳·顧歡傳》中,有“民族”一詞,且含義亦與當今“民族”之所指十分接近。但此后,“民族”一詞沒有流行起來。
在中國的國門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之后,隨著中外交流的深入開展,現代意義上的“民族”(nation)一詞在近代逐步普遍使用。1882年,王韜在《洋務在用其所長》一文中云:“夫我中國乃天下至大之國也,幅員遼闊,民族殷繁,物產饒富,茍能一旦發奮自雄,其坐致富強,天下當莫與頡頏。”1899年,梁啟超所著之《東籍月旦》中有“東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變遷”、“民族競爭”等術語。1901年,梁啟超在《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中,首次將中國各族群稱為“民族”。1903年,黃遵憲在《駁革命書》中稱“倡類族者不愿漢族、鮮卑族、蒙古族之雜居共治,轉不免受治于條頓民族、斯拉夫民族、拉丁民族之下也”,首次將中國各族群稱為“漢族”、“蒙古族”之謂并與國外民族并列。
“民族”(nation)概念的傳人,讓中國人對自己的人們共同體產生新的見解,作出新的分類。在強大的政治和經濟支持下自西方進入中國的民族主義,由于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占有優勢,以一種理想模型,成為現代中國追求的目標。一代政治思想家有感于中國“一盤散沙”的狀況,為了“保種強國”,希望以西方民族主義學說動員人民,達到創造強大國家的目的。如孫中山就認為,中國人傳統上祟拜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對“國族主義”全然不知。面對國族如林的現時代,需要把家庭主義和宗族主義擴展成為國族主義,中國要成為一個“哪遜”。然而,要用“民族”(nation)將中國從“天下主義”變為“國家主義”,卻面臨一個難題:具有歷史延續性的政治實體(即“天下”)如何可能運用“民族”的觀念(或“國族”)來處理這個政治實體長期存在的內部族群多元性的問題。要解此難題,必然要經歷一個以傳統話語對“民族”的本土改造過程。正如杜贊奇所指出,有關群體的總體化的表述與敘述結構歷來是存在的,“人們用它們來實現歷史認同,并在現代民族中繼續實現認同。當然,前現代的政治認同并不一定、也不必發展為現代的民族認同,現在與過去存在重大裂痕。一套新的詞匯和新的政治體系——民族國家的世界體系——選擇、適應、重組乃至重新創造這些舊有的表述。但是,對于原有的總體化的表述的歷史記憶并不總是消失,而且由于此種記憶的定期復活,它常常會提出一些有效的材料,用來動員新的群體。”“過去與現在的結合是不斷進行的、真實的”,自近代以來,西來的“民族主義”與中國傳統的“天下主義”(“文化主義”)在不斷地對話、斗爭和交易之中。“民族”的內涵也在此對話、斗爭中流動、塑造。
現代與傳統敘述結構的對話、斗爭在辛亥革命前已非常熱烈。當時,民族主義已經在中國廣為傳播,大量書刊將西方的民族主義和各種科學知識介紹到中國來。現代民族主義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扎下了根,其與中國傳統的關于群體的表述的對話和斗爭,在當時對立的君主立憲派和革命派中,同中有異,異中有同。
起初,激進的革命黨人試圖照搬西方的“民族”和“民族主義”概念,以“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模式,改造中國,于是片面宣傳漢族對中華文明的貢獻,視滿族等少數民族為“低等”的“異類”,發起了轟轟烈烈的“排滿運動”,以期建立以漢族為單一民族的民族國家。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也曾一度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作為革命口號,稱“如冰山之難持,滿漢之不容”,要“將滿洲韃子從我們的國土上驅逐出去”。
而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君主立憲派繼承了中國傳統關于群體的文化主義觀念。盡管康有為受現代民族主義的影響,但他對“民族主義”的定義和解釋具有較濃厚的文化主義色彩。他持“大同”中的種族觀,一貫主張“漢滿不分”,中國應該是“大統一”的原則,認為華夷的區別在于對文明的追求,隨著文化的普及,將來華夷的區別即種族的差別就會消失,華夷就會成為一個整體的“華”。在與章太炎等革命黨人的論戰中,引述孔子的夷狄觀,指出孔子的夏夷之別是指文化和禮制,如果夷狄接受了中國禮制和文化,就應以中國待之。在《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中,他以中國歷史上民族融合的事實,說明不應將滿族視為“異族”的道理。以此論說為基礎,康有為批駁當時革命派日益高漲的建立只有漢族的國家的主張和排滿主義。“他嚴厲警告說革命派所主張的將滿洲人驅逐至其故地東北等,其實就是一種將中國置于小國之境地,以至滅亡之道。”
康有為的弟子梁啟超是西方“民族”和“民族主義”最積極的宣傳者之一,也曾主張“排滿”。然而,隨著“排滿運動”的開展,其導致民族復仇和中國分裂的危險的顯露,促使梁啟超對西方民族主義如何“適宜”于中國進行了冷靜思考。作為一個學貫中西的知識分子,他對民族主義的態度兼有了“批判的武器”與“武器的批判”雙重意味。一方面,是“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主張以民族主義改造和更新中國傳統的“天下主義”。他在《中國積弱溯源論》中指出,不知“國家”與“天下”之別的“天下主義”嚴重阻礙了中國人學習他人的進取精神,淡化了中國人的政治國家意識,是中國積弱的第一根源,中國要想免于淪胥,必須“先建設一民族主義國家”,樹立牢固的國家思想。另一方面,“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強調和重視儒家文化在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建構中的意義和作用,稱:“且試思我國歷史,若將孔子奪去,則黯然復何顏色,且使中國而無孔子,則能否摶挽此民族為一體,蓋未可知。”因而,此后梁啟超民族主義思想呈現中國傳統“文化民族主義”與西方政治民族主義交融的特征。他在《新民叢報》發表的《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中,對革命派提出質問:“日必離滿洲民族,然后可以建國乎?抑融滿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諸民族,而亦可以建國乎?”并以“小民族主義”和“大民族主義”兩個概念來闡述中國民族主義,曰:“吾中國言民族者,當于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民族對于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之諸族以對于國外之諸族是也。”指出:“自今以往,中國而亡則已;中國而不亡,則此后所以對于世界者,勢不得不取帝國政略,合漢、合滿、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類,以高掌遠瞻于五大陸之上,此有志之士所同心醉也。”
然而,不論是君主立憲派還是革命派,在他們的觀念里,“民族”與家族、種族是相互滲混的。如梁啟超云:“最初由若干有血緣關系之人,(民族愈擴大,則血緣的條件效力愈減殺。)根據生理本能,互營生活;對于自然的環境,常為共通的反應;而個人與個人之間,又為相互的刺激,相互的反應;心理上之溝通,日益繁富,協力分業之機能的關系,日益致密;乃發明公用之語言文字及其他工具,養成共有之信仰學藝及其他趣嗜;經無數年無數人協同努力所積之共業,厘然盛開特異之‘文化樞系;與異族相接觸,則對他而自覺為我。”“血緣、語言、信仰,皆為民族成立之有利條件;然斷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徑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要素,‘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何謂民族意識?謂對他們自覺為我。‘彼,日本人;我,中華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華人之一觀念浮于其腦際者,此人即中華民族之一員也。”對梁啟超而言,“民族”一詞既有構成國家的“國民”這一西歐政治學意義,又兼有相同血脈的種族和宗族的意義。蔡元培則指出:“凡種族之別,一曰血液,二曰風習。”汪精衛認為:“民族云者,人種學上之用語也,其定義甚繁,今舉所信者,曰:民族者同氣類之繼續的人類團體也。茲所云氣類,其條件有六:一同血系(此最要件,然因移住婚姻,略減其例),二同語言文字,三同住所(自然之地域),四同習慣,五同宗教(近世宗教信仰自由,略減其例),六同精神體質。此六者皆民族之要素也。”柳亞子認為:“凡是血裔、風俗、言語同的,是同民族;血裔、風俗、言語不同的,就是不同民族。”他們對“民族”的定義,多以家族血裔、世系和文化禮儀為框架,同時與種族相混淆。只是“康有為等君主立憲派論認為居住于包括漢、滿在內的中華帝國境內=中國的全體子民,都是黃帝的子孫。其理由是滿洲人同化于漢人,所以接受了中華之禮。君主立憲派主張為了‘保國保種,應該具有‘愛國愛種的意識。他們所指的‘國的范圍是中華帝國=清朝之版圖。”而革命派認為只有漢種是黃帝子孫,中國境內的其他“種”都不是皇帝子孫,因而主張“排滿”、“仇滿”。
革命派在與君主立憲派的思辯、論爭中,逐步認識到漢人主導的民族主義在推翻滿清后會自然地導致蒙古、藏、維吾爾等族脫離中國,于是,“孫中山和新建立的民國領袖試圖用自己的政敵即維新派和清廷所闡釋的文化主義民族觀的敘述結構來補充自己的種族主義敘述結構。中華民族開始由‘五族(滿、蒙、藏、回、漢)組成,從而中華民族繼續承襲著大清帝國的邊界線,正如印度民族試圖根據大英帝國的構想來重建一樣。種族作為民族基本成分的敘述結構本身也煙消云散,或許被納入了更大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共同歷史經驗的更大的民族主義敘述結構之中。”1919年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一文論及民族主義時,已拋棄“排滿”思想中的大漢族主義狹隘性,提出了“中華民族”的全新范疇。在1923年的《中國革命史》中,孫中山曾精辟概括了其民族主義思想的淵源與宗旨。對孫中山及其追隨者的這一轉變,有的學者概括為“從華夏中心主義到文化民族主義”。
但“五四”運動之后,由于中國周邊形勢的變化,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又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一是從“五族共和”轉向漢族民族主義。1921年3月6日,他在《在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上的演說》中說:“今天我們講民族主義,不能籠統講五族,應該講漢族的民族主義。或有人說五族共和揭橥已久,此時單講漢族,不慮滿、蒙、回、藏不愿意嗎?此層兄弟以為可以不慮。彼滿洲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即無自衛能力的表征。然提撕振拔他們,仍依賴我們漢族。兄弟現在想得一個調和的辦法,即漢族來做中心,使之同化于我,并且同為其他民族加入我們組織建國的機會。仿美利堅民族的規模,將漢族改為中華民族,組成一個完全的民族國家。與美國同為東西半球二大民族主義的國家。……故將來無論何種民族參加于我中國,務令同化于我漢族。本黨所持的民族主義,乃積極徹底民族主義。”同年12月10日,《在桂林針對滇贛粵軍的演說》中又說:“所謂五族共和者,直欺人之語!蓋藏、蒙、回、滿,皆無自衛能力。發揚光大民族主義,而使藏、蒙、回、滿,同化于我漢族,建設一最大之民族國家者,是在漢人之自決。”孫中山之所以要使藏、蒙、回、滿同化于我漢族,是因為他們沒有“自衛能力”,而“自衛能力”的缺乏,在他看來是文化程度低的緣故。漢族同化諸族為中華民族的力量是使宗族團結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
二是提出“融宗族為國族”的理論。他在“種族的”民族觀的基礎上,接受社會進化論,認為民族的構建要靠種族的“同一”和“進化”。“同一”,“即漢族來做中心,使之同化于我”。“進化”則是指“中國民族的構建要從人種→部落→村落共同體→宗族→國族(中華民族)。因而,要把以家族為單位的宗族聯合起來,促成‘國族。”他認為中國人家族、宗族觀念根深蒂固,可以之鍛造民族,曾說:“堯的時候,‘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他的治平工夫,亦是由家族入手,逐漸擴充到百姓,使到萬邦協和,黎民于變時雍,豈不是目前團結宗族造成國族以興邦御外的好榜樣嗎?”
之所以有此變化,與當時的局勢有關。因為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陰謀紛紛付諸實施,中國處于四分五裂當中,如何實現統一當是當時仁人志士苦苦求索之歷史使命。變“五族共和”為強調以漢族為中心,同化滿、蒙、回、藏諸族是孫中山開出的“藥方”。而此變化表面上看又是此前革命派對西方“一民族一國家”的照搬,實則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主義的更深的“復歸”。因為此時孫中山的建國思想里,已包括了漢、滿、蒙、回、藏,只是要以漢族同化他們,這與古代“天下主義”以“華”化“夷”的思想同出一轍。
這種把漢族等同于中華民族和“融宗族為國族”的民族觀一直影響到孫中山逝世后的整個民國時期,成為當時中國民族主義的主流話語。1942年蔣介石在《整個中華民族共同的責任》講話中說:“我們集許多家族而成為宗族,更由宗族合成為中華民族。國父孫先生說:‘結合4萬萬人為一個堅固的民族。我們中華民國,是由整個中華民族所建立的,而我們中華民族,乃是聯合我們漢、滿、蒙、回、藏五個宗族組成一個整體的總名稱。我說我們是五個宗族,而不是說五個民族,就是說我們都是構成中華民族的分子,象兄弟相合成家庭一樣。……我們中華民族是整個的,我們的國家更是不能分割的。”而在蔣介石1943年發表的《中國之命運》中也說,五族不是各自的民族,而是原本有著共同血緣的宗族的集合體的單一的中華民族。
可見,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50年代前,在中西族群敘述結構對話中行進的中國的民族構建一直不同于西方,后者注重市民社會的建立和語言的同一陛,而前者始終注重“種族”的“同化”與“進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中西敘述結構對話之下,尚包含有古今族群敘述結構的對話。在此紛繁交錯的對話框架下,當時的政治家、思想家,包括孫中山和蔣介石等,他們都是以“種族”和中國傳統的家族、宗族及其文化來想象和定義“民族”的。可以說,在他們的觀念里,“民族”就是一個“種族一家族象征體”。這是以中國傳統對外來“民族”的改造和創造出來的本土概念。
1949年以后,由于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以馬列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因而其民族的理論與實踐受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影響甚大。然而,如同孫中山等人的民族主義思想一樣,中國共產黨的民族觀也是實踐中經由馬列主義民族理論與中國傳統族群觀(民族觀)及所面臨的社會現實的對話中建構形成的。
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對于“民族”的認識無疑是來源于馬列主義經典作家有關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現代民族的論述,反映在實踐上,曾根據蘇聯民族政策提出民族自決和建立聯邦制國家的設想。但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延安之后,中國共產黨的民族綱領有了明顯改變:不再提聯邦制和“民族自決權”,而提民族自治。1938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作《論新階段》的報告中提出:“允許各少數民族與漢族有平等權利,在共同對日的原則下,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同時與漢族聯合建立統一的國家;在民族雜居地方,由當地少數民族人員組成委員會作為省縣政府的一個部門,管理有關事務;尊重少數民族文化,幫助他們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糾正大漢族主義。”之所以有此轉變,美國學者德雷爾(June Teufel Dreyer)在1976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的四千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少數民族和民族融合》(Chinas Forty Millons: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認為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是紅軍長征的經歷使黨的領導人認識到少數民族對于中國革命的重要性,也認識到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少數民族不會“自愿”地選擇與漢族共同組成一個國家;第二是當時蘇聯控制新疆的戰略使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擔心新疆變成第二個外蒙古;第三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國各地極力扶植少數民族的傀儡政權,“民族自決”可能會被日本侵略者利用來分裂中國。馬戎基本接受這一觀點,并進一步作了闡述。
尚在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就開始了民族自治的實踐,1935年在寧夏豫旺、海原兩縣建立了豫海縣回民自治政權,1942年在陜甘寧邊區定邊建立回民自治區,1947年成立了內蒙古自治政府。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取了全國政權后,即將民族區域自治作為一項法定的制度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制定的“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結構形式是單一制的多民族統一的人民共和國,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此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4年還制定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至今為止,全國建立了5個少數民族自治區,30個自治州,120個自治縣(旗)。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并在法律上和實踐中不斷完善著。
美國學者德雷爾曾將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民族理論大致歸納為三點:一是強調各族群的平等;二是對于“民族自決”的模糊定義;三是試圖把族群特征與階級結構相聯系,認為強調族群特征和族群利益是為資產階級服務。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抉擇,既堅持了馬列主義民族理論的基本原理,又充分認識和正確把握中國歷史文化和現實的特殊性,將馬列主義普遍性與中國的具體隋況相結合。“據李維漢同志回憶,1949年人民政協籌備期間,毛澤東同志就是否實行聯邦制的問題征求了他的意見。李維漢同志作了深入研究,認為我國同蘇聯的國情不同,不宜實行聯邦制。理由是:(一)蘇聯少數民族約占全國人口的47%,與俄羅斯民族相差不遠。我國少數民族只占全國人口的6%,并且呈現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狀態,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以及幾個少數民族之間往往相互雜居或交錯聚居。(二)蘇聯實行聯邦制是由當時的形勢決定的。本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都主張在統一的(單一制的)國家內實行地方自治和民族區域自治,只是在例外情況下允許聯邦制。……俄國經過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許多民族實際上已經分離成為不同國家,不得不采取聯邦制把按照蘇維埃形式組成的各個國家聯合起來,作為走向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我國則是各民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由平等聯合進行革命,到平等聯合建立統一的人民共和國,并沒有經過民族分離。因此,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更加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在統一的國家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更有利于民族平等原則的實現。中央采納了這個意見。”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由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特點和當今民族分布的特點所決定的。它與我國歷史上的“羈縻制度”和“土司制度”相似,是在統一國家下統治管理少數族群的制度形式。當然其目標是建立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實現各民族的共同發展繁榮。這一宗旨和目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中有充分的體現。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所反映的民族觀就是費孝通先生所歸納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雖是費孝通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正式提出,但卻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探索建設民族國家的“中國道路”的經驗總結和智慧結晶。其實,從梁啟超與“小民族主義”相區分的“大民族主義”,到孫中山的“五族共和”,都包含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思想的萌芽,只是比較含混、模糊,或自相矛盾。而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通過民族識別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運行,構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正是在此情形下,費孝通先生集前人之大成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作為一種“中國化”的民族觀是對西方民族主義的挑戰、突破和拓展,是對世界民族國家建設的重大貢獻。近代以來,隨著西方民族主義的廣泛傳播,“一民族一國家”的民族國家模式濫觴于世界,成為主流的政治模式,給世界以深遠影響,甚至到20世紀90年代,世界性和區域性的沖突,大多發源于“一民族一國家”的理念,而西方對于區域沖突和主權問題的介入也常以維護此理念為借口。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實踐表明,“一民族一國家”并非全人類歷史的必由之路,也不一定是最佳的政治模式。
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為了貫徹“民族平等”,落實民族區域自治,從制度上建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通過“民族識別”確定了56個“民族”。雖然民族識別的指針據稱是斯大林的民族定義。但從現有的材料看,當時從事民族識別的不論是領導者還是科學工作者,都充分認識到,斯大林關于民族四大特征的理論是針對歐洲資本主義上升階段的現代民族的理論,而民族是個歷史范疇,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產物,每一個國家和每一個民族的具體歷史條件不同,如何結合中國各民族的實際靈活運用這個理論來進行民族識別是搞好這項工作的關鍵。在中國民族識別的實踐中,不僅沒有生搬硬套斯大林的民族定義,而且從中國民族實際出發,重視對待識別族體的族稱和歷史來源的調查研究。馬戎先生曾對我國的民族識別工作進行了獨到而中肯的總結和歸納:
從曾參與“民族識別”工作的老一代人回憶錄和他們留下的著作來看,當年的“民族識別”工作有四個特點:第一,當年在收集各類材料以判定群體差別是否可以定義為“民族”差別時,主要的資料是歷史、語言文字、服飾習俗等基本上屬于文化層面的內容;第二,行政區劃和管轄邊界等政治層面的內容并不是當時的重點;第三,由于在大多數情況下各群體的體質差異并不明顯,所以體質差別也沒有成為識別工作的主要內容;第四,在“識別”過程中,對于當地群眾的愿望給予特別的重視。所以,在斯大林關于“民族”定義的四條標準中,“共同語言”、“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這兩條主要表現文化層面共性的標準受到了特別的重視,“共同經濟生活”和“共同地域”這兩條在一些民族(如回族、滿族等)的識別中是相對淡化的,“共同地域”在應用中實際被解讀為“傳統居住地”。但即使是這兩條,在中國“民族識別”中的運用也不具有很強的政治色彩。在當時,除了西藏一度具有自己的地區政府之外,中國的各個“民族”并不是政治色彩很強、具有清晰的“領土”和人口邊界群體。所以回顧當年的“民族識別”工作,應當說主要關注點是文化差異和自我認定,而不是政治因素和體質因素。而當年一些群體申報希望成為獨立的“民族”,強調的是自己群體的文化特點和歷史傳統,強調的是希望在各方面得到政府更多的重視,并不是強調自己是具有特殊政治利益和擁有政治獨立性(如“民族自決權”)的群體。
因此,盡管中國民族識別可能存在著某些偶然性和主觀性,但大體說來,經過“識別”的56個“民族”,具有文化共同體的內涵。然而,中國的“民族識別”是為了建立和完善落實民族區域自治,貫徹黨和政府的其他各種民族政策,以制度性的安排保證“民族平等”及扶持少數民族發展目標的實現,所以存在著有共同文化的群體被“識別”為不同“民族”,而文化差異明顯的群體被“識別”為同一“民族”的現象,而且在實踐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過程中,各少數民族普遍擁有自治權,在各級政府、人民代表大會等機構中,都要求按各種民族成分配備人員,這些政治訴求也影響到了“民族識別”。所以,這56個民族中的各民族其實既是文化共同體又是政治共同體。既不是ethnic group,更不是nation,而與nationality相似。
在構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還重新定義和詮釋了“中華民族”概念。據研究,“中華”一詞源于魏晉,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民族”一詞傳人時,兩詞相合,乃成“中華民族”。自近代以來,“中華民族”一詞廣泛使用,意義卻有所不同。在章太炎的概念里,“中華”專指漢族。在梁啟超、孫中山的觀念里,“中華民族”時而指中國境內各民族,時而指漢族。而中國共產黨由于始終堅持民族平等,注意糾正“大漢族主義”,早在革命戰爭年代,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中,就已英明地認識到中華民族是中國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爭中自覺地結成的整體,因而其“中華民族”的意義是指根本利益和目標一致的中國各民族。建立了新中國,通過“民族識別”構建了56個民族之后,中國共產黨更賦予“中華民族”新的意義:比56個民族高一個層次的“民族”。正如松本真澄所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如果說與國民黨時期有著某種連續性的話,就是提出以‘漢族為主體,同時把具有‘中華民族的identity(認同感)的‘少數民族包括在內的中華民族的nationalism的發揚作為國家的柱石。”
關于“中華民族”的性質,有的學者認為只是個政治概念和地域概念,要從“文化多元”和“政治一體”的結合來理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筆者以為不然。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國家,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民族一國家”(nation-state),她“是一個以文化而非種族為華夷區別的獨立發展的政治文化體,或者稱之為‘文明體國家(civilizational state),它有一獨特的文明秩序”。在此崇尚以“王道”(即文化“教化”)化“夷”為“華”,富有在“和而不同”基礎上“協和萬邦”達至“天下大同”的大一統理想的國度,各族人民是否在千百年的“華夷互化”中共同創造了他們共同踐行的歷史文化大傳統——“中華一體文化”?在我看來,回答是肯定的。費孝通先生認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分為三步:一是華夏集團的形成,二是從華夏核心擴大為漢族核心,三是長城內外農牧兩大統一體的融合。他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一文中,將“中華民族”形成發展的歷史分為“自在”和“自覺”兩個階段。費孝通先生筆下作為“自在的民族實體”的“中華民族”是由多元文化(族群)融合形成的,當然是一個“文化的實體”。“中華民族文化”,如張海洋先生所言,也是“多元一體”的格局。“一體”是指中國各民族共同創造和踐行的歷史文化大傳統,這個單數的大傳統不是國內某個民族的民間文化,而是中國各族人民共同的歷史文化。“多元”是指中國境內各民族、族群、地域、地方的歷史文化小傳統。這些復數的小傳統是具體的民族民間的,它們以不同的程度和方式與大傳統交織勾連,成為中國人內部不同層次的認同對象和識別表征。這個多元多層次交織而成的體系,就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多元一體。中國共產黨和政府一再強調要弘揚“中華民族文化”,這個“中華民族文化”既包括中國境內各民族的多元的文化,也包括“中華民族一體文化”。“中華民族”既是一個政治體,也是一個文化體。
[責任編輯:袁麗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