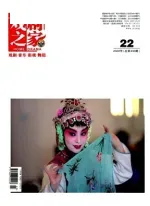文學評論應跟上創作的腳步
□楊繼軍
19世紀西方現實主義文學的興盛和發展,使得社會學的評論方法得到了發展,使典型論成為檢驗作品高下優劣的重要標志;20世紀以來,隨著形形色色的現代派創作的興起,隨之在文學評論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觀念和模式。
在我國,曾經出現過只有八個樣板戲和一部小說的可悲景象,與之相適應的,是評論的單一化、棍棒化、政治化、絕對化;新時期以來,創作上的多樣化導致了文學評論的多樣化。
文學的發展史表明,創作和評論,總是同命運共呼吸,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一般來說,總是創作在前,評論在后,從這個角度看,評論對創作的依賴性是無法更改的。常常是創作上的突破帶來評論方法的更新和變異。比如面對那些側重寫心態、情緒或某種氛圍的小說,就不宜單用典型化的原則去衡量。評論家要想進行評論和闡釋,必須改換新的視角,尋找新的切入點和新的評論方法。比如,當代文學注重揭示人的情感歷程和心靈奧秘(即所謂“向內轉”),與之相適應的是情節的淡化,不再以塑造完整的人物性格為指歸;在再現中有了很強的表現性因素,出現了象征、夸張、荒誕、意識流等等。
正是面對創作現象的變異,于是諸如心理評論、原型評論、結構主義、符號學等諸如此類的評論模式便應運而生。對作品的整體把握,也有了多種視角,拓展了思維空間。但是文學評論的“超越”性品格又使它具有了相對的獨立性。反轉過來,它又對創作起著引導、規范、升華的作用。
文學評論的生命就在于它的開放性和兼容性。藝術形象的創造有多么豐富它就應當有多么豐富。凡是藝術形象涉及到的領域(諸如社會歷史的、政治的、倫理的、道德的、宗教的、人類學的、文化學的……)都理所當然地成為它的評論對象。文學評論的一個重要的使命,是它應當追蹤一切新的文學現象而不能采取充耳不聞,視而不見的貴族老爺式的態度。面對變動不拘、亂花迷眼的文學現象,評論家應具有敏銳的眼力,要善于及時地發現它們,捕捉它們,對它們進行研究、分析、剖示、概括……
文學評論不是純理性的思辯,它要建立在評論家個人的藝術感受上,因此較之文藝理論更帶主觀性和情感性。但它又不能僅僅停留于感受和體驗的層面上,而要將這種感受和體驗升華為理性認識。這就使得評論不同于創作,即是說,它主要不是進行形象思維和靈感思維,而基本上是以理性思維為主。
所以,文學評論總是在某種哲學思想、美學思想的指導下進行評論和闡釋的,總是受到某種理論的規范。這就是一個矛盾。因為理論帶有相對的穩定性,而藝術形象的創造總是越出理論的規范。在新的藝術形象面前,理論總是顯出自己的陳舊和不合時宜。于是評論家常常處于兩難的境地,因為徹底擺脫傳統理論的約束是根本做不到的。
再說,沒有理論作指導的評論只能是膚淺的評論。評論家的難處在于,他常常是用舊理論來闡釋新形象。因此,文學評論極易犯這樣的錯誤:不是通過對藝術形象的分析得出新的結論,而是用舊規范去限定新形象,指責新形象,甚至采取不承認態度。在這種情況下,文學評論就會落后于創作,就很難說與創作的發展做到“同步”。
文學評論和創作發展的“同步”,關鍵是防止評論家思想上的保守和僵化。毫無疑問,評論家有權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這也是評論家成熟的標志。問題在于,評論家不應固守某一理論,更不能把它視為絕對正確的金科玉律。事實上,任何理論都有局限,都需要不斷地加以豐富和發展。評論家在遵從和信奉某一理論的同時,必須要有一種懷疑精神、叛逆精神、超越意識。當自己的理論觀念和新的文學現象發生矛盾和錯位時,更應尊重后者而懷疑前者。不是用舊規范去否定新現象,而是用通過新現象的具體研究去補充、豐富原有的理論,甚至徹底地與之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