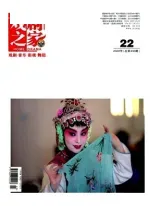試論器樂演奏的三個境界
□徐國生
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有一段關于孔子學琴的記載,文字雖然很簡短,但對器樂演奏,具有重大的美學價值,很值得予以剖析和借鑒。這段記載是這樣的:
“孔子學鼓琴于師襄,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如此也。”
美學家徐復觀在《中國藝術精神》一書中,對這段話做了如下精辟的詮釋:“按‘曲’與‘數’是技術上的問題;‘志’是形成一個樂章的精神‘;人’是呈現某一精神的人格主體。孔子對音樂的學習,是要由技術以深入技術后面的精神,更進而要把握到此精神具有者的具體人格;這正可以看出一個偉大藝術家的藝術活動的過程。對樂章后面的人格的把握,即是孔子自己人格向音樂中的沉浸、融合。”
這段關于孔子學琴的珍貴記載,是音樂史話的一例個案,但這一個案具有普遍意義和永恒價值。因為它在音樂美學的意義上,涉及到器樂演奏層層遞進的三個境界,即技藝境界,意象境界,人格境界。
第一個境界是技藝境界。技藝境界是表層境界。在技藝境界里,器樂演奏者著重把握的是音樂形式。他要熟悉基本樂理知識,懂得基本音樂語匯,能讀懂作曲家的樂譜,具備基本的演奏技藝和技能。技藝境界是不可逾越的基礎境界。猶如不懂文字、詞匯和語法,便無法讀書和寫作,不懂的“永字八法”和執筆方法,便不能從事書法藝術。一般來說,過了技藝這一關,便可以進行演奏了,但這種演奏只能停留在技藝境界。所以,孔子雖然已掌握了“曲”和“數”,解決了演奏技藝問題,但仍然不進行演奏。
第二個境界是意象境界。意象境界是中層境界。在這個境界里,器樂演奏者著重把握的是音樂意象。音樂意象,即物我交感,情景交融,并訴諸特定音樂形式。它是一個樂章的音樂形象,傳達特定的音樂精神。音樂意象情感飽滿,風格鮮明,或優美或壯美,富有人生感、生命感、宇宙感。器樂演奏必須經由技藝境界,進入意象境界。一旦進入意象境界,傳達出樂章精神,其演奏便會臻于上乘。但在音樂意象后面,還有更深層的音樂意境有待挖掘與表現。所以,孔子在把握了由音樂意象體現的樂章精神后,仍然悵然若失意猶未盡,不肯停留在意象境界上進行演奏。
第三個境界是人格境界。人格境界是深層境界。在這個境界里,器樂演奏者著重把握的是樂章意象(精神)背后的人格主體。人格主體,即樂章創造者的胸襟與情操,審美趣味和審美理想。人格主體是樂章精神的底蘊,是樂章的審美靈魂。音樂生發于深心深情,美是心靈與自然和諧的結晶。在音樂意象背后,還有一個更感人的音樂形象,即樂章創造者的抒情形象;在樂章精神背后,還有一種更動人的音樂精神,即樂章創造者的人格精神。音樂即情感情操,情感情操即人格。主體人格演繹為樂章精神。把握樂章精神,必須感悟人格主體。
另一方面,只有演奏者將自己的人格,融入樂章的主體人格,達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情意綿綿,物我兩忘,才能將樂章的意象與精神,聲情并茂地演奏出來,也才能讓聽眾和自己,真正經過音樂審美而陶冶情操,完善人格,激發生命活力。器樂演奏,只有經由意象境界,與樂章主體的人格境界達成默契,才能達到演奏的最高境界。所以,當孔子最終感悟到樂章的主體人格后,它居然激動得形神突變,“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
人格境界,是器樂演奏的最高境界。是否達到人格境界,是衡量器樂演奏品位的試金石。阿炳演奏的《二泉映月》,之所以讓人心馳神往,讓其他演奏者難以望其項背,是因為他的演奏是他整個人格的全身心投射。其他中外器樂大家的絕唱,也無一不是其人格精神的盡情宣泄。
孔子學琴經由的三個階段,三種境界,給我們的根本啟示是,器樂演奏這門藝術,最終博弈的是人格精神。中華文化藝術,一向崇尚人的精神境界,高度強調“藝如其人”。弘一法師曾留給我們一條他一生踐行的藝術信條:“先器識后文藝。”器識即人格修養。人格精神博大精深,才談得到從事藝術事業,才談得到藝術精品。在文學藝術日益功利化,人格精神日益萎縮的今天,孔子學琴的故事,弘一法師的遺訓,不啻暮鼓晨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