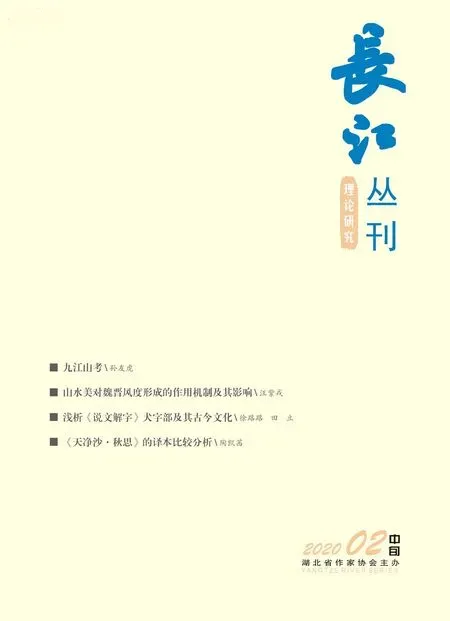擔當精神:當代青年的必備網絡文明素養
■趙春霞/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數學與統計學院
一、前言
在改革轉型的歷史條件下青年群體理應以勇于擔當、開拓創新的擔當精神對待學習、工作和生活,自覺擔當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歷史重任。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提出,青年一代有能力、有擔當,國家和民族才會有前途、有希望,每個青年都應當不負歷史使命和人民期盼。[1]網絡社會是青年群體生活和學習的重要場所,也是價值觀教育和道德教育的重要陣地,網絡文化生態深刻影響著當代青年的擔當精神培育。所以應將擔當精神培育作為網絡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在網絡空間中培育當代青年的擔當意識和創新精神。
二、當代青年文明素養培育的網絡境域
但是虛擬的網絡世界并不太平,也不美好,經常受到各種消極文化的侵蝕,成為眾聲喧嘩的“烏托邦”和秩序紊亂的虛擬社會,這些給青年網絡文明素養培育帶來負面影響。
(一)網絡空間是眾聲喧嘩的“烏托邦”
在人人都是“自媒體”的網絡世界中,網民們常以情緒化表達、無節制宣泄的方式表達自我,形成了眾聲喧囂、烏龍混雜的網絡次生輿論生態,這些給網絡文明建設和網絡秩序建構等帶來負面影響。比如在天津港爆炸事件發生后,各種謠言四處傳播,就連氣象局、民政局等部門也無辜中槍,給有關部門的突發事件處理工作帶來許多負面影響。此外,在眾聲喧嘩的網絡世界中無端猜測、夸大宣傳、情緒化表達等往往更有生命力和傳播力,能夠借助自媒體的“東風”肆意傳播和擴散,事實和真相卻往往人拋之腦后,導致網絡文化心態偏激、網絡輿論導向失衡。勒龐在心理學著作《烏合之眾》中就提出,當人們面對陌生事物時,往往會從外部世界尋找證據,盲目聽從專家、權威、大眾的意見,于是就形成了極端化的社會情緒和心理。比如在“王XX離婚事件”事件等網絡事件中,都折射了網民的焦躁不安的情緒。
(二)網絡社會是秩序紊亂的虛擬社會
網絡世界是一個虛擬世界,各種社會文化和價值觀都可以在網絡世界上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從而導致內容低俗化泛濫等問題比較嚴重。比如在網絡直播中有些主播以雷人言語、粗言粗語、低俗內容等吸引受眾眼球,給網絡文化生態建設帶來許多負面影響。再如在網絡知識付費、網絡影視觀賞等方面,盜版、侵權等問題屢見不鮮,帶來了網絡秩序混亂問題。在垃圾信息大肆泛濫的網絡世界中,各種網絡假新聞、偽信息給網絡世界給青年一代造成了許多負面影響,比如消費主義、娛樂至上、極端思想等在網絡世界中大肆泛濫,給青年一代的價值觀成長帶來許多負面影響。再如在網絡傳播中逐漸形成以順其自然、一切隨緣、隨遇而安等為價值取向的文化,在文化影響下少量青年將無所作為、渾渾噩噩過日子作為人生追求,抱著“什么都行”、“無所謂”的態度對待生活、學習和工作,直接影響了青年群體的擔當精神培育,也給青年一代的網絡文明素養培育帶來負面影響。
三、擔當精神是青年必備的網絡文明素養
擔當精神是指在重大挑戰面前敢于知難而上,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敢于亮劍,在危機時刻能夠挺身而出,在出現失敗和失誤時敢于承擔責任。擔當精神是一種優秀的政治意識和道德品質,也是當代青年必備的網絡文明素養。在2019年全國教育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提出,青年學生要志存高遠,敢闖敢干、勇于擔當。
(一)擔當精神是青年一代必備的優秀品質
擔當精神不僅是一種堅守政治原則的政治勇氣,也是一種敢于接受挑戰的精神狀態和責任意識。首先,堅持原則、恪守底線的政治勇氣。原則和底線是習總書記在重大公開場合常用的高頻詞,也是總書記對當代青年的政治要求和殷切期盼。青年一代理應堅守政治原則、恪守道德底線,在大是大非、重大問題上保持正確的政治原則和立場,不能為不正當利益所誘惑或歪理邪說所蠱惑。其次,直面困難、不畏挑戰的精神狀態。《易經》開篇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血氣方剛的青年群體理應以直面現實的勇氣、勇于擔當的精神迎接各種困難和挑戰,以“明知山有虎,偏要虎山行”的態度對待困難和挫折,在艱難的生存環境、繁重的工作任務中迎難而上。正如總書記所說,青年一代要有不問前路、只問耕耘的風骨,有戰風險、渡難關的主心骨。此外,服務國家、服務社會的責任意識。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歷代先賢和仁人志士都以國家和民族事業為己任,自覺擔當國家與民族重任。所以青年一代理應以國家振興和民族復興為己任,以認認真真學習、踏踏實實工作的方式擔當時代責任。最后,放眼全球、著眼未來的博大胸懷。承擔責任、擔當使命是以放眼全球、著眼未來的眼光和胸懷為前提的,年青一代理應以高瞻遠矚的眼光、心系天下的胸懷規劃自己的人生,努力為民族復興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2]
(二)擔當精神是青年必備的網絡文明素養
擔當精神是青年群體必備的基本素質。青年一代是國家和民族的未來,青年群體是否愿意擔當時代責任、能否擔當歷史重任,直接決定著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就非常重視青年擔當意識培育問題,在重大場合多次論及“應當培養什么樣的青年”、“為誰培養人才”、“如何培養青年一代”等問題。比如青年要有清晰的自我定位,明確自己的歷史責任,認真扣好人生“第一顆扣子”;時代將光榮和使命賦予了青年,青年應當樹立堅定的理想信念,勇于拼搏和奮斗。此外,在青年成長成才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提出,青年要把握時代賦予的使命和機遇,以勇于擔當、自覺擔當的精神謀劃事業、創造未來;理想信念是青年的人生之“鈣”,絕不能喪失理想信念、患上“軟骨病”,要為偉大的事業和追求付出青春。在互聯網廣泛普及的今天,少量的不良網絡文化對青年一代的思想觀念和價值信仰存在一定的負面影響,導致少量青年喪失了積極進取的奮斗精神和開拓創新的擔當精神。所以,應當將網絡空間作為青年價值觀教育的重要平臺,將擔當精神作為當代青年必備的網絡文明素養。
四、在擔當精神培育中提升青年網絡文明素養
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中提出,網絡空間是現實社會的映射,需要以網絡交往規則、網絡道德秩序等規范網絡生活,否則,虛擬的網絡世界就會變成眾聲喧嘩的“烏托邦”。所以應將網絡空間作為青年擔當精神培育的重要陣地,在網絡空間中培育青年一代的擔當精神,在擔當精神培育中促進青年網絡文明素養生成。
(一)開展價值觀教育,培育青年的擔當意識
在文化影響下,許多青年產生了隨遇而安、無欲無求的人生態度,對國家、民族、社會、家庭等缺乏責任擔當意識,這些給網絡文明素養培育帶來許多負面影響。為此,應將理想教育、責任教育等作為網絡道德教育的重要內容,以網絡媒體、網絡社交等引導青年一代醒吾身、明吾志,促使青年一代以積極進取的態度對待生活、以自強不息的精神應對挑戰。此外,應當在網絡平臺上開展價值觀教育,以誠信、敬業、擔當等道德觀念教育廣大青年,提高青年群體的社會責任意識、敬業愛崗意識等,促使青年群體自覺擔當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比如可以在新浪、搜狐、微信、快手等網絡平臺開展網絡教育,以主流價值觀引領網絡輿論傳播的內容、走向等,不斷提高主流價值觀對當代青年的影響力。[3]
(二)優化網絡輿論生態,培養青年的擔當精神
在網絡空間中草根階層、普通網民等成為影響網絡輿論走向的重要力量,官方媒體、知識精英等反而成為網絡輿論生態中被邊緣化的群體,這種力量和格局的變革深刻影響著網絡輿情傳播,并形成了以主觀化言論、情緒化表達、娛樂化話語等為主的次生網絡輿論生態,而青年群體就是網絡次生輿論生態中的重要力量。網絡次生輿論生態的無序發展必然會影響當代青年的擔當意識培育和網絡素養生成。所以應當引導網絡次生輿論生態的發展走向、輿論導向等,以積極健康的次生網絡輿論生態培養當代青年的擔當意識。比如在重大突發事件發生后,官媒應積極回應網民質疑,與網民進行交流互動,引導網絡次生輿論的發展走向,促使青年網民理性宣泄情緒、表達利益訴求。此外,應當加強對網絡次生輿論的監管,批評各種標簽化、情緒化的網絡言論,引導青年網民理性發表言論、合理表達訴求,促使網絡次生輿情朝著健康有序的方向發展。應當建立網絡輿論信息過濾機制,以信息過濾技術、不良信息屏蔽技術等過濾思想傾向錯誤、思想誤導性強的網絡輿論;應當加強對網絡大v、意見領袖、網絡主播等網絡從業者的監管,引導公眾人物自覺遵守網絡道德底線、維護社會公序良俗。最后,應當為網絡次生輿論營造良好的文化生態。
(三)開展道德實踐活動,培養青年的擔當能力
在青年成長成才問題上,不僅要培養青年一代的擔當意識、開拓精神等,還應當培養廣大青年的擔當能力,以形式多樣的網絡文明實踐培養青年的實踐能力和擔當能力。首先,應當培養青年群體明辨是非的能力。擔當精神培育是以“知道擔當什么”、“懂得如何擔當”等為重要前提,如果廣大青年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就無法擔當時代賦予他們的歷史使命。所以應當開展形式多樣的青年道德實踐教育,將道德實踐教育滲透到網絡文明創建、網絡輿情引導、依法治網實踐等活動中,以靈活多樣的道德實踐中提高青年群體的是非明辨能力。比如可以開展優秀青年、文明青年、青年擔當者等評選活動,在道德實踐中培養青年群體的擔當意識和擔當能力。此外,應當在網絡道德實踐中消解腐朽網絡文化的負面影響,提高青年群體的道德履行能力和社會實踐能力,使青年一點能夠擔當起時代所賦予的歷史使命。[4]
青年一代是民族的希望和未來,青年一代的精神風貌、擔當意識直接決定著民族的前途和命運,青年敢擔當、能擔當,國家和民族就有希望、有前途。所以應當高度重視青年群體的擔當精神培育,將擔當精神作為青年網絡文明素養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