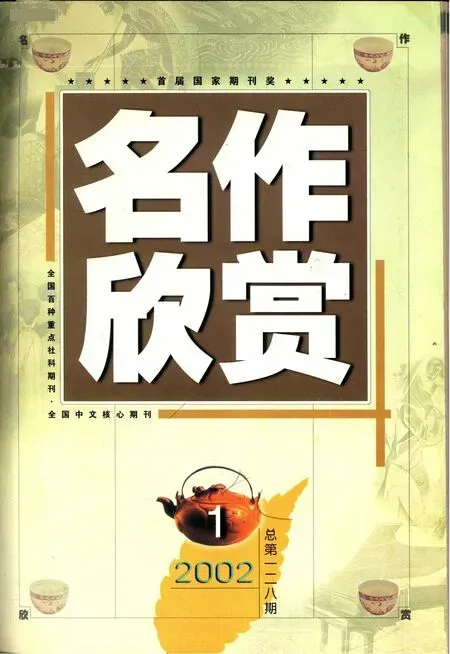真正的影響力取決于價值觀
/ 天津_朵 漁
作 者: 朵漁,詩人,《名作欣賞》雜志文化觀察員,現居天津。
郵 箱:tjduoyu@sina.com
前些天在深圳參加了兩個詩會,討論的話題頗有些相似:一是“當代詩歌寫作的現狀與傳播的可能”,另一個題為“詩神遠游——建構當代中國詩歌國際傳播力”。兩個話題有一種共同的焦慮感,那就是漢語詩歌在當下的影響力問題。
所謂“當代詩歌傳播的可能性”,話題本身即預設了一基調:當代詩歌的傳播是一種不可能的可能。所謂不可能,不僅僅是因為當代詩歌的文化邊緣身份,更是基于詩歌在文化金字塔中的自身定位:詩歌只影響“無限的少數人”,它與普遍的大眾無關。但每一首詩歌、每一個寫詩的人,又都在苦苦尋找或等待它∕他黑暗中的讀者,這種期待又成為某種可能性的動力。就是這么糾結。可能——總是可以找到一堆似是而非的辦法,比如網絡傳播、在公眾面前朗誦等等,這是可能的;但結果依然是不可能——讀詩的人永遠只是那少數中的少數。
詩人韓東認為,“詩歌的傳播”,它在最根本的地方,是不可能的。你不能跑到大街上,揪住一個人的脖子來讀你的詩——如果他對詩根本就不感興趣。但韓東同時也強調,即使當代詩歌不能進行有效的傳播,詩人們也不應拒絕各種傳播的可能性。因為自新時期以來三十多年的新詩發展,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這個成果,怎么和不寫詩的人,怎么和民眾去分享?至少也是一部分詩人,不應該拒絕的東西。因為它確實是一個好的東西”。詩評家姜濤將詩歌的傳播或者是詩歌的公眾性分為幾個不同的層面,“一個層面是指你的詩歌讓更多的人知道,更多人來讀,這是一種所謂的傳播。還有另外一種,就是詩歌提供的一種價值……現在讀詩的人的確不多,但是這種閱讀,恰恰是有價值感的閱讀,不是簡單的觀看和簡單的知道,這是有區別的。”
從一個詩人的角度來講,每個詩人在內心深處都會有幾個理想的讀者,這些“理想讀者”不可能太多,有時可能是三五知己,有時也許就是那一個“她”。我從來不會奢望馬路上的每個人都喜歡我的詩。討好所有人的寫作,肯定是一種變態的寫作。從一個讀者的角度來看,一個詩人的寫作,你到底為讀者提供了什么有價值的東西?你不能平白無故地讓別人愛上你。如果你和那些讀者心靈都沒有溝通,連戀愛都沒有談,再奢談所謂的傳播力和影響力,就是一種撒嬌。
如果說探討“詩歌傳播的可能性”是一種身份焦慮的話,那么“建構當代中國詩歌國際傳播力”就是一種存在感的焦慮。你寫詩,但別人根本看不到你,根本無視你的存在。這種虛無感的吞噬性太強大了。很多詩人嘴硬,說“我們本來就在世界中”,但問題是,“世界”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存在。要讓“世界”知道,這個“世界”就是一個預設的中心。這個中心肯定不在越南或柬埔寨,而是在“第一世界”——一種強勢文化。如何讓強勢文化認同?一個最簡便的邏輯就是:你自身也要強大起來。詩人于堅就認為,目前中國詩歌的“實力”可以說是國家實力的體現。“我覺得中國詩歌要走向國際這個問題,回到最根本的層面來說,從歷史發展來看,有武力就有文化,如果你這個國家非常強大,如果你有武力,你的文化就成為世界標準,如果你是弱小民族,你受欺負,你就沒有什么文化。”如盛唐的時候,長安城就是世界的詩歌之都,許多日本詩人跑到中國來學習。文化標準在某種意義上跟經濟是聯系在一起的,如果你的經濟強大,可能你的文化標準就會得到接受。
但是,這個邏輯又太過便宜。如果一國的文化影響力是由其經濟、武力強弱所決定,那我們就很難理解像波蘭、捷克、立陶宛等等這些東歐小國的詩歌影響力何以如此之大。波蘭這樣一個歷遭劫難的東歐國家,僅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就有四位。我認為,一種文化或文學的國際傳播力,取決于它所提供的價值觀,而非一國之經濟或武力。如果你輸出的價值觀不能為世界人民所接受,再強大的經濟和武力可能都于事無補。
不久前召開的第八屆“作代會”,其主題之一也是要解決中國文學的“國際傳播力”問題。作協無疑擁有巨大的體制資源,是可以做些事情的,但問題是,國際傳播力的建構不取決于你占有多少經濟資源,而是取決于價值觀,就是說你到底向世界輸出了什么東西,這是最關鍵的。在深圳的討論會上,翻譯家高興舉了幾個他親身經歷的例子。他曾多次跟隨中國作家代表團出訪世界各地,一些作家名為傳播中國文化和文學,但一張口還是“文藝為什么人服務”的老話題,根本就與“世界”不在同一個軌道上。這種傳播方式,其實是一種“反傳播”。
在經過三十多年的經濟狂奔之后,“文化”這只紙老虎又被重新提高到國家敘事的層面上來。這是件好事請。無論是“大發展大繁榮”也好,還是“黨管文化”也好,至少已關注到文化在民族復興中的決定性作用。從大歷史的角度觀察,每一個文明板塊的勃興,都與其為人類的共同生活所貢獻的原創性價值有關。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說:“世界歷史從1500年至1830年這一段時期,在西方是以其大量特殊的個性、不朽的詩篇和藝術作品,最深層的宗教動力以及在科技領域的創造而著名的。”而這段時期,正是我們這個日益僵化的東方帝國開始走向沒落的時期。
價值的原創性基礎是鼓勵文化多樣性,并為與社會秩序相容的個人主動性提供最大空間。很難想象在一個僵化的文化環境里,會有什么樣的原創性思想出現。羅素在他的題為“權威與個人”的廣播講座里曾提到:“通過使人馴服和膽怯,我們不可能建立一個美好的世界,而是要通過鼓勵他們勇敢大膽、敢于冒險和無所畏懼來創立一個美好世界。”沒有這樣一個基礎和環境,思想的原創性將很難出現,文化影響力和傳播力更是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