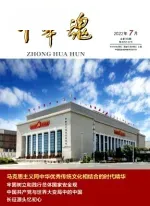經(jīng)濟學(xué)研究應(yīng)該有哲學(xué)家的頭腦
文孔 見
經(jīng)濟學(xué)研究應(yīng)該有哲學(xué)家的頭腦
文孔 見
毛澤東十分重視政治經(jīng)濟學(xué)的理論研究。他主張,經(jīng)濟學(xué)研究應(yīng)該有哲學(xué)家的頭腦。他說:沒有哲學(xué)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jīng)濟學(xué)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qū)懗觥顿Y本論》,列寧能夠?qū)懗觥兜蹏髁x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xué)家,有哲學(xué)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從哲學(xué)的高度研究經(jīng)濟學(xué),才有可能做到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具有說服力。他批評蘇聯(lián)政治經(jīng)學(xué)教科書沒有運用一貫的、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分析事物。
這一段話,切中時弊。當(dāng)前經(jīng)濟學(xué)研究存在許多問題,其中一個毛病就是缺乏哲學(xué)頭腦,停留在現(xiàn)象的描述上,從而不能從總體上、本質(zhì)上把握經(jīng)濟問題。
毛澤東特別重視矛盾分析方法。他認(rèn)為,當(dāng)作一門科學(xué),應(yīng)該從分析矛盾出發(fā),否則就不能成其為科學(xué)。蘇聯(lián)教科書的基本缺點就是不承認(rèn)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認(rèn)矛盾的發(fā)展和轉(zhuǎn)化,不承認(rèn)社會主義發(fā)展的動力還是矛盾。
毛澤東這個論斷對我們研究當(dāng)前的改革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xué)研究的重要內(nèi)容。應(yīng)該看到,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解放、發(fā)展生產(chǎn)力的一種手段。我們不是為改革而改革,而是因為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某些環(huán)節(jié)不適應(yīng)甚至束縛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需要通過改革,調(diào)整生產(chǎn)關(guān)系,來促進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因此,研究改革問題,必須從分析生產(chǎn)關(guān)系與生產(chǎn)力的矛盾著手。我們必須全面地探討社會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與生產(chǎn)力之間的關(guān)系,具體地分析社會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中哪些部分是適合生產(chǎn)力性質(zhì)的,因而必須堅持,哪些部分已經(jīng)不適應(yīng)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需要了,因而必須改革。切忌籠統(tǒng)地講改革,仿佛凡是改革都是對的,都應(yīng)該支持。如果具體地分析生產(chǎn)關(guān)系與生產(chǎn)力之間矛盾的狀態(tài),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社會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基本部分(反映在制度上就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適應(yīng)生產(chǎn)力性質(zhì),能夠解放、發(fā)展生產(chǎn)力的,決不能拋棄;社會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中某些局部性的環(huán)節(jié) (反映在制度上就是具體的經(jīng)濟體制、運行機制)不適應(yīng)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需要,與生產(chǎn)力發(fā)生矛盾,需要進行改革。例如原有的計劃經(jīng)濟體制就是如此。換句話說,改革的對象是經(jīng)濟體制、運行機制,而不是整個社會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確定了這一點,就可以劃清兩種改革觀的界線: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不適應(yīng)生產(chǎn)力發(fā)展需要的經(jīng)濟體制,這是社會主義的改革,因為就改革的內(nèi)容來說,它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把改革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否定和拋棄整個社會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這是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的改革,目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遺憾的是,某些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dǎo)思想的“改革家”在論述改革時,往往不是從分析生產(chǎn)關(guān)系與生產(chǎn)力的矛盾出發(fā),而是從抽象的人性出發(fā)。他們的邏輯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所有的人都追逐個人的私利。必須根據(jù)人的自私的本性來進行“制度安排”。生產(chǎn)資料公有制、社會主義制度是與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相矛盾的。過去我們搞這一套是“人性的迷失”,這是經(jīng)濟發(fā)展的最大障礙,因此必須進行改革,即根據(jù)人的本性來改造社會主義制度。按照這種觀點,結(jié)論必然是:改革應(yīng)該拋棄不符合“人的本性”的公有制、社會主義制度,必須通過私有化恢復(fù)符合“人的本性”的私有制,重新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回到人類文明的正道”。顯然,這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是違反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上并沒有抽象的人性。自私自利,作為一種觀念,屬于上層建筑,它是由經(jīng)濟基礎(chǔ)決定的,而不是永恒存在的“人的本性”。正如馬克思指出的:“人的本質(zhì)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xiàn)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guān)系的總和。”①以抽象的人性論作為邏輯起始點的“制度安排”,只能把改革引導(dǎo)到資本主義化道路上去。
政治經(jīng)濟學(xué)的研究應(yīng)該透過現(xiàn)象找到本質(zhì),這是毛澤東一再強調(diào)的重要的方法論原則。他指出:研究問題,要從人們看得見、摸得到的現(xiàn)象出發(fā),來研究隱藏在現(xiàn)象后面的本質(zhì),從而揭露客觀事物的本質(zhì)的矛盾。人的認(rèn)識總是先接觸現(xiàn)象,通過現(xiàn)象找出原理、原則來。他完全肯定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分析方法,指出: 《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分析,就是從現(xiàn)象出發(fā),找出本質(zhì),然后又用本質(zhì)解釋現(xiàn)象,因此,能夠提綱挈領(lǐng)。他批評蘇聯(lián)的教科書,說它不承認(rèn)現(xiàn)象和本質(zhì)的矛盾。本質(zhì)總是藏在現(xiàn)象的后面,只有通過現(xiàn)象才能揭露本質(zhì)。
當(dāng)前社會主義經(jīng)濟學(xué)的研究存在一種傾向:滿足于描述現(xiàn)象,用現(xiàn)象代替本質(zhì)。經(jīng)濟學(xué)家往往沉湎于一大堆數(shù)學(xué)公式而不揭示這些數(shù)學(xué)公式背后所隱藏的人與人之間的經(jīng)濟關(guān)系;熱衷于描述各種生產(chǎn)要素在配置過程中出現(xiàn)的種種現(xiàn)象,而不揭露背后的各個階級、階層之間的經(jīng)濟利益關(guān)系;詳細(xì)地分析各種工資、獎金形式的利弊,而不研究決定分配方式的生產(chǎn)方式,即“生產(chǎn)條件的分配”;如此等等。所有這些研究工作都是必要的,但停留在這上面是不夠的,用現(xiàn)象的描述來掩蓋事物本質(zhì),更是錯誤的。經(jīng)濟學(xué)的任務(wù)應(yīng)該透過表面現(xiàn)象來研究和揭露人們的經(jīng)濟關(guān)系。
沒有哲學(xué)頭腦,沒有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經(jīng)濟學(xué)研究就抓不住事物的本質(zhì),往往一大篇文章,不知所云,甚至?xí)贸鲥e誤的結(jié)論。這類教訓(xùn),比比皆是。?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