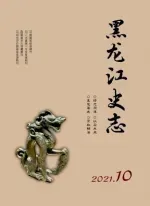一部當代方志人的交響樂——中國地方志協(xié)會學術委員、天津市地方志學會會長郭鳳岐先生訪談錄(上)
邵長興簡介:
邵長興,為遼寧省鞍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離休干部,《當代中國志壇群星集》主編;1988年起主撰《中國地方志十件大事》,從2000年始由《中國地方志》首發(fā)。還主撰《中國地方綜合年鑒十件大事》、《全國新版方志學年鑒學暨相關編著述略》等。他先后出版《西藏高原旅行記》、《邵長興方志文存》、《志域求索》等文集。
“頌其德,贊其才,揚其業(yè)績!”是邵長興為當代方志人樹碑立傳的主旨。方式有八:寫簡介,寫小傳,編群星集,以書系人,以事系人!贊方志人家屬奉獻精神,贈寄語或楹聯(lián),訪談。近年選各類代表人物十位,或晤談或筆談。此文為首批系列訪談錄的殿軍之作。
郭鳳岐簡介:
郭鳳岐 男,漢族,河北藁城人。1941年5月8日出生于藁城趙莊。1965年畢業(yè)于南開大學中文系,1966年2月16日入黨。曾任南開大學中文系負責人、教師,天津市委辦公廳政法處副處長,天津電影制片廠副廠長、編導,天津市地方志編委會副主任、秘書長兼天津市地方志辦公室主任,天津市地方志學會會長。
現(xiàn)為中國地方志協(xié)會學術委員、中國近現(xiàn)代史史料學學會顧問、南開大學客座教授、南開大學地方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天津市口述史研究會副會長、天津市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天津市藝術學會會長。
專著有25部。如《方志論評》,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志苑雜纂》,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天津的城市發(fā)展》,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近代中國看天津叢書·100件歷史大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銀幕上的聲畫藝術—電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
影視作品20部。如《書劍恩仇錄》(上、下集),與金庸合作編劇、監(jiān)制,天津與香港合作拍攝,獲1987年法國巴黎國際婦女電影節(jié)特別獎、香港第七屆金像獎、“十大優(yōu)秀國語片獎;電視劇《心律》(上、下集),編劇,由天津電影制片廠攝制。
發(fā)表散文、隨筆、論文等200多篇。主編、主審志書400多部、約3.7億多字。
先后到美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法國、德國等訪問交流。
多家多次媒體進行采訪、報道。如:《經(jīng)濟消息報》1999年5月31日,以《默默耕耘,無私奉獻》為題長篇報道;《經(jīng)濟消息報》2001年10月29日,以《提高地方文化品位的人》為題的長篇報道;《天津廣播電視報》2001年第20期,以《為了讓天津文化品位長高》為題的長篇報道;《中國改革報》2002年2月9日,以《堅持創(chuàng)新修佳志》為題的報道;《太原晚報》2003年5月25日,以《方志學專家——郭鳳岐》為題的報道;《記者觀察》2003年第8期,以《十二年苦修天津志》為題的報道;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于2003年8月出版的《實現(xiàn)三個代表的楷模》,以“新世紀新聞人物訪談”的形式,對郭鳳岐作了長篇報道;《今晚報》2011年11月9日,《古稀學者的健康“小”理論》為題的報道。
此外,中央電視臺、天津電視臺、上海電視臺、香港鳳凰臺、香港陽光衛(wèi)視臺、天津廣播電臺等,多次對郭鳳岐進行專訪。
長興:2011年,是感天動地的一年。黨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年,也是中共中央發(fā)布《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70周年。《決定》首次指示“收集縣志、府志、省志、家譜,加以研究”,還倡導“寫名人列傳”。天緣巧合,今年恰恰是先生的70華誕,也是從事方志工作20多年,在這樣一個意義深遠的年份,先生想必感慨萬端,可否披露一二?
鳳岐:在這不平凡的一年,的確感慨良多,并有機緣巧合。我們這一代人,雖然沒有趕上那烽火年代,未能親歷那浴血戰(zhàn)斗。但是我們有幸參加了盛世修志,用新編志書如實地記述了革命先驅和烈士們的斗爭史詩。天津是我黨斗爭和辛亥革命的北方中心,有眾多可歌可泣的偉大壯舉和感天動地的英烈事跡。民國時期,天津有多部志書,如《天津縣新志》、《天津政俗沿革記》、《天津志略》等,對我黨在天津的建立、斗爭和辛亥革命活動,皆沒有記錄。這個歷史的重任,歷史地落在了我們肩上。
在《天津通志·大事記》、《和平區(qū)志》、《薊縣志》等志中,我們翔實地記述了那些英雄的斗爭史實。無論黨的斗爭,還是辛亥革命,都創(chuàng)造了歷史。而歷史活動是千百萬人民群眾的壯麗事業(yè)。修志的過程,正是把握千百萬人民群眾的脈搏和歷史前進軌跡的過程。我們從這歷史過程中,既看到了過去,也看到了現(xiàn)在和未來。我們以揮灑天地的大手筆,使那革命史跡第一次入志,讓先驅、先烈的革命精神垂范后世,光照日月。從而讓過去和現(xiàn)今在志書的鏈條上接軌,這不就是歷史的緣合嗎?我已古稀之年,在大事連臺的一年,回想往事,感慨良多。我的生命旅途,工作多變,并有坎坷。有幸參加修志,當無愧此生。
長興:好!鳳岐先生一向出口成章,談鋒甚健,此番高屋建瓴的概括,令人景仰。
俗話說,凡事皆有來龍去脈,我們可否從頭說起,談談您1990年初登志壇的情況,當時面對的是怎樣的局面,您采取了那些舉措創(chuàng)新局面的?
鳳岐:談不到高屋建瓴,一點感慨體驗而已。1990年2月,我步入方志之門前,是天津電影制片廠領導班子中最年輕的成員。在短短的6年時間里,我成功地領導了大型傳奇故事片《書劍恩仇錄》(上下集)的拍攝、后期制作和發(fā)行審批;主持修改了電影劇本《失去的歌聲》,使中途停拍的這部影片拍成、得獎;創(chuàng)作了《書劍恩仇錄》、《心律》等多部影視劇本;為主編導了大型紀錄片《天津新貌》,獲天津魯迅文學優(yōu)秀作品獎;撰寫了《銀幕上的聲畫藝術—電影》專著和多篇論文。從實踐與理論的結合上,為天津電影廠從科教片廠向故事片廠的轉變,作了開創(chuàng)性的奠基。
當時,由于電影制片廠與地方志辦公室,都隸屬市委宣傳部領導,部里把我從已經(jīng)熟悉、喜愛和熱門的電影圈,調到了陌生、清冷的地方志。那時,我根本不懂地方志為何物,也不知道天津有個修志機構,盡管它的大牌子比任何單位都大;盡管我與它的駐地都在一條馬場道上,相距里許之遙。從有聲有色的活動畫面,到枯燥干巴的志稿文字,從一個幾百人的局級大單位,到一個級格未定、二十幾個人,并分派、打架的單位,實在反差太大,簡直難以接受。在40多年的人生旅途中,雖然有過多個角色的轉換,從大學,到機關;從政法界,到影視圈,不如意事常八九,此次變化為最大。
我走入志門時,天津地方志辦,已經(jīng)成立了四五年時間,雖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卻無聲無息,修志工作沒有真正開展起來。為了打開這萬馬齊喑的局面,我采取了一些措施。
首先,是學習方志知識。志辦的人員,來自不少單位。但都未曾接觸過方志,大家(包括我在內(nèi))對方志幾乎為“一張白紙”。不懂方志理論、知識,不可能指導和編修地方志。而專門學習,現(xiàn)實又不允許,只有邊工作,邊學習。我決定從編輯《地方志基礎知識選編》入手,組織了十幾位同仁,把當時能夠收集到的方志著述、論文、刊物,約計幾百篇(部),從中選編出精華部分,經(jīng)我主編審定,終成35言的方志綜合性理論著述,先后出版兩次,不僅是當時天津少有的方志理論著作,是開辦方志培訓班的教材,而且在全國也有較大影響。不少同仁從中學到了方志知識,我也掌握了方志的基本理論,取得了志壇的入門證。
其次,是增加中心區(qū)修志。在原來制定的修志方案中,未包括市內(nèi)10個區(qū)修志,通志又未搞起來,從而形成了只在5個縣打外圍仗,使天津修志在行政建制上出現(xiàn)了中心大空缺。我經(jīng)請示市領導,新增了10個市區(qū)修志。這不僅是數(shù)量的添加,而且中心區(qū)動起來后,才形成了萬馬奔騰的全市修志氛圍。
再者,出版志書鼓舞士氣。我到志辦后,發(fā)現(xiàn)辦公室門后角落里,有一堆志稿。經(jīng)詢問,原來是未完成的《天津簡志》稿。由于辦公室人員內(nèi)部矛盾、辦公室與出版社的矛盾,使花費了四五年時間、每個字約合1元錢的《簡志》,出不了成品,領導很有意見。我把這個志稿拾起來,組織人通審全稿;對稿子差者退回撰稿單位重寫,要求撰稿單位領導審核簽字;最后我參與總纂。并做好單位人員工作,服從出書的大局;協(xié)調與出版社的關系,消除矛盾等。終使《天津簡志》在1991年總纂完成,千呼萬喚始出來。并召開了全市部委辦局領導、專家學者和全市修志人員參加的首發(fā)式,請市委副書記劉峰巖出席講話,使修志人員得到很大鼓舞,并向全市吹響了修志的號角。
還有,召開系列重要會議。我到地方志半年后,組織召開了天津市地方志編修委員會擴大會議,請市主要領導出席講話,重新下達修志方案、部署10區(qū)修志、加快修志步伐。1991年,在天津成功承辦了華北地區(qū)城市志研討會的召開,實際是全國性的城市志會議,對天津修志給與了很大促進。由此,天津修志“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
長興:在方志面向百科,百科走向方志的新形勢下,先生提出“開門修志”的主張,為新志編修打開了一條“金光大道”,愿聞其詳!
鳳岐:先生講“金光大道”不敢說。我們的“開門”修志,是指:既把天津各專業(yè)的頂級專家請進來,又讓修志人員走出去;既編纂新方志,又參加地方文史活動。這樣路子就會越走越寬、越走越活,并把冷板凳坐熱;還可以擴大地方志在社會上的知名度,使方志單位在地域歷史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如果修志“閉門造車”,躲進小樓成一統(tǒng),哪管春夏和秋冬,方志單位就可能成為被人們“遺忘的角落”。
請志外專家參與評稿、纂稿,主要是聽取他們的意見,將內(nèi)循環(huán)與外循環(huán)結合起來,這是開門修志的一個層面;我要求志人主動參與熱點課題的研究,如研究水西莊,從而鍛煉隊伍,使志人既會修志,又會從事研究,并從中搜集了大量資料,包括專家學者提供的史料,使志書的內(nèi)容更加豐厚,這是第二個層面;我們主動參加天津市歷史文化活動,有的活動我們是主辦單位之一,有的活動由我們主辦,每次活動都有我們的重點發(fā)言等。
開門修志,使我們志辦變成了全市明星單位,培養(yǎng)了“天津通”、區(qū)縣通。在社會上具有較強的影響力,在雙實踐中鑄造了強內(nèi)功,在領導、專家和群眾中贏得了聲譽。有作為,才使天津修志走上了“快車道”。一位地方志的主管領導說:“郭君專職修志,大有作為,有了他和地方志辦同仁的‘為’,就不需要我的‘為’了,因為他們的‘為’更有力,‘治’得更好。地方志辦公室如同一部完好的日夜奔馳在大道上的列車,當它走到我的‘站頭’,不需要‘指揮’,不需要‘停車’,不需要‘檢修’,不需要‘加油’,只要給他們開個‘綠燈’,它就會急馳而去。”
長興:在修志過程中,一方面解決用志的問題,一方面創(chuàng)新理論,例如“縱不斷主線,橫不缺要項”的提出,便是一項重大建樹,早已為全國各地所認同,并在實踐中加以運用。請談談您這一重大理論思維的原委!
鳳岐:也許因為我從志外而來,也許因為在時尚的影視圈呆過,對修志的一些規(guī)定、原則和理論等,比較敏感。加上思想比較活躍,有一定的創(chuàng)新意識。例如,在1991年召開的鄭州省級志辦主任會議上,我提出了突破《暫時規(guī)定》、使新志“三貼近”(即貼近現(xiàn)實、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建議。對《暫行規(guī)定》中沒有一席之地的區(qū)志,我積極提倡、親自實踐、大力鼓吹。為區(qū)志這個新秀,登上當代志壇,終成志苑俏麗的奇葩,盡了綿薄之力。
對一些方志理論,我一直在進行探索。地方志作為一門科學,與其他科學一樣,有自己的一套理論和特殊的規(guī)矩。要接受它、認識它、掌握它,即從糊涂到不惑,是難事;掌握后,再突破它,難度更大。以“縱不斷線,橫不缺項”來說,可謂是方志的核心理論。所謂“縱不斷線”,是指志書資料的時間段;而“橫不缺項”,是指志書內(nèi)容的空間面。這種“縱”“橫”結合,經(jīng)緯交織,構建了全方位、貫通性的方志。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縱”“橫”的理論,亦非僵化的、一成不變的模式。“縱”“橫”理論,是新志的特點、優(yōu)點;也是它的缺點、弱點。首輪志書時間跨度長達千年,完全做到“縱不斷線”,幾乎不可能;現(xiàn)在各項事業(yè)發(fā)展,門類眾多,真要做到“橫不缺項”,十分困難。從一些新志問世,所反映出來的“縱”“橫”缺點,更加說明了,真正能做到“不斷”、“不缺”的志書,是鳳毛麟角。我認為,即使做到了,未必是好事,也許是缺陷。這樣會造成志書的“重、腫、平、同”弊端:一部縣志大到150多萬字、重四五斤,如史料雜列、臃腫,往往把重要的事物,淹沒在無足輕重資料的汪洋大海之中;門類與門類之間,平淡無奇,志書與志書之間,“似曾相識”,怎能成為佳志?我市《地震志》送審稿,把30多頁無感地震列入正志中,影響了有感地震的重點,削弱了志書的可讀性,此“不缺項”之弊端。《天津通志·大事記》,從東漢至明永樂初年,長達1000多年歷史,沒有多少史料,若“不斷線”,根本不可能。
由此,我們對“縱不斷線,橫不缺項”的理論,作了修正,加上了“主”和“要”兩個字,將其變成了“縱不斷‘主’線,橫不缺‘要’項”。這就是說,對于縱向的史料,要求不斷主線,并突出事物發(fā)展軌跡的特殊節(jié)點;對于橫向的眾門類,要求不缺要項,并突出本區(qū)縣、專業(yè)的特項事物。
1996年11底,在南寧市召開的全國方志理論高級研討會暨地方志工作經(jīng)驗交流會上,我的發(fā)言是《談志書體例結構的創(chuàng)新》,其中涉及到了“縱不斷‘主’線,橫不缺‘要’項”的話題。會后,中指組領導,要我再展開講這個問題。當時,沒有時間準備,手頭上也沒有資料。便即席專門講了這個題目。大家反映很好。
這就再次告訴我:“物無不變,變無不通”。這個理論的修志,符合實際,使平淡的志書,創(chuàng)新出彩、出奇、出精。正如長興老在《志壇金秋:津門書香縷縷飄九州》大作中所說:北方港口大都會地方志之作“刻意創(chuàng)新,獨領風騷。深入熟諳地情,深入提煉精華……設篇立目突破程式,全志特色燦然如虹。”
長興:方志文化與地域文化在開發(fā)建設方面,其軌跡不盡相同,但也有某些共同點。先生提出要開墾地域文化處女地,志人要自己做嫁衣裳,要有地域文化的話語權,要借巢下蛋構架文化品牌等命題,令人耳目一新。先生在實踐中付出了才智,也取得了驕人的成果,希能扼要作一闡述。
鳳岐:先生說得好!方志文化與地域文化,性質有異,發(fā)展軌跡不同。天津方志人所以能開墾地域文化處女地,主要破解了幾個理念。
第一,方志文化與地域文化有交叉點。地域文化是方志中的重要部類;方志又對地域文化進行歷史地、全面地記述。地域文化的發(fā)展、研究,為方志提供了豐富的內(nèi)涵;方志內(nèi)容又為地域文化的發(fā)掘、建設,提供了厚重的史料。這個交叉點,就把方志文化與地域文化鏈接了起來。
第二,有些地方忽視了自己文化處女地開發(fā)、研究。我這樣說,可能有的人不高興,已經(jīng)搞了幾十年的文化,怎么還有處女地?請聽老外是怎么講的。
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包華石(英文名為MartinPowers),在給新法家中英文版總編輯翟玉忠的一封信中說:“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忽視了自己文化中的一些寶貴的資源,有諷刺意味的是,想用國外的資源時也常常用錯了——不是根本不懂外國的實際情況,就是因為忽視了自己的情況而用錯了。不過國外也有些值得參考的東西,中國知識分子有了自信之后才能理性地使用。”這些話,雖然尖刻、刺耳,難免也有些偏激。但是,中國學者對自己的文化不夠重視、缺乏文化自覺,忽視自己地域文化原點,這是事實。比如,中國約2000多個縣市,有多少地方找到了自己的文化原點?地域文化原點,也是一種原點文化,是文化根基,是豐富的、寶貴的文化資源。
第三,新方志人既是編纂者又是研究型人才。我們編纂了大量地方性文獻,就地情資料而言,比地方圖書館、檔案館亦勝一籌。這些既有教化、資政、存史的功能,又為學術研究提供了豐厚基礎。我曾對天津的志人說:我們掌握著地情資料寶庫,不要滿足于生產(chǎn)“毛條”,不要光為別人做嫁衣裳;還要琢磨生產(chǎn)成衣,并為自己做嫁衣裳。與其讓不熟悉地情的人做“夾生飯”,不如我們一些“地方通”做“可口大餐”。我們方志同仁,不要只會“編”,還要能“研”;既要做編輯,還要做專家。自己手里有糧食,不要以供出去為滿足。既然不怕辛苦、不怕流汗,去播種;還要不怕艱苦、不怕勞累,去耕耘。讓它開出鮮艷的花,結出碩大的果實。我們方志人,不僅要滿足于方志的話語權,而且要爭取有地域文化的話語權。
以天津為例,就利用豐富的方志文獻,連續(xù)開墾了幾個重要文化處女地。
*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利用新舊志書的大量資料,開始開墾天津城區(qū)的文化原點,這是從來沒有人問津的課題。我連續(xù)撰文發(fā)表了《天后宮—天津文化的原點》、《天后宮—天津商貿(mào)的始點》、《天后宮—天津城市的支點》、《東西天后宮建立時間考》、《漕運舶來的直沽媽祖文化》等論文,以及《天津的城市發(fā)展》等專著。論證了天津天后宮就是天津城區(qū)的文化之原點。受到領導和專家的肯定。
*我研究了天津建城時間,這是近600年沒有解決的問題。我連續(xù)撰寫、發(fā)表了《天津建城時間考證》、《天津衛(wèi)城為何建在這里》、《600歲的天津城》、《天津城俗稱“算盤城”》等論文。確定為永樂二年十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日)。一個城市的建立,能精確到了年、月、日,這在我國并不多。并在2004年之前,向市委寫報告且建議,舉行了天津建城600周年紀年活動。
天津衛(wèi)是軍事建制,天津衛(wèi)城的管轄范圍,就是城廂。所謂“城”即衛(wèi)城之里;所謂“廂”,即城外之邊。出來衛(wèi)城東門,西門,便為靜海轄地;出了衛(wèi)城北門、東門,便為武清轄地。天津衛(wèi)城3面環(huán)水,名副其實的地域孤島。而且衛(wèi)的設置,從明永樂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日)設立,一直延續(xù)到清雍正九年(1731),天津設府,附廓置天津縣,縣域管轄增大。前后327年,天津衛(wèi)都是孤島,這種地域的管轄和特點,形成了天津“廂風衛(wèi)俗”文化,以及“方言島”。從而打破了清代淮軍帶來天津方言的長期束縛。
*新世紀以來,打造地方文化品牌活動,在各地迅速發(fā)展起來。浩瀚的志書資料,為地方文化品牌的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各文化單位和有關專家,都在研究天津的文化品牌。我們也在探討、考量。
原來,天津有一個說法,叫“百年中國看天津”。我考慮這樣提法不夠明確,中國的百年有多個,這里究竟指那個百年呢?近代是天津城市重要發(fā)展時期,天津成為近代中國風云變幻的舞臺,許多重大事件在海河兩岸演繹。有眾多近代事物,天津開全國風氣之先。天津堪稱是中國近代歷史的縮影。我考慮天津的文化品牌,應定位于“近代中國看天津”。但是,我們方志部門畢竟不是搞文化事業(yè)的,如何實現(xiàn)這個想法?時人有“借雞下蛋”之說,我可否來個“借巢下蛋”?
機會終于來了,時任天津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的黃興國,要抓天津的文化品牌的構建,召開了專家座談會。會上黃市長一槌定音:“郭先生講的,就是我所想的”。經(jīng)市委、市政府批準,確定了“近代中國看天津”文化旅游品牌。天津市旅游局要編制詮釋這個品牌的板塊,就找到了我這個“雞”,而我需要他們那個“巢”,雙方一拍即合。經(jīng)奮戰(zhàn),制定了12個主板塊、12個副板塊。并根據(jù)黃市長的要求,我與旅游局一名老處長,共同主編了“近代中國看天津”叢書,共4冊:百件歷史大事、百位知名人物、百座風貌建筑、百處名人故居。其中《百件歷史大事》,是我的專著;《百位知名人物》是我與另一先生的合著。這套叢書,裝幀豪華,設計精美,中英文對照,每一頁都有一二幅照片。印制兩版、8000套,基本發(fā)完。生動、形象的解讀了“近代中國看天津”的文化品牌。
今年,“近代中國看天津”叢書獲得天津市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二等獎。天津最大的報紙今晚報,在“近代中國看天津”大標題下,連續(xù)刊載了我的《百件歷史大事》,每天一篇,刊發(fā)了100天。使天津對“近代中國看天津”的文化旅游品牌,深入人心。2010年9月19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聯(lián)播,對“近代中國看天津”文化旅游品牌作了報道。
長興:修志與用志本是一對孿生兄弟。修志的目的,就在于應用。先生主張在修志過程中就解決用志的問題,確是十分高明的提法,煩請舉例說明。
鳳岐:先生說得好,修志的目的,在于應用。問題是如何用?是志書編修完成后應用,還是把用志貫穿修志的全過程,我主張后者。修志與用志是辯證統(tǒng)一的關系,二者相輔相成。修志是用志的前提,用志反過來又會對修志得失進行檢驗和促進修志工作。天津歷史名園水西莊的發(fā)掘、研究正是如此。
我對天津的志書,提出要設“特色篇”。但《紅橋區(qū)修》篇目(初稿),卻平淡無奇,是“似曾相識”之作。要求他們找到自己的特色。有人提出了水西莊,可資料不足,擬深入挖掘水西莊。當時的區(qū)志辦主任不同意,怕影響修志工作。我把主任請到辦公室,做他的工作,說明:水西莊的發(fā)掘、研究,會獲得的豐厚史料,可能形成區(qū)志中水西莊的特色;另一方面,水西莊的挖掘、研究,可動員全市專家學者參與,既能擴大修志的影響,又會收到“眾‘家’修志”的良效。
結果出現(xiàn)了意料中大好局面。天津幾十位專家參與,紅學泰斗周汝昌先生親臨指教,我邀請與水西莊北查同宗的南查的金庸大師蒞津指導,時金庸大師在英國講學,來信說今后有機會到天津,一定去看水西莊。而且,水西莊史實有了重大突破:它是興衰百多年的高雅文化大觀園;是《紅樓夢》大觀園的重要原型之一;少年的曹雪芹曾客居水西莊;乾隆多次駐蹕水西莊,賦詩三首,并賜名“芥園”。
周汝昌先生對水西莊寫了多篇文章;后來金庸先生到南開大學講學,特意去看水西莊,并題了詞;天津許多專家撰寫了水西莊的文章。我開始寫了《水西莊與地方志》,刊于今晚報;既而撰寫了《天津文人文化的輝煌代表——試論水西莊的文化現(xiàn)象》,刊于《天津文史》,在社科聯(lián)評獎中,被專家們視為“金子”,評為一等獎;此后,我為國家圖書館錄像講了《水西莊》,共十講,全面介紹了這個文化大觀園;《紅橋區(qū)志》將水西莊作為專編記述,形成了區(qū)志亮麗的特色篇,水西莊的豐厚資料,為其復建提供了堅實的史實基礎。《紅橋區(qū)志》被評為中國地方志一等獎和天津社會科學著作二等獎,是天津市政府獎中唯一的一部志書二等獎。
長興老在《讀<紅橋區(qū)志>兼談天津市修志工作領導風范》大作中說:“對應歷史文化名城,自當列出與之相適應的典型事物……還有‘歷史名園水西莊’。這一連串足以令紅橋人引以自豪與驕傲的勝跡,儼然一串串珍珠瑪瑙,熠熠生輝,讀者也為之眼前一亮。”
水西莊的研究,影響人們對天津城區(qū)文化的重新認識。長期以來,天津城市文化被一類話語權所控制:起初說“文化沙漠”,后來說“文化積淀不深厚”,現(xiàn)在說是“俗文化”。從水西莊研究和《紅橋區(qū)志》編修、應用,使歪曲的天津文化開始終結。
繼而,我們又不失時機,在修志過程中,利用志書的文獻,策劃、編輯了一套《天津文化通覽》叢書,基本完成了10冊,我并起草了一份重點論述天津地方文化定位的序稿,請時任天津市長的李盛霖批準作序。由此,天津地方文化的定位,有了一個明確說法。要點是:“天津開放性發(fā)展的獨特性,社會變革誘發(fā)的突變性,經(jīng)濟活動衍生的多樣性,以及城市功能拓展的漸進性,決定了天津地方文化包容吸收的特征,多元文化的構成和與時俱進的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