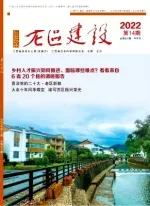思政工作的英國經驗:讀《英國安茹王朝議會研究》有感
劉婷婷 傅小兵
一名優秀的思政工作者,既要及時總結工作經驗,也要不斷加強理論學習;既要有針對性地閱讀思政教育類的著作,也要有選擇性地涉獵其它學科的成果。近讀余永和的新著《英國安茹王朝議會研究》讓我頗有收獲。該書在系統梳理學界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早期英國議會的發展脈絡、主要制度、實際職能與歷史影響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尤其在議會與王權的關系上提出了獨到的見解[1]。捧讀全書之后,我除了對早期議會的憲政地位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外,還深感早期議會作為當時英國各派政治勢力進行思想交鋒與政治協商的場所,其運作中的一些成功經驗為我們今天思政工作提供了有益啟示。
一、搭建溝通平臺
西方關于中世紀議會史研究主要體現為兩大學派的分野:憲政主義史學派片面夸大議會主權,突出議會對國王的遏制與約束功能;修正學派則刻意貶低議會職權,強調國王對議會的主導與支配地位。作者則在國家宏觀政治系統的視野下看待中世紀議會,指出議會與王權并非二元對立此消彼長的關系,而是順向共生共同發展的關系。中世紀英國議會是由國王召集的由教俗貴族及地方代表(主要包括騎士與市民代表)參加的議事機構,因有選舉產生的地方代表參加而有別于之前的御前會議,因仍是隸屬于國王的封建機構而有別于近代意義的議會[1](P46)。議會作為國王召集的由教俗貴族及地方代表參加的會議,既是國王順利施政和強化統治的重要工具,也是教俗貴族參與政務和拱衛王權的封建機構,還是地方代表申訴冤屈和領受賦稅的政治場所。也就是說,議會為國王、教俗貴族與地方代表搭建了相互溝通共同協商的平臺。國王雖然對議會具有支配地位,但貴為一國之君,處理諸多國事必須經過議會的程序,雖然被有的學者視為走過場,但能夠搭建與教俗貴族尤其是全國各地的代表進行溝通的平臺,無疑有助于化解諸多民怨減少施政阻力。王國政府的大政方針獲得議會同意后,也更能贏得各方的支持與理解。
搭建平臺也是思政工作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在一些單位的思政工作部署中,比較重視思政工作者的個人素質,而忽視思政工作的平臺建設。不容否認,有的思政工作者政治過硬,作風優良,手段靈活,方式多樣,也經常深入基層,了解思想動態,傾聽多方意見,這些當然是值得肯定之舉,但如果未能構建固定平臺,僅靠工作人員的“一己之力”難以保證思政工作的長效性、持久性、穩定性。很多地方往往是人員一調走,思政工作的程序與作風就隨之“變臉”,許多工作也只好半途而廢。
二、完善制度建設
英國最先產生議會固然有其特殊的社會歷史機緣,但也與議會自身不斷完善制度建設密不可分。早期英國議會與法國三級會議類似,但發展結果迥然有異:法國三級會議后來幾乎流于形式,而英國議會卻不斷成長,這得益于其一直努力完善各項制度,形成規范,逐漸確立了自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很多人譏諷早期議會類似橡皮圖章,沒有實權,但議會卻非常珍視來之不易的地位與角色,即使是橡皮圖章,蓋起來時也顯得有模有樣,終究將橡皮圖章演變成權力大印。14 世紀時,議會的召開時間、召開地點、召開頻次、與會人員就趨于制度化。盡管議會何時召開主要取決于國王,但通常會根據法庭的開庭日期來決定議會的召開日期,會期一般為2—3 周。議會召開地點逐漸固定在威斯敏斯特,因為附近的倫敦可以提供可靠的后勤保障與強大的輿論支持,當然這在無形之中也加強了倫敦作為首都的地位。國王還發布公告,議會召開時,禁止任何人在當地穿戴鎧甲或攜帶武器,禁止所有擾亂議會討論的娛樂活動[1](P102)。至于與會人員,國王的官僚集團一度主導議會,但最終除部分高官外,非貴族的官僚逐步淡出議會。教會人員中,低級教士與會頻次越來越低,乃至脫離議會;高級教士與世俗貴族一起,構成了上議院。以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等構成的世俗貴族勢力強大,成為議會中的重要力量。此外,每郡選舉兩名騎士代表,每座城市選舉兩名市民代表,這些地方代表構成了下議院。兩院之間既分立,又有聯系的管道。議會召開頻率也趨向穩定,除非特殊情況外,議會都能逐年召開。議會的召集制度、選舉制度、工作程序、組織制度與議長制度也不斷完善,這都大大增強了議會的地位。可以說,中世紀歐洲大陸諸國很多等級機構最終湮沒無聞,唯有英國議會,能由當初名不經傳的非常設性機構,逐漸演變為國王處理政務的重要助手,并且在近代一躍而成為國家的權力核心,個中緣由當然復雜,但議會緊抓制度建設無疑功莫大焉。
制度建設在我們當前思政工作中同樣不可小覷。一些思政工作者雖然不乏新點子、新招數、新方式,但由于頭緒眾多,任務繁雜,責任重大,如果缺乏整體考慮與全盤規劃,沒有形成完善的機制,還是難以保證收到實效。靠偶爾大搞突擊戰、運動戰、攻堅戰,或許短期內容易取得戰果,但畢竟難以持久,成效也可想而知。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科學的規劃和系統的設計,加強思政工作的制度建設,使思政工作走上科學化、規范化與制度化的軌道。
三、凝聚各方共識
作者論證了中世紀議會并非國王的異己機構,盡管表面上似乎對王權構成一定的約束,但實際上卻強化了以國王為首的王國政府的公共權威。國王、貴族與地方代表之間有分歧與矛盾,但并不尋求單純對抗或壓服的辦法去解決,而是采用協商與妥協的方式達成共識。議會開會期間,各方都有表達意見的機會。國王一般會親自出席議會開幕式,甚至作即席發言,表達體恤臣民之意。官員在開幕詞中通常會陳述國王面臨的難處,提出財政要求,希望提供資助,還有就是承諾糾正冤屈,希望議員把人民訴苦的請愿狀遞來。議會書記官宣布請愿書接收員與審理員名單。議員遞交的請愿書分為個人請愿書與公共請愿書。個人請愿書大多涉及私人利益,經常是請愿者整理好一系列請求,逐條記錄在一份請愿書上;個人請愿書最初是呈交給立案官,由審判法庭予以答復,復雜問題轉交議會委員會裁決。公共請愿書則攸關公眾福祉,以下議院集體的名義提出,經議會書記官呈交國王與議會委員會[1](P149)。接下來議會再分組討論,所有需要解決的問題都提交各個討論組。議決過程中還建立了一些委員會,甚至針對單獨的議題,也會設置專門委員會以進行詳細討論。議員逐漸贏得自由發言權。經過分組討論,在全體會議上形成決議后,議會便告解散。也就是說,議會是在充分聽取各方意見后,經過輪番討論,最后達成一致,再下達到地方。
同樣,由于思政工作的對象較多,興趣多元,需求不一,凝聚共識形成合力就顯得尤其重要。思政工作者如果忽視個體差異,單純采取自上而下集體灌輸式的教育方法,甚至頤指氣使,動輒訓誡說教,只會事倍功半,甚至適得其反,產生負面效應,引發不滿情緒。思政工作要少走彎路,必須牢記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理解群眾,幫助群眾的法寶。思政工作者要堅持把解決思想問題與解決實際問題相結合,多傾聽群眾的意見,了解群眾的實際困難與切身需求,想方設法為他們排憂解難。“做思想政治工作如果不注意解決群眾的實際問題,思想教育就會脫離群眾,難以收到實效”[2]。思政工作者要盡力營造集思廣益、群策群力、共同發展的和諧環境,思政工作的對象也要積極轉變角色,由被動接受者轉為主動參與者,主動建言獻策,形成思政工作“人人參與,個個共享”的良好氛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總結包括英國在內的他國經驗,對于加強與改進我們的思政工作無疑有所裨益。
[1]余永和.英國安茹王朝議會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2]李紅.新時期思政工作方法創新淺析[J].民營科技,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