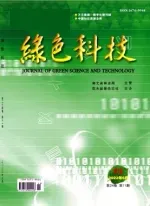清潔發展機制對我國環境保護的作用研究
吳穹
(吉林省長春市環境工程評估中心,吉林 長春130000)
1 引言
《京都議定書》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補充條款,其主要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明確各國對控排溫室氣體應擔負的責任;另一個方面是為了促進實現減排目標,提出了“清潔發展機制”、“排放貿易機制”和“聯合履約機制”的三靈活機制。其中“清潔發展機制”是一種促進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的模式,以求達到共同的減排效果,尤為引人注目。
2 “清潔發展機制”的內容
“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簡稱CDM),是由《京都議定書》第12條設計、規定的一種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控排溫室氣體領域協作雙贏的新穎模式。主要可以理解為發達國家提供經濟援助和技術扶植,和發展中國家實施多方合作,也就是同意履行控排義務的國家,在另一國投資可以減少釋放量的項目,但減下來的釋放數字允許歸回投資國,主要是來沖抵其本身的減排義務。這樣良好的新型模式對于帶動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合作、實現節能減排的目標體現出十分深遠的意義。研究資料表明:明確了各國對控排溫室氣體應擔負責任;CDM與ET(排放貿易機制)兩者都是實施減排溫室氣體的較好手段,它把減排數額看成是能夠進行買賣、交易的特殊產品,吸引經濟比較發達國家的政府和企業把雄厚財力、先進技術投入到減排溫室氣體的行動當中。綜上所述,第一個機制能夠使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CDM合作中都獲得相應的利益,在全世界又有利于實現《京都議定書》約定的減排任務,在國際領域開辟了國際投資、貿易的創新領域和新型模式。
3 “清潔發展機制”的法律性質分析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講,“清潔發展”機制可以說是一種激勵制度,是與發展中國家關系最密切的機制。《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把締約方劃成兩類國家,附件I締約方涵蓋了西方發達國家和前蘇聯、東歐轉型國家;非附件I締約方則主要是一些發展中國家。《京都議定書》依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規定,對所有成員量身定做了各自的責任和權利。前者有詳細、并且體現拘束力的減排目標,后者相反卻沒有強制性的減排規定,獲得了京都機制所帶來的溫室氣體釋放降低的公共產品,可是它承擔的履約成本卻較前者小很多。按照《京都議定書》的要求,在清潔發展機制下,發展中國家則得到了來自發達國家的龐大環保項目的經濟援助和技術支持,一方面在環境保護上取得利益,另一方面也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百利而無一害。對那些那些加入《京都議定書》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這個政策一方面給其帶來了公共產品;另一方面也給其帶來了獨特的正面激勵。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講,即使當下發展中國家不履行減排義務,并不表示發展中國家不履行防止氣候惡化的成本任務。“清潔發展機制”是一種促進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的模式,以求達到共同的減排效果,尤為引人注目。半導體工業和電子工業的日益興旺也極大地提高了以中國、印度、巴西為主的發展中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事實上,發展中國家變為所有產業鏈中的生產基地,向發達國家出口成品,他們排放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是在為發達國家“買單”。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正在經歷經濟飛速發展的關鍵階段,重工業燃煤釋放出的CO2量與日俱增,并且,發達國家逐步向我國遷移數量眾多的鋼鐵等重污染工業,吸納的項目質量雖然比以往要高一些,然而在資源利用與環境污染等角度,國際標準與日提高,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也愈來愈遠,造成了“引進、落伍,再引進、再落伍”的非良性循環。假使不迅速調整產業結構,假使不開展跨越式綠色發展,在第三個履約期逐步減排的同時,發展中國家一定會付出沉痛的代價,試想一下后果可能會給那些首先考慮發展的發展中國家造成龐大的負擔和壓力。
4 “清潔發展機制”對我國環境保護制度的作用
當下,即使發展中國家還沒有擔負起實質性的減排責任,但并不表示發展中國家束手旁觀。為數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印度等國,數額龐大的溫室氣體實際釋放量、與日俱增的釋放增長速度以及氣候惡化難題的越來越嚴重,讓其陷入到出自國內、國際的諸多壓力之中,發展中國家的實際釋放水平日益增長。
(1)為了應對后京都時代的挑戰,我國應大力運用《京都議定書》的靈活機制。最重要的是利用投資和技術轉讓的方式,同相對不比較發達國家合作實施清潔發展項目。一方面可以和本議定書體制內的歐盟和日本合作,另一方面也能夠同那些在本議定書體制外的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合作。首要條件是把好國內引進項目的法律和技術關,擇優選擇,使得那種環境和經濟效益都不錯的項目落戶中國,最大程度的力避吸納污染嚴重、能源消耗大的項目,將低碳經濟作為國際合作的核心要素。
(2)項目合作并不是唯一有效的措施,目前,發展低碳經濟也為很多國家所青睞。2003年,英國政府提出新的名詞-低碳經濟,隨即歐盟、日本、美國等國陸續出臺了發展低碳經濟的相關策略,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等經濟轉型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也日益進行低碳經濟策略的探討和任務的部署。我國應緊跟時代潮流,大力發展高新技術,實現新能源與可替代資源的開發,發展低碳產業,走低耗高效的綠色發展道路。
(3)致力于制定一系列法律和政策,盡快建立健全我國國內以《大氣污染防治法》為核心的法律法規,并出臺相關體制和行動方略,促進國內相關產業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雖然人類解決嚴峻的環境問題征途漫長,但在國際社會的積極合作和努力下,在眾多有效機制的影響下,實現高能效、低排放的轉型,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將不再是奢望。
[1]張 磊.從哥本哈根會議看全球氣候合作前景[J].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10(4):64~65.
[2]周洪鈞.〈京都議定書〉生效周年評論[J].法學,2006(3):237~238.
[3]莊貴陽,陳 迎.國際氣候制度與中國[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
[4]李摯萍.環境法的新發展——管制與民主之互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