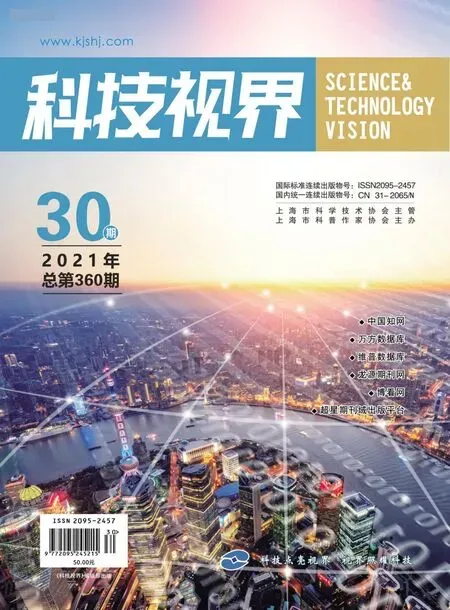佛教、苯教、藏區社會:康寧漢藏學研究論述
申曉虎
(曲靖師范學院 云南 曲靖 655011)
康寧漢(R.Cunningham)系中國內地會傳教士,于1921年自倫敦來華。1922年,因原駐四川打箭爐 (今甘孜康定)的徐麗生(Theo Sorensen)回國休假,被差會指派接替其工作。后加入華西協合大學華西邊疆研究學會,與名譽主席葉長青(J.H.Edgar)共事于打箭爐。葉長青1937年去世后,康寧漢繼續從事康藏地區宗教研究工作,相關結果發表于《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志》,20世紀40年代中期離開中國。
康寧漢以打箭爐為中心,數次前往周圍德格、理塘、巴塘、鄉城等地游歷考察,重點關注藏傳佛教的教義與理論體系,宗教對當地社會及藏族傳統文化的影響,分了析苯教與佛教之間的關系。
1 對藏區社會的認識
康寧漢于1922年來到當時被稱為“川邊”之地的打箭爐,利用之前內地會傳教士徐麗生創造的條件,繼續宣教事工。當時的打箭爐連接西藏與內地,是川邊政治、經濟與軍事重鎮。康寧漢在報告中對打箭爐的地理環境與名稱的由來進行了描述:“打箭爐海拔9000英尺,四周雪山環繞,為兩河匯流之處……打箭爐藏語為‘Dar dzen do’,Dar和Dzen表示兩條河,而Do表示交匯之處。藏區許多地名都以Do為結尾。”[1]傳統觀點認為打箭爐的藏語音譯為“打折多”,指折多河與雅拉河匯合之處,亦有觀點認為“打折多”指“以箭桿矗立的郭達山為標志的三山環抱二水夾流之地”[2]。清乾隆年間出版的《衛藏通志》中關于此地名由來的描述為“打箭爐未詳所始。蜀人傳諸葛武鄉侯亮鑄軍器于此,故名”[3]。由此可知,康寧漢對地名的解讀,明顯受田野考察影響,而非源自漢文典籍。
康寧漢對康藏地區社會的考察,始于傳播基督教的考量。為熟悉環境,了解受眾情況,康寧漢在藏族向導陪同下,前往康定周圍地區考察,記錄了沿途見聞,為后來者留下描述當時社會情形的生動記載:
我們通常在村子附近扎下帳篷。村里的頭人負責提供食物;人們為我們帶來水、食物和木材。照顧我們的藏民被稱為烏拉(ulag),他們以這種服務代替交稅……在旅行中騎未馴服的馬很危險。有一次兩位藏民拉著一匹馬,我妻子剛把一只腳放在馬蹬上,馬就像閃電一樣跳開了,我實在是害怕藏區的馬[4]。
康寧漢所提到的烏拉,指藏區由民眾提供的特殊勞役制度,主要為交通運輸服務,應差者稱為“差巴”,所承擔義務在清代始有詳細規定。清末經趙爾豐改革,以土地大小與牲畜多少作為劃分烏拉承擔數量的標準,將差民分為人差、牛差和馬差三等[5]。烏拉使用權先后控制土司和地方政府手中。葉長青于清末亦前往康區考察,他對烏拉制度進行了解讀,認為“獲得道路附近一片土地租種權的當地人,有義務承擔從某個驛站到下一個驛站的運輸任務……從理論上講這個制度沒有什么不妥之處,但它被當權者濫用,成為某些人賺取利益的機會,而官道沿途不斷增加的廢棄驛站體現了這個制度的失敗。”[6]相較之下,雖然對原因分析仍有不足之處,但葉長青認識到了烏拉制度的弊病。清末康區烏拉制度中差民所承擔的義務與土地之間的不平衡狀態日益嚴重,因而造成大量差民逃亡,躲避差役。至民國初年,往來交通已陷入困境。后經劉文輝改革,始有恢復。
康寧漢在考察中,對當地藏民的描述中存在頗多偏見,甚至錯誤之處。如在其早期的記述中,他提到“藏民大多無信義、迷信而無知,喜好飲酒……他們無意讀書或花時間看書,我們周圍的許多喇嘛認字,但很難找到一位能聽懂內容的人。”[7]就其原因而言,康寧漢早期的傳教工作因文化差異、語言不通等諸多原因進展受阻,他對藏民的認知產生偏差。另一方面,外出考察必用烏拉,而外國人本無權使用之。地方當權者為利益驅使,大多為其提供“便利”,“宰客”現象時有發生。康寧漢數次遭遇此情形,故有“無信義”之語。
2 對藏傳佛教的認識
康寧漢對康藏地區藏傳佛教的認識,經歷了兩個階段:早期對寺院、僧侶群體及其影響的直觀感受,后期對藏傳佛教歷史、理論教義的宗教學研究。
2.1 早期研究
康寧漢對寺院的考察,多集中于打箭爐。他在報告對城中的寺院與僧侶群體進行了描述:
打箭爐的寺院分屬格魯派、寧瑪派和薩迦派……在這些寺院中,一般約有400名左右的喇嘛。街上民居中住著約100名 “阿珂”(Amcho),即讀經僧,人數變化大,但整個打箭爐的喇嘛人數維持在500人左右……打箭爐有七大寺院,安覺寺、金剛寺、南無寺、薩迦寺等。最大的寺院安覺寺有120名喇嘛,可能是城中最大最富有的寺院。這些寺院不僅是藏傳佛教的中心,也是大量的商業機構、銀行和貿易中心……藏區的行政、民事或宗教事務從來都不是非常復雜。寺院通過直接而簡單的方式控制著每戶人家、每頂帳篷[8]。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對直觀感受的描述,康寧漢還認識到藏傳佛教寺院政治、經濟等社會功能。作為藏區政教合一制度核心的寺院,除宗教功能外,本身亦承擔其他重要的社會職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政治功能。寺院擁有莊園、牧場、所轄人群的司法權,與地方政府和世襲貴族相結合,控制權力。第二,經濟功能。因占用大量生產、生活資源,寺院通過放債、經商,控制地方經濟命脈。第三,文化教育功能。寺院擁有豐富的藏書,加之受過宗教教育的僧侶,既作為藏區主要的文化交流場所,也充當教育中心[9]。
在早期對藏傳佛教的研究中,受基督教神學思想與西方文化中心論的影響,康寧漢對之有諸多誤解,其結論也有許多錯誤的地方。如他對寺院與僧侶群體的論斷中提到:“藏傳佛教呈現高度組織化的特色,以無知、拜偶像和迷信維系自身。實際上其中并無真正的宗教可言。在這個由身著紅色衣袍,成百上千的僧人構成的龐大社團中,沒有人得到真正宗教性或屬靈的呼召,他們不受道德約束,終日無所事事,晚間尋歡作樂。”[10]在作為傳教士的康寧漢看來,“真正”的宗教,即信仰上帝,而不是佛教中的所謂“拜偶像”。在此,康寧漢以傳教士的視角對藏傳佛教進行解讀,其結論無疑存在諸多謬誤。同時,以研究宗教現象,揭示宗教發展規律的宗教學學科在當時仍處于早期發展階段,作為未接受正統學術訓練的康寧漢,亦很難跳出基督教神學思想的窠臼。
2.2 后期研究
1922年,戴謙和等一批外國人類學、醫學、地理學專家在華西協合大學成立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旨在從事華西民族歷史、宗教習俗與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抗戰時期,大批海內外知名學者亦加入其中,推動了華西邊疆學研究的發展。受其影響,康寧漢的學術研究日益成熟,專注于藏傳佛教歷史、教義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過去思維的限制,轉而以人類學的視角對問題開展研究。
在《藏傳佛教起源》(Origins in Lamaism and Lamaland)一文中,康寧漢嘗試以學術的眼光來看待藏傳佛教的本質,并提出疑問,即如何定位藏傳佛教,是宗教、文化、哲學還是道德標準。在論述宗教歷史議題時,康寧漢準確地認識到了藏傳佛教的發展歷程,并簡要分析了四大教派的由來與特點:
寧瑪派又稱古舊派,或稱之為紅教,由蓮花生大師(Guru Rim-boche)所創……赤松德贊(Trisong Dehdzen)決定消滅藏區的薩滿與萬物有靈論,當聽到這位大師住在印度北部的奧金,便派遣一隊隨從前去請他來拉薩……蓮花生大師創立寧瑪派,旨在反對苯教。宗喀巴(lozang draba)創立格魯派時,主要反對佛教內部仍然存在的巫術……從蓮花生于公元749年創立藏傳佛教以來直至宗喀巴1400年間的宗教改革,這段時期藏傳佛教內部出現了諸多改變與革新……“七覺士”時期寧瑪派如日中天,其后薩迦派占據了世界屋脊的主流……公元1400年后,宗喀巴又成為響當當的名字[11]。
康寧漢對藏傳佛教歷史的記述,基本把握了歷史的脈絡,但細節部分存在不少問題。如格魯派的創立:一方面,因為當時僧俗界限混淆,僧人群體威望下降,僧侶對立;另一方面,宗教社會凝聚力下降與依托于宗教的政治發展之間存在矛盾,故要求宗教革新、恢復宗教純正以重新增強社會凝聚力[12]。
在分析藏傳佛教何以在藏區傳播發展的原因時,康寧漢將之歸結于地理環境對宗教的影響。他認為“藏傳佛教有可能是佛教適應藏區高原氣候與地理條件的產物嗎……在物質條件有限的情況下,受其影響,藏區居民接受佛教禁欲的理論,即擁有世間財物將使人沉溺于現世、欲望、不幸、痛苦與死亡。”[13]在論及寺院與之的關系時,他認為“寺院吸收大量人口的原因只能用地理控制來解釋。許多加入寺院的兒童是因為父母的意愿……藏區商業或手工業不可能像寺院那樣吸收如此之多的人口。”[14]
為進一步了解藏區文化,康寧漢向當地一位名叫羅桑土登的喇嘛學習藏文與藏傳佛教知識。在此基礎上,他對藏傳佛教中的活佛轉世制度進行了解讀。康寧漢認為:
對白天放牧、夜晚做美夢的牧人來說,轉世是神靈對世人的顯現。對有文化、受教育的喇嘛而言,轉世有著神圣的價值,其意義有時難于理解……總的說來,轉世有三種形式。一是靈魂可以花數月或數年來尋找新的身體或者并不成功;二是靈魂直接離開舊的身體進入新的身體;第三種是介乎兩者之間……轉世制度在藏區通行無阻,亦會產生更多的轉世活佛[15]。
由于文化背景與知識體系的局限,康寧漢并未對此議題有較為深刻的認識。活佛轉世制度衍生于佛教轉世、三身學說,在藏區特殊的社會環境中,起到了保持和發展宗派與寺院既得政治、經濟地位,解決首領繼承問題的作用。
康寧漢也對藏傳佛教真言“嗡嘛呢叭咪吽”有過描述。他在文章中提到:“信徒們搖動轉經筒口誦真言,將真言印在經幡上,刻在石頭上……無論理解其真正含義,在藏區沒有人懷疑真言能夠使人從此世中解脫出來。我們的一位受過教育的年老喇嘛堅信佛陀本人將真言帶到藏區。對他而言,真言就是藏傳佛教的精粹……藏傳佛教與真言息息相關,如果用一句話來描述藏傳佛教的話,那么我們能找到的唯有這六字真言了。”[16]
康寧漢對藏傳佛教的研究,更多地是從神學理論的角度進行解讀,并未用人類學、社會學的理論加以解釋,與同為邊疆學會成員的李安宅等人相比,其分析過程與結論顯示出學術訓練的不足與視域的局限。
3 對苯教的認識
對藏族傳統宗教的苯教,康寧漢亦給予了一定程度的關注。康寧漢將苯教視為藏族先民自然崇拜(nature worship)、薩滿(shamansim)或萬物有靈論(animatism)的產物。他認為:“苯波或黑教,作為一種萬物有靈論的宗教在松贊干布之前的藏區十分盛行……諸多證據表明,松贊干布之前的藏區宗教幾乎全是充滿薩滿信仰和萬物有靈論。至今仍留有許多證據證明藏區仍舊如此。”[17]同時,他認為苯教是薩滿與萬物有靈論融合的結果。
苯教在早期發展階段,無疑呈現自然崇拜與萬物有靈論的特點。但苯教在后期借鑒佛教理論體系,結合自身傳統,編寫經文,已形成系統化的宗教理論體系,實現從原始苯教向制度化的雍仲苯教的轉化。康寧漢只關注到苯教中遺留的有萬物有靈論因素,卻沒有提及已組織化、制度化的雍仲苯教。
同時,康寧漢也研究了藏區佛教與苯教的關系。他采用神話敘事來表達對苯佛關系歷史的認知:“赤松德贊在蓮花生大師到來之前,數次試圖興佛驅魔。有一次他建造一所寺院,但魔鬼總是晚上前來,把白天建造的成果毀掉。赤松德贊將之歸咎于魔鬼,但有謠言稱是苯教在與他作對……當蓮花生建立寧瑪派時,其主要的目標就是毀掉舊有的苯教及其薩滿信徒……時至今日,川藏地區的格魯派、寧瑪派和苯教共處一地,共同擁有活佛轉世系統,使用驅鬼、治病的儀式。”[18]
康寧漢對苯教的認識,基本代表了華西邊疆研究學會學者對苯教的看法。對于佛苯關系的解讀,更多地反映了傳教士對宗教間關系的直觀感受。值得注意的,身為學會名譽主席的葉長青,是所有成員中對苯教認識最為深刻的。他撰文對苯教的起源,苯教祖師辛饒米吾及其出生地之間的關系,以及苯教苯教八字真言Om ma dri mu ye sa le`dug進行了分析,其結論至今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19]。
4 結語
康寧漢對藏區社會的考察與宗教的研究,應置于國外藏學發展歷程的大背景下加以審視。國外學者對藏區社會的考察最早可追溯到17世紀天主教傳教士對藏區的探索。19世紀30年代,匈牙利人喬瑪(Alexander Csoma de K?r?s)所進行的研究,被學界視為藏學研究(Tibetology)的發端。20世紀初至40年代,華西邊疆研究學會利用地利之便,對康藏地區開展考察,其研究成果涉及藏區民族、宗教、歷史等方面,并利用英文刊物,發表學術成果,推動研究。該學會前期研究主力多為諸如葉長青、康寧漢、葛維漢等外國學者。抗戰以后,李安宅等中國籍學者逐漸掌握主導。20世紀中葉,法國巴考(J.Bacot)、英國托馬斯(F.W.Thomas)與意大利圖齊(G.Tucci)等人著作問世。50年代以后,美、英、法、日、意等國相繼成立藏學研究機構,并舉辦相關學術研討會,促進了世界性藏學研究的發展。
康寧漢等華西邊疆研究學會學者的藏學研究,正處于國外藏學研究的早期。盡管康寧漢未接受過正規的學術訓練,作為傳教士對其他宗教的看法難免有失偏頗。但是,康寧漢對藏區社會的考察,對藏區見聞的記載,為后來者留下了珍貴的一手資料,研究成果亦反映了當時外國學者對藏區社會的認識與觀點。同時,康寧漢及其他學者的研究,也推動了“華西學派”的形成與發展,為西南地區人類學研究創造了良好的學術氛圍與堅定的基礎。
[1]R.Cunningham.A Religious Stronghold[J].China`s Millions,British ed,1932(10):210.
[2]馬月華.打箭爐的傳說及地名芻議[J].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3):101.
[3]衛藏通志[M].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133.
[4]R.Cunningham.Camping Out Among Tibetans[J].China`s Millions,British ed,1926(5):72.
[5]胡曉梅.康區烏拉制度研究[D].四川大學,2003:17-19.
[6]J.H.Edgar.The Marches of the Mantze[M].London:China Inland Mission,1918:62.
[7]R.Cunningham.Camping Out Among Tibetans[J].China`s Millions,British ed,1926(5):73.
[8]R.Cunningham.A Religious Stronghold[J].China`s Millions,British ed,1932(11):211.
[9]丹珠昂奔.藏區寺院的社會功能及其改造[J].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2(6):42.
[10]R.Cunningham.A Religious Stronghold[J].China`s Millions,British ed,1932(11):210.
[11]R.Cunningham.Origins in Lamaism and Lamaland[J].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1938(10):178-180.
[12]石碩.格魯派的興起及其向蒙古地區傳播的社會政治背景[J].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3):17.
[13]R.Cunningham.Lamaism[J].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1941(13):2-3.
[14]R.Cunningham.Origins in Lamaism and Lamaland[J].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1938(10):182.
[15]R.Cunningham.Some Incarnations and Reincarnations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J].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1939(9):23-35.
[16]R.Cunningham.Lamaism[J].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1941(13):11.
[17]R.Cunningham.Origins in Lamaism and Lamaland[J].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1938(10):176.
[18]R.Cunningham.Origins in Lamaism and Lamaland[J].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1938(10):176.
[19]申曉虎.比較的視角:葉長青康區宗教文化研究探析[J].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