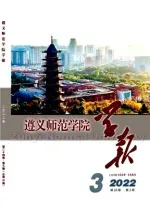語言視差的多維理據及其翻譯策略
楊司桂,李華琴
(遵義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貴州遵義563002)
所謂視差(Parallax)是指“人們的大腦對所觀察事物產生的判斷與實物有所不同”[1]。視差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例如,用一把尺子去測量木頭的長度永遠達不到絕對的精確,得到的測量結果與實際長度總存在一定的誤差;用秤去秤一個物體所得到的重量與實際重量也存在一定的誤差等等。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視差”現象,易引起人們的注意。然而,另一種“視差”,即“語言視差”,卻被人們所忽視。語言是對客觀現實的反映,它“不僅表現現實,還扭曲客觀現實”[2]。扭曲客觀現實也就意味著語言與客觀現實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視差”。作者將從符號因素、語言因素以及認知因素對語言的視差進行詮釋,并就如何翻譯帶有“視差”性質的語料提出與之相對應的翻譯策略。
一、語言視差的符號因素
符號是信息的載體,是對客觀現實的表征,與客觀現實有一定的關系,我們使用的漢字便是如此。例如,“人”,就像一個人雙腿叉開站著,“雨”字有“四點”,像似在下雨;而“日”和“月”酷似天上的(⊙)和()。拼音書寫文字亦不例外,根據希伯來語的早期記載,字母“a”就是對牛頭的寫實,“b”是對馬的模仿,“g”像駱駝的頭像,等等。隨著社會的發展,語言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由具體到抽象,由簡單到復雜。日久天長,就很難看出早期圖像對文字留下的痕跡。這樣,語言符號對客觀現實的表征關系勢必會出現一定的“偏差”或曰“視差”。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Heidegger)以及法國符號學家德里達(Derrida)的語言符號學對于解釋語言視差的成因有一定的說服力。海德格爾認為語言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清晰、完整、有聲,另一方面則晦暗、殘缺、無聲[3];他認為人們通常在命名、形成或使用某個概念時只注意到前者而忽視后者。由于前者常常掩蓋或壓制后者,后者就不為人所注意。這里提到的“晦暗”、“殘缺”、“無聲”就說明人類的命名和概念存在著極大的局限性,進而對客觀現實的表征便存在一定的“視差”。而德里達對語言符號的獨到見解,對語言視差的解讀也自有其道理。德里達首先對傳統的符號學觀點進行了批判,認為符號并不是能指與所指的統一體,能指與所指的關系也并非像索緒爾(Saussure)比喻的硬幣的兩個面那樣密不可分。他認為符號的出現并不等于它所意指的東西(客觀現實)現時在場,而是意味著所指不在場,是推遲了的在場,人們從符號中尋找意義時所得到的不過是能指的能指,解釋的解釋,例如,“樹”常被釋義為一種“植物”,而“植物”又需要其他詞來解釋。不僅如此,德里達還認為每個符號都是由無限延續的符號的意義構成的。德里達把語言作為能指的集合體,與所指無關,這樣,語言與客觀現實之間的表征的距離就更大了。雖然德里達的看法有點偏激,但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語言與現實客觀世界的對應關系存在著偏差,有時偏差還挺大。
以上兩位符號學家對語言的闡述,說明語言符號的表達和認知功能是有缺陷的,不能全方位地表征“客觀現實”,出現了扭曲客觀現實的現象。對于這一點,陜西師大文學院教授韓寶育在“語言符號的局限性[4]”一文中也進行過相關論述。他認為“語言符號在表達認知內容時,具有粒散性的特點,如果我們要用語言來勾畫一個未知事物,只能得到一個疏略的框架,這個框架的顆粒是很大的。單憑語言,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顆粒以下的細部”。在這里,“顆粒”是指對語言細部的假象。以照片為例,顆粒大的照片模糊,顆粒小的照片清晰。語言有類似的特點。我們說語言顆粒很大,是指純語言符號提供給我們的世界和意義是很模糊的。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由“顆粒”構成的,因而都有一個顆粒大小的問題。純語言所提供的圖像雖然模糊、粗梳(清晰度以下),但我們感受卻很具體、很清晰。而“顆粒以下”就是指清晰度以下語言符號所漏掉的內容。語言既然類似顆粒結構,線形排列中的各個語義點之間,在其前后左右,就都會有空白,這就是所謂的粒散性,也就是本文所說的語言“視差”現象。
簡而言之,語言符號與客觀現實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對映,或語言表達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現實世界,從而導致語言視差的產生。當然,除了因對映不一致而產生語言的視差外,語言符號的不足或貧乏也會產生語言的視差。
二、語言視差的語言因素①
①語言因素其實屬于符號因素的一部分,為了更好闡述語言視差產生的緣由,加上語言不足是視差產生的重要原因,故單獨作為一部分來闡釋。
我國翻譯家胡以魯認為,“天地之始無名也。名之起,緣于德業之模仿。”意思是說,宇宙起源時有物無名,名是人類模仿自然的結果。在古代,由于原始初民的語言簡單,或相當貧乏,不能想出更精確的新詞語表達他們周邊的新概念及新現象。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用現存的詞語或短語來表達,有時把兩個實際不同的事物當成一個。至今,人們還在使用這一方法,不過美其名曰“隱喻”,它既是一種修辭格也是一種思維方式。符號學家皮爾斯(G.Peirce)區分了記號(icon)的三種情況,而隱喻就屬于其中一種,表達的是一種平行關系,即通過指出某物與另一物之間某方面的相似來表達某物,此表述本身就意味著語言表達與客觀現實存在一定的距離,即“語言視差”。
即使到了現在,語言還是顯得非常貧乏,總落后于現實,新的事物幾乎每時每刻都在出現,而語言中的新的與之相應的表達卻不可能立即跟上。此時此刻,隱喻便趁虛而入,填補了這一方面的空缺。隱喻中的本體與喻體是一種平行的喻指關系,這種表述就意味著語言與現實存在著一種“視差”。這種“隱喻”性的視差現象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是無處不在的。例如,在中國,某人要辭職去經商,我們稱之為“下海”,而“經商”與“下海”從表面上看不存在任何聯系,而現存詞庫中沒有合適的詞語來描繪“辭職經商”這一現象,于是乎,人們只得使用“下海”這種“視差”語料來表達。其它相類似的情況還有:泡妞(court girls)、熔爐(melting pot)、曬太陽(bathing sun)、打掃衛生(do some cleaning)等等。因囿于篇幅,不再贅述。
總之,語言總是滯后于現實,導致語言符號不夠用,不能與豐富多彩的世界一一對應。中國人常說“詞不達意”、“千言萬語也表達不盡”、“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難以用言辭表達”、“這樣說是掛一漏萬”等說法,就是對以上現象的生動寫照。人們為了準確描述客觀世界及人類情感世界,隱喻便應運而生,而隱喻來身就是一種平行關系,故語言與現實之間的“視差”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
三、語言視差的認知因素
認知語言學認為客觀現實是語言的源泉并對語言的形成起著決定作用,不過,人的認知因素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認知語言學家認為語言能反映現實,但不是直接的,在反映的過程中,人的認知因素不可避免地介于其間,也就是“心生而言立”,其模式是:
客觀世界→認知加工→概念→語言符號
可見,認知發展先于語言表達并決定語言的發展演變,也就是說,語言是認知能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只有被理解了的客觀事物才能用語言表達出來。
這一點在古代,尤其是原始社會尤為突出。古時候,人們的思維能力是很有限的,或曰“思維貧困假說”,其思維能力處于低水平狀態,他們只使用簡單的方法來了解周圍的客觀事物,通常把實際上不一樣的事情當作了同一種事物,或用一些簡單的語句來代表一定場景的某些模糊指稱。如,單詞“sea lions”,表面上看來似乎指的是海中的獅子,其實不然,指的是大耳朵海豹。不過,人們還是以“sea lions”對該動物加以指稱,因為他們常用些普通的詞來描繪一些模糊但差異明顯的不同客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簡單的詞語及表達便成了固定語言表達,從而導致語言表征與客觀現實之間出現差異,或曰“語言視差”。又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是古代人認識和描述事物的一個基本原則,因而身體活動便成了當時人類思維活動的典型活動,那時的人們易于根據自身的部位來認識周圍的事物,例如:他們認為山有頭,于是便形成詞語“山頭”。類似的還有“山腰,山腳,桌腿,樹身”等等。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表達便慢慢地成了人們的日常用語。但我們知道山和樹不是“人”,因而不可能長有頭、腳、腰等等,這樣語言與現實便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某些“視差”。又如,我們所熟悉的“sunrise(日出)”和“sunset(日落)”這兩個表達亦是如此。古時候,人們對他們周圍的事物用自身的部位來命名,而對于遙遠的事物,他們就只有用附近的物體來命名,也就是說,他們了解事物的規律是從近到遠。當早晨太陽升起來時,由于他們把自己所處的位置作為參照點,因而誤認為是太陽在運轉,便有了“sunrise(日出)”與“sunset(日落)”兩詞,后來我們知道實際上地球繞著太陽轉,而根本就不存在“太陽上升”、和“太陽下落”這兩種情形。然而,久而久之人們習慣了那種扭曲現實的詞語表達,也不刻意去改變這些表達。因為有些表達在某些社團一旦形成,就不易于改變,即便為了接近現實而臨時改變,人們也不接受這些新生的詞語表達。
總之,人的認知因素在“語言視差”的形成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認知先于語言表達。當人們還沒有獲得“溫床”的概念及其特性以前,就不會出現“溫床”一詞;當人的認知能力尚未發展到被動概念時,人類就不會使用被動概念的語言結構。而人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正因如此,在古代,也就會出現語言對現實的“錨定”與客觀現實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視差”,我們也相信,隨著社會的發展及人類認知能力的提高,現今的語言表達在將來也會被認為是對現實的一種“扭曲”,存在著“視差”。
可見,由于各種原因我們現存的語言中有著大量的語言視差現象,這些程度不等的“視差”現象給不同國家人們之間的交流帶來了一些障礙。為了消除這些障礙以及提高國際之間的交流合作,我們應采取適當的翻譯策略。
提及翻譯策略,我們先看一些中外學者對翻譯所下的定義:矛盾認為“翻譯是把一種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正確無誤地、恰如其分地轉移到另一種語言文字中去的創造性活動”;曹明倫教授則認為翻譯是“把一套語言符號或非語言符號所負載的信息用另一種語言符號或非語言符號表達出來的創造性文化活動[5]”。西方學者卡特福特(Catford)在《翻譯的語言學理論》中提到:“翻譯是把一種語言的話語材料替換成等值的另一種語言的話語材料[6]”,而尤金·奈達(EugeneA.Nida)則說翻譯即譯意或曰用最自然的語言去復制源語的信息,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定義意味著:在進行文本翻譯時,意義的傳譯應為先。目前翻譯策略有兩類①盡管也有歸化與異化之說,很多學者認為它們是同出一轍,不過,歸化與異化策略偏重于文化層面而已。:直譯和意譯;它們各有千秋,即直譯重形式而輕流暢而意譯重內容而輕形式。上文所提到的那些有著“語言視差”的語言材料,雖然與現實有著不同程度的扭曲,但與現實卻存在“異質同構(lsomorphism)”現象,故在翻譯帶有語言視差性質的話語材料時應采用奈達的“功能對等論”,理由是該理論不僅是建立在異質同構體(1somorphism)[7]基礎之上,強調客觀實體間的同構性,而且能彌補直譯與意譯間的不足。此外,異質同構體是在符號學中象似性(iconcity)特征基礎上引伸并發展起來的[8]。而上文所提到的帶有“視差”的語言素材也屬于符號學中的一種,因而,功能對等是翻譯“視差”語言材料的最理想策略:一是它們之間有聯系,二是功能對等論吸收直譯與意譯的精華,彌補了兩者間的不足。關于這一點,筆者在此不再贅述,僅舉一例。當一個中國人對英國人說,“我不教書了,已下海了”。此處的“下海”指的是“經商”,應譯成“go out for business”,而不能譯為“go into sea”。“下海”的表面意義“go into sea”與其實際意義“經商(go out for business)”無任何瓜葛關系,兩者“視差”過大。再者,若直譯成“go into sea”,西方人聽了則不知所云。簡言之,在跨文化交際中,為達到良好的交際效果,我們應采取功能對等去翻譯帶有“視差”性質的話語材料。
四、結語
綜上可知,由于各種原因,“視差”廣泛存在于我們現存的語料中,給跨文化交流造成了一定的障礙。為了消除各國之間的交際障礙,筆者以為,奈達的功能對等論是一個較理想的翻譯策略,應該加以提倡及推廣,因為功能對等論是基于異質同構體之上的,與“視差”具有一定的通約性。換言之,功能對等論的優點及“視差”語料本身的特點決定了在翻譯“視差”語料時應把功能對等論視為最佳翻譯策略,這樣,跨文化交流才能取得較好的效果。
[1]黃宜思.簡論英漢翻譯中的“視差”現象[J].中國翻譯,1999,(5):22-25.
[2]EugeneA Nida.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6.
[3]廖七一.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75.
[4]韓寶育.語言符號的局限性[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4):90-91.
[5]曹明倫.翻譯之道:理論與實踐[M].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6.129.
[6]方夢之.譯學辭典[Z].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396.
[7]楊司桂.淺析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J].河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7,(1):68-71.
[8]冒國安.同形現象與形式可譯[J].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3):8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