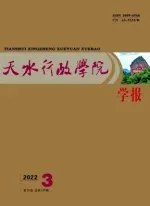文化建設困域與文化自覺意識構建
粟國康
(西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重慶 北碚 400715)
一、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必要性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深刻闡述了文化建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鮮明地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并用“四個越來越”精辟地概括了發展文化事業、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必要性。
第一,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是對急劇變化的時代潮流的理性回應。面對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多極化不斷深入的國際背景,中國文化建設事業置身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風口之上。在這樣的時代潮流中,一方面,中國文化需要直面經濟全球化發展中的“文化競爭”,面對當前國際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相互競爭,如何既能在提高文化生產力的同時擴大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又能在擴大中國文化產品出口的同時保有自己的民族品格和文化競爭力,是一大難題。另一方面,中國文化需要直面政治多極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挑戰。文化入侵、文化安全是政治多極化背景下任何國家都不容回避的一個挑戰,面對國際各種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鋒,面對他國的文化攻勢和文化演變,加強自我主流意識形態和文化安全建設刻不容緩。
第二,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態勢的清醒體認。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文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個逐步認識、不斷提高的過程。從忽視文化建設的沉重教訓中,我們體認到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應“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隨著認識的提升,又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三位一體”,并把文化作為一種軟實力,視為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七大更是提出了“更加自覺更加主動地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就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態勢的清醒體認,提出“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愿望”[1]。
第三,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是對當前文化建設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深刻洞察和準確把握的必然結果。改革開放尤其是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文化領域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取得了豐碩成果,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具備諸多有利條件,但也面臨一系列矛盾和問題:文化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亟待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引領功能有待提高、文化產品不夠豐富、文化發展的體制機制尚不順暢、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有待增強、文化人才隊伍的建設也有待加強等。這些矛盾和問題,實質是我國當前文化建設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尚不完全適應。
二、現實文化建設中的文化困域
第一,文化失真:關于文化與經濟、政治協調發展的困域。馬克思主義認為,所謂文化,就是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的力量的書,歸根到底,文化就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2]。作為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文化,他是人類在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過程中創造出來的,同時在創造出文化的過程中文化自身也成為人類得以實現進一步擴大生存和超越發展的推動力量,這種力量就是毛澤東所提出的“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反映, 又給予巨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3]。但是,現實中文化的發展卻陷入一個困境:人們越來越難以駕馭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文化,甚至迷失了文化創造的目的和意義,造成文化發展滯后于經濟和政治發展,甚至成為經濟、政治發展的桎梏,導致文化失真。文化的失真還突出體現在各種低俗文化、庸俗文化的沉渣泛起,對文化雙重屬性的定位不當使文化生產走向了刻意的商業化包裝而致使文化的本真功能被屏蔽。
第二,文化失范:關于文化與道德、精神風尚引領的困域。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物質貧乏不是社會主義,精神空虛也不是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應該引領人民內心世界、道德水平和精神力量的極大豐富和作用的充分發揮。但是,現實中文化的這種引領功能正日漸被弱化,導致社會文化的失范。文化失范在思想層面表現為人們的思想、價值觀念和心理的混亂、無序狀態,如人們理想信念模糊、誠信缺失、道德滑坡等;在行為層面則表現為人們的行為在不同領域陷入混亂、無序狀態,如經濟領域的假冒偽劣,文化領域的論文抄襲、造假,政治領域的貪污腐敗等。種種跡象表明,我國當前文化建設中的文化失范已經到了極為嚴重的地步,文化不僅難以切實起到引領道德、精神風尚的作用,反而在與各種丑惡現象的糾纏中陷入更深困域。
第三,文化盲從:關于文化自卑與文化自信的困域。中國古語云:十年樹人、百年樹木、千年樹文,中華文化正是在數千年的歷史發展中積淀、提煉而形成的具有自我民族特色、自我民族風格的文化。經濟全球化趨勢下,中華文化面對外來文化的強勢入侵,在文化實踐中出現了諸多的文化盲從現象,這種盲從突出體現在對自我文化的不自信以及主流文化面對非主流文化的拷問步步后撤。從學術界對西方學術話語的亦步亦趨,到娛樂界對西方娛樂符號的沿襲,再到日常生活中人們的盲目跟風,無不突出展現出民族文化自尊心、自信心的嚴重缺失。而各種非主流文化的勃興、亞文化的突起,甚至某些反文化的東西開始在中國文化市場上大行其道,日漸擠占主流文化的生存空間,造成主流文化信仰者流失。
無論是文化失真、文化失范還是文化盲從,究其實質,都在于在民族文化、外來文化和現實文化之間的契合點上陷入迷思,尋找不到現實文化理性嵌接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的坐標點,最終使文化發展迷失方向。
三、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需要構建文化自覺意識
所謂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4]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首先需要對我們所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有所體認、有所反思,為此需要構建文化自覺意識。文化自覺意識的構建,需要提點三重理念,廓清兩重錯誤傾向,具備三種自覺意識。
第一,自覺民族文化,實現傳統與現實、繼承與發展的契合。文化自覺首先強調對民族文化的自覺,強調人們對自己文化的“自知之明”,即既能看到本民族文化的長處、優勢,又能看到本民族文化的短處、劣勢;既能看到本民族文化建設已取得的成績,更要能看到本民族文化建設面臨的困難和潛在的危險。對民族文化的自覺,需要具備“批判繼承”意識。任何國家任何社會的文化建設都離不開歷史和傳統,都是在既有的歷史和傳統基礎上推展開來的,任何企圖抹殺文化傳統或繞過文化傳統的門欄而發展文化事業,都是不可能的,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5]對傳統文化要秉持一種辯證統一的科學態度:既不全盤肯定又不全盤否定,承認傳統文化既有精華也有糟粕,既有優秀成分也有陳腐因子,在此基礎上繼承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和優秀成分,剔棄其糟粕和陳腐因子。
第二,自覺外來文化,實現“我”與“他”、學習與借鑒的契合。目前中國的文化發展存在極嚴重的文化復歸傾向,主張文化復歸的取向是一種明顯的倒退復古,并不是提倡文化自覺的本意,更不是繼承傳統的本意。除了文化復歸的傾向,另一個突出取向則是全盤他化,尤其是全盤西化,不加質疑不加鑒別地沿襲西方現代化道路、接受西方各種理論。這兩種取向無疑都不是對待外來文化的正確態度,更不是文化自覺的真實態度。
文化多元時代對外來文化的自覺,需要具備“博采眾長”意識。學習、借鑒外來文化的精華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對此學者樂黛云曾說過:“一個民族要認識自己,就要走出自己的墻,從外面看。一個民族要認識別個民族,就要走進別人的墻,從里面看。其實,認識自己和認識別人是同時的。”[6]在多元文化時代,面對外來文化紛至沓來的現象,構建文化自覺意識需要具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理性看待外來文化。對外來文化中所蘊含的精華部分、理性成分,要吸收、借鑒、轉化以為我所用,“對于那些不適合我國國情的東西,對于一切錯誤的腐朽的東西,我們不但不能引進,而且要堅決進行抵制和斗爭。”[7]
第三,自覺現實文化,實現傳統、現實、未來的契合。為此需要深刻洞察和理解文化創造與文化發展規律,揭示中華文化的未來走向,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文化建設有其自身規律,市場經濟規律并不完全適用于文化領域的文化創造、文化生產和文化傳播,需要始終堅持區分文化的雙重屬性,明悟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所適用的發展規律的差異性,防止和控制經濟規律在整個文化領域的“越位”。
文化自覺不僅僅是一種理論觀點、思想意識,更是一種實踐活動,是一種為實現現實文化健康良性發展的實踐過程,為此需要具備“積極建設”意識。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實現,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重在建設,需要自覺推進文化體制改革,以改革促發展;需要積極發展社會公益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活動需求;需要始終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文化建設的全局,找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前進方向;需要建設宏大文化人才隊伍,為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有力人才支撐。●
[1]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N].人民日報,2011-10-26(1).
[2]邱觀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概論[M].武漢:武漢理工大學出版社,2004.215.
[3]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664.
[4]費孝通.反思·對話·文化自覺[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3).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
[6]樂黛云,勒·比雄.獨角獸與龍—在尋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誤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79.
[7]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