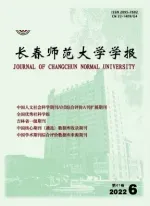張綖《詩余圖譜》詞調論芻議
張海濤
(南開大學文學院,天津 300071)
張綖《詩余圖譜》詞調論芻議
張海濤
(南開大學文學院,天津 300071)
張綖的《詩余圖譜》是詞由音律向格律轉變的定型之作,其中一個重要標志便是其對于詞調的探討。該書不僅首創了詞調三分法,而且對同調異名和一調多體等問題皆有開拓之功,為后人的進一步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張綖;《詩余圖譜》;詞調
張綖,字世文,別號南湖,高郵人,明代中期文學家。其平生對詞學尤為屬意,于嘉靖十五年(1536)編撰了現存最早的真正意義上的詞譜——《詩余圖譜》①,對后世產生了很大影響。該書不僅為填詞提供了規范,還涉及了關于詞調的諸多問題,使當時完全脫離音樂的詞得以被人們重新審視。
一、詞由音樂文學到案頭文學的轉變
詞是配合燕樂演唱的歌詞,其本質是一種音樂文學。經過了唐五代、兩宋的發展,到了南宋后期詞的樂譜、歌法漸次散失。明初以后,填詞以歌終成絕響。這個時候,詞已經完全脫離了音樂,不得不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案頭文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碧雞漫志》中對此有一段精當的論述:
迨金元院本既出,并歌詞之法亦亡。文士所作,僅能按舊曲平仄,循聲填字。自明以來,遂變為文章之事,非復律呂之事。[1]1826
詞在明代成為了“按舊曲平仄,循聲填字”的“文章之事”,似乎較依律倚聲容易了許多。但實際上并非如此。相對于傳統的詩文和現世的散曲,詞顯得尤為復雜,其“一調或至數體,一體或有數名,其目幾不可殫舉”[1]1826。作為一種剛剛徹底脫離音樂的文學體裁來說,它還存在著許多需要解釋和規范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明人的填詞創作便出現了兩種傾向:
其一是隨意為之。這個時期出現了一些嚴重不合詞律的作品,如桑悅的《念奴嬌·登仙弈山作和東坡韻》[2]373、姚綬的《水調歌頭·云東偶興二首》[2]306等等。這些詞不但某些地方平仄不合,就連字數也多有出入。張仲謀先生對此解釋道:“因為詞早已不能唱了,作為書面文學,多一字或少一字,在他看來是無關緊要的。”[3]這與后來楊慎、王世貞等人所作自度曲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信筆寫作長短句之詩,只不過一個冠以舊調,一個標以新名罷了。
其二是亦步亦趨。所謂亦步亦趨,即按詞填詞,平仄不易。弘治間《詞學筌蹄》的出現便反映出這種情況。其出于便于填詞的考慮,將《草堂詩余》重新按調編排,并圖為平仄,以滿足時人的需要。但它完全按照例詞文字的平仄來標注,名為“按譜填詞”,實則“按詞填詞”。這樣的詞譜無疑正是當時文人“按詞填詞”模式的產物。
隨意為之、不顧詞律之作固然不能稱之為詞,而亦步亦趨、按詞填詞的方式也只會使詞愈加僵化,走向消亡。這兩種傾向的出現表明時人對詞體的理解、認識已經走上了歧途。倘若任其發展,最終的結果只能是“詞將不詞”了。
二、《詩余圖譜》論調
《詩余圖譜》的編撰目的是“俾填詞之客,索駿有象,射鵠有的”②,即為人們填詞提供一個可以依據的規范。然而它并非僅僅是一部指導填詞的詞譜,其自序、凡例、圖譜、例詞、按語之中多有關于詞調的見解與發明,對于人們重新認識詞體有著積極的引導作用。
(一)詞調的分類
詞最初有小令、慢詞之分,這當是由其音樂屬性而來。當詞不復可歌之后,張綖對這種純文學體裁進行了重新的分類。《詩余圖譜·凡例》中說:
圖譜分為三卷。第一卷小令,第二卷中調,第三卷長調。每卷之調又以字數為序。
并且在目錄中對每一類的字數范圍作了一個界定。即三十六字至五十七字為小令;六十字至八十九字為中調;九十二字至一百二十字為長調。這樣按字數多少給詞分類,是面對眾多詞調所采取的執簡馭繁的辦法,是很有創造性的。不過由于張綖所見詞調有限,其所分三類之間還存在著五十八字、五十九字、九十字、九十一字的空白。且因其疏忽,雙調五十八字的《踏莎行》、《小重山》也出現在了卷一小令中,與目錄相矛盾。
張綖在《詩余圖譜》中首創三分法,其初衷或是便于人們填詞時查找詞調。然而,這種做法很快為時人所認同,并在一些詞選、詞譜中紛紛效仿。嘉靖二十九年(1550)上海的顧從敬按小令、中調、長調重編《草堂詩余》,且每一詞調所屬類別皆與《詩余圖譜》相同。此分調本一出,很快取代了《草堂詩余》的其他版本,成為了最為流行的本子。也正是由于此本的廣泛傳播,后來的人便誤認為顧從敬是三分法的始作俑者。我們如果聯系上文提到的《詞學筌蹄》就會發現,同樣是《草堂詩余》的分調改編本,一個風行一世,一個反響微弱,造成這種反差的原因當有三分法的運用在其中。此后的詞選如《類編箋釋國朝詩余》,詞譜如《嘯余譜》等皆如此分類標目。通行既久,小令、中調、長調便漸漸固定為了一種術語,為人們論詞時廣泛使用。如俞彥說:
今人既不解歌,而詞家染指,不過小令中調。[4]400
又說:
長調尤為亹亹,染指較難。[4]401
沈雄更是在《古今詞話·詞品上卷》列“小令”、“中調”、“長調”之目分別加以論述[5]。在這種三分法深入人心的同時,一些詞學家也對此提出了質疑。毛奇齡說:
其調不拘短長,有屬黃鐘宮者,有屬黃鐘商者,皆不相出入。非若今之譜詩余者,僅以小令中調長調分班部也。[6]
朱彝尊《詞綜·發凡》則說:
宋人編集歌詞,長者曰慢,短者曰令,初無中調、長調之目。自顧從敬編《草堂詞》,以臆見分之,后遂相沿,殊屬牽率。[7]
應該說,毛奇齡和朱彝尊的批駁都是有道理的。但詞至明代已非宋時的合樂曲子,而成為了格律詩之一種。張綖如此分類,恰恰反映了這樣的客觀現實,順應了時代的潮流。直至今天,我們依然會感受到這種三分法的影響。如同近體詩分五言、七言,小令、中調、長調也已成為人們認識詞、了解詞的入門概念。
(二)同調異名的辨析
所謂同調異名,是指同一個詞調有很多不同的調名。這種現象在前人詞作中經常能夠見到。將繁多的調名歸并到各個詞調之下,這當是理清詞體的一個重要方面。對此,張綖也做了很多的嘗試。《詩余圖譜·凡例》中說:
詞有同一調而名不同者,蓋調有定格不可易,名則可易。如東坡赤壁《念奴嬌》,因末有“酹江月”三字,后人作此調者即謂之《酹江月》。又謂之《赤壁詞》。又謂之《大江東去》。因其一百字,又謂之《百字令》之類是也。亦有同義易之者,如《蝶戀花》謂之《鳳棲梧》、《鵲踏枝》;《紅繡鞋》謂之《朱履曲》之類是也。今皆列注名下,云一名某,一名某,使覽者知其同調。
這段話是張綖對于同調異名的一個總論。不僅對這種現象做出了自己的解釋,還舉例說明了某些詞調異名產生的緣由。圖譜中共有18個詞調標注了別名,如“上西樓,一名相見歡”、“南柯子,即南歌子”、“尾犯,亦名碧芙蓉”等等。其中除了《浣溪沙》③、《風流子》④有待商榷之外,其他詞調別名的標注都是正確的。然而由于識見所限,張綖未能對同調異名的情形一一洞察,圖譜中還是存在著本是同一詞調,卻重復收錄的情況。如卷一中的《洛陽春》、《一落索》、《玉聯環》;《醉落魄》與《一斛珠》;卷二中的《小桃紅》與《連理枝》。應該說,張綖在《詩余圖譜》中辨析異名的詞調數量較為有限,且有未能看出以致同調重出的失誤,這都說明他對于同調異名的理解還并不完善。雖然如此,他仍為后人繼續深入、細致、全面的研究詞調別名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另外,張綖在探討同調異名的時候,還提及了調名緣起的問題。他在《凡例》“詞有同一調而名不同者”一條后有小字附識:
凡名詞之義,吳人都玄敬嘗著其說于《南濠詩話》,要之不盡如都說。蓋古人或是因篇首之字名之,如《詩·關雎》之類;或是取篇中字至雅者名之,如《書·梓材》之類。后人承之,即謂之某調耳。故茍不異其音節,則名亦可易。
明人都穆認為“昔人詞調,其命名多取古詩中語”[8],其所舉詞例不免有穿鑿附會之處。張綖在辯駁都穆說法后,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雖然張綖的解釋也經不起推敲,但他在都穆之后再一次提起了詞調命名的問題,對于引起時人對此關注是有推動作用的。稍后,楊慎在《詞品》中屢屢論及調名的緣起。直至清初毛先舒著《填詞名解》,對調名來歷的探索可謂蔚為大觀了。
(三)調有定格與一調多體
《詩余圖譜·凡例》開篇便說:
詞調各有定格,因其定格而填之以詞,故謂之填詞。
又說道:
蓋調有定格,不可易。
可以說,“調有定格”是張綖繪圖制譜的立足點,是他對于詞體的一個基本認識。但事實上,一個詞調并非只有一種體式。但凡披閱宋元以來流傳下的詞作,這種情形便不難發現。對此,張綖采取了實事求是的態度,將其認為屬于同一詞調的不同體式的詞附錄于圖譜例詞之后,即《凡例》中所說的“其不同者亦錄其詞于后,以備參考”。經過統計,《詩余圖譜》三卷共收153調,216體⑤。若加上未能傳世的后集四卷⑥,張綖所歸納的體式還會更多。
這些作為附錄的詞作大都只是一一列出,偶爾張綖也會對其體式的不同之處加以說明。如在《定風波》又一體詞后說:
諸家皆中藏韻,惟此詞無中韻。
又如《摸魚兒》錄歐陽修“卷繡簾梧桐秋院落”一闋為又一體,其后注云:
“那堪更”,“更”字當是韻;“佳期過盡”,“盡”字當是韻。今皆無之。蓋大手筆之作,不拘拘于聲韻。然音律既諧,雖無韻可也。但韻是常格,非歐公不可輕變。又有可以有韻,可以無韻,如律詩起句者,不在此例。
張綖指明此詞之所以為異體,主要是由于其押韻與正格不同,并進一步推測其成因。
除了錄詞于后以外,某些詞調的異體是通過文字提示來體現的。如《畫堂春》一調,前具圖譜,后列一詞,儼然一調一體。而仔細看會發現例詞后有雙行小字:
一調兩段末句各多一字。
意思是另有一體上下片的結句各多一字,為五個字。查《欽定詞譜》可知黃庭堅《畫堂春》(摩圍小隱枕蠻江)即此體,張綖此說無誤。再如《行香子》圖譜“后段同前”下有雙行小字:
起二句無韻,亦有有韻同前者。
也就是說除了像其所錄例詞“舞雪歌云”一闋過片二句不押韻外,另有一體過片二句押韻。秦觀《行香子》(樹繞村莊)即此體。
總的來說,《詩余圖譜》是第一部具有明確備體意識的詞譜。不論是從全書體式的數量,還是從相關詞調異體的列舉(如《生查子》一調五體,《應天長》一調四體,《臨江仙》一調六體)來說,張綖對此都是下過一番功夫的。特別是他參考了久已不傳的《花間集》⑦,將其中的詞調異體也收入圖譜,使得一調多體的情況更為全面,也更為復雜。略顯遺憾的是,張綖所下的功夫僅僅止于對一調多體的搜集和整理,更進一步的理解與分析是很有限的。也就是說,《詩余圖譜》將“調有定格”與“一調多體”的矛盾無限地放大,并以存疑的姿態呈現在人們面前。因此,它成為后人面對詞體時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明朝嘉靖間郎瑛《七修類稿》⑧“南詞難拘字韻”條中說:
然照字依韻名曰填詞,今一詞之名雖同而文有多寡、韻有平仄不同者,不可辯明,正無《樂府詩章》之書證之耳。[9]
又鄒祗謨引俞彥語曰:
至于《花間集》同一調名,而人各一體,如《荷葉杯》、《訴衷情》之類,至《河傳》、《酒泉子》等尤甚。當時何不另創一名耶?殊不可曉。[10]644
在困惑與不解中,人們還是嘗試從各種角度對此加以解釋和說明。如沈際飛,他便從襯字、宮調、體制等方面來討論同調異體[11]。其中雖有以曲例詞之誤,卻仍不失為一種進步。到了清代,這個問題仍是詞體研究領域,特別是詞譜撰制中的一個著力點。由此來看,張綖對此問題的提出與呈現也是一份不容抹殺的貢獻。
《詩余圖譜》是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詞譜,其在詞譜發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凡例》附識中提出的“婉約、豪放”二分說,為后來的明清以至現當代學者屢屢提及⑨,足見其影響之廣泛而深遠。以上這些都毋庸贅言。筆者以為,在詞由音樂文學變為案頭文學的時代,在詞學漸次紊亂的時代,張綖于《詩余圖譜》中對詞調諸多問題進行了梳理、提出、分析和定義,可謂繼“別是一家”[12]后詞體的又一次自覺,并對清代諸種詞律,如萬樹《詞律》、《欽定詞譜》等一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雖然其中得失相參,但從對后來學人的啟發和引導來看同樣是功德無量的。清初的鄒祗謨曾說:“張光州南湖《詩余圖譜》,于詞學失傳之日,創為譜系,有蓽路藍縷之功。”[10]658當我們現在再來看這段話的時候,應當會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了。
[注釋]
①本文所據《詩余圖譜》版本為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五年(1536)刻本。
②見蔣芝《詩余圖譜序》。
③《浣溪沙》第二首例詞“菡萏香銷翠葉殘”題下注云“一名山花子”,實為《攤破浣溪沙》別名。
④《風流子》調下注云“一名內家嬌”。按:《風流子》有單調、雙調。后者萬樹《詞律》亦以為又名《內家嬌》,而《欽定詞譜》則分作兩調。
⑤這兩個數字是剔除了同調重出,增加了調后所附詞調(如《生查子》后附《醉花間》)及圖譜后所列之詞本是另一詞調(如《浣溪沙》譜后第二首詞為《攤破浣溪沙》)的結果。
⑥張綖自序云:“近檢篋笥得諸詞,為成圖譜三卷,后集四卷。”《凡例》云:“圖譜未盡者,錄其詞于后集。仍注字數、韻腳于下,分為四卷。庶愽集眾調,使作者采焉。”惜后集今已不傳。
⑦《花間集》于正德后始流行于世。《詩余圖譜》卷一《應天長》例詞后注云:“此詞又見《花間》。”為張綖參考《花間集》的明證。
⑧《七修類稿》初刻于明嘉靖間,具體年代不詳。王海妍《郎瑛<七修類稿>研究》推斷其成書于嘉靖二十六年左右。黃阿明《明代學者郎瑛生平與學術述略》斷定其初刻于嘉靖二十六年。總之,其成書當晚于《詩余圖譜》。
⑨明代卓人月《古今詞統·雜說》引用“婉約、豪放”之說標為張綖“論詩余”;清人王又華《古今詞論》亦引“婉約、豪放”之說標為“張世文詞論”;王士禛《花草蒙拾》云:“張南湖論詞派有二:一曰婉約,一曰豪放。”王水照先生《蘇軾豪放詞派的涵義和評價問題》引錄了《詩余圖譜·凡例》“按詞體大略有二”一段文字,并在頁下注中說:“《詩余圖譜》之明刻通行者為汲古閣《詞苑英華》本,卻無《凡例》及按語。此據北京圖書館所藏明刊本及萬歷二十九年游元涇校刊的《增正詩余圖譜》本。”張仲謀先生《張綖<詩余圖譜>研究》以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詩余圖譜》初刻本為據,重新證實了“婉約、豪放”二分說始于張綖。
[1][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2003.
[2]饒宗頤(初纂),張璋(總纂).全明詞[M].北京:中華書局,2004.
[3]張仲謀.明詞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99.
[4][明]俞彥.爰園詞話[C]∥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
[5][清]沈雄.古今詞話[C]∥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836-837.
[6][清]毛奇齡.西河詞話[C]∥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587-588.
[7][清]朱彝尊,[清]汪森(編),李慶甲(校點).詞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4.
[8][明]都穆.南濠詩話[M].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C].北京:中華書局,1983:1343.
[9][明]郎瑛.七修類稿[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367.
[10][清]鄒祗謨.遠志齋詞衷[C]∥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
[11][清]王又華.古今詞論[C]∥唐圭璋,編.詞話叢編[C].北京:中華書局,2005:597.
[12][宋]李清照(著),徐培均(箋注).李清照集箋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67.
A Elementary Analysis on the Theory of Ci-poetry Tune of Zhang Yan’s Shiyu Tupu
ZHANGHai-tao
(School ofLiterature,NanKai University,Tianjin300071,China)
Zhang Yan’s Shiyu Tupu is the stereotyped works which shows that Ci-poetry started to depend on metrical(closely related to poetry)instead of temperament(closely related to music).One important symbol is his exploration on the tune ofci-poetry.He was not onlythe first one that divided the tune ofCi-poetryintothree types,but also a research pioneer doing on issues such as“one tune but different names”and“one tune but different styles”. What Zhangyan di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udyoffuture generationgs.
ZhangYan;Shiyu Tupu;the tune ofci-poetry
book=125,ebook=125
I207.23
A
1008-178X(2012)07-0061-05
2012-03-15
張海濤(1987-),男,天津人,南開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從事詞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