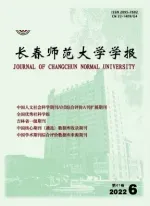論《本事詩》之“七題猶四始”說
伍雙林
(安順學院,貴州安順 561000)
論《本事詩》之“七題猶四始”說
伍雙林
(安順學院,貴州安順 561000)
《本事詩》一書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徵異、徵咎、嘲戲七題分條記述詩人詩作的事實原委,其序所言“七題猶四始”,符合了上層統治者尚經重史的要求,內容上繼承創新了四始即風、雅、頌的編撰方法,更重要的是繼承和發展了四始的政治教化及其交際功能。
《本事詩》;七題;四始
中晚唐人孟棨所撰《本事詩》一書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征異、征咎、嘲戲七類分條記述詩人詩作的事實原委,其序言曰:“詩者,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懷佳作,諷刺雅言,雖著于群書,盈廚溢閣,其間觸事興詠,尤所鐘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因采為《本事詩》,凡七題,猶四始也。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徵異、徵咎、嘲戲,各以其類聚之。”“凡七題,猶四始也”,這幾個字有著怎樣的內涵?本文就此問題進行探討。
一
所謂“七題”,即《本事詩·序》中所說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征異、征咎、嘲戲七類。
關于“四始”,歷來主要有三種說法:一是《魯詩》“四始”說,見于《史記·孔子世家》:“《關睢》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1]329二是《毛詩》“四始”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是謂四始。”[2]269-272三是《齊詩》“四始”說:《詩緯汜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四牡》在寅,木始;《嘉魚》在巳,火始;《鴻雁》在申,金始。”[2]272
《本事詩·序》云:“詩者,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懷佳作,諷刺雅言,雖著于群書,盈廚溢閣,其間融事興詠,尤所鐘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因采為《本事詩》,凡七題,猶四始也。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征異、征咎、嘲戲,各以其類聚之……拙俗鄙俚,亦所不取。”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孟棨所言之“四始”即是《毛詩序》中所說的“四始”,亦即“風、大雅、小雅、頌”。
中晚唐時期,統治者更多地傾向于重經史,無論是科舉取士還是政治上的用人都由前期重詩賦轉向重經史之才,《新唐書》卷一百七十六《韓愈傳》載:“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3]5255當權者對史的重視,如《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七載殷侑《請試史學奏》:“歷代史書,皆記當時善惡,系以褒貶,垂諭勸戒。其司馬遷《史記》,班固、范蔚宗兩《漢書》,旨義詳明,懲惡勸善,亞于六經,堪為代教。伏惟國朝故事,國子學有文史直者,宏文館宏文生并試以《史記》、兩《漢書》、《三國志》。”[4]7855
中晚唐無論是文人自身還是統治者都注重經史。《詩經》為《六經》之首,其中很多詩本身就是一部史詩,且毛公為其作序使其更具備了史的性質。《本事詩》記載了詩人軼事,這本身就具有“史”的特點,又指明其“猶四始”,這符合了當時統治者尚經重史的需求。因此,孟棨說“凡七題,猶四始也”。
二
《本事詩》的編撰,從其分門別類的紀事方法來說,應源于《世說新語》,但“本事是詩歌與詩事的結合。唐詩本事中,詩與事的關系有兩種:一是引事明詩,二是引詩證事。前者源出《詩序》,敘事的目的在于說明詩作背景,交代寫作緣由,從而揭示詩歌意旨。”[5]57縱觀《本事詩》七題,得出這樣的結論:《本事詩》以詩系事的編撰主要受《詩序》的影響,而體例則源于《詩經》的風、雅(大雅、小雅)、頌的分類。
《本事詩》七題,不光在詩史性質、體例上“猶四始”,而且在內容和功用等方面可以說是對四始的體現。
《詩經》的內容大致涉及周民族的史詩、贊頌、怨刺、婚戀、農事和征役等等。以上的內容在《本事詩》里除農事之外其余都有所提及。首先來看“七題”對“四始”中“風”的體現。《詩經》三百,精華在《國風》,《國風》中又以婚戀詩最為精彩。“婚戀”指以戀愛、婚姻為主題的詩篇。[6]39而《詩經》305篇中,風詩就有160篇,占《詩經》總數一半以上。《本事詩》亦如是,寫得最多的就是愛情,七題41則詩本事中“情感”有12則,占整個《本事詩》將近一半。以下就《本事詩》對四始中“風”詩的具體體現進行論述。其次是“二雅”。二雅詩中很多都是怨刺詩,關于《小雅》和《大雅》的內容,凡是事關諸侯與士大夫的均歸于《小雅》;凡是事關周王的則均歸于《大雅》。[7]43《本事詩·嘲戲第七》中記張元一作詩嘲武懿宗帶兵無能,戰場上臨陣脫逃之事,在二雅中如《小雅·信南山》則是刺幽王“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2]470的治國無方。二者大同小異,沒有什么區別。至于四始的“頌”,《詩經》的頌詩幾乎都是歌功頌德,而七題中歌功頌德的也不少,如《本事詩·情感》第一條記:“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制于宮中。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后身緣。’兵士以詩白于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可以這樣說《本事詩》“七題”內容的編撰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四始”,但是更多的是對“四始”的發展。
當然,孟棨說“七題,猶四始也”,這不僅僅只是說內容上猶“四始”,《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本事詩·序言》中有一句話很值得注意,即“拙俗鄙俚,亦所不取”,顯然他認為“拙俗鄙俚”的詩,不適宜教化,達不到四始那樣教化效果,故“亦所不取”。所以孟棨說“七題猶四始”,是說“七題”具有“四始”的“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功用,簡而言之就是能進行政治教化。而《詩經》除了能進行政治教化外,“作為社會交際手段來說,它是貴族階級、士大夫特別是外交官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8]9這一觀點同樣適用于《本事詩》。
縱觀七題所記載的本事詩大多都是與用詩交流有關,所以從這點來看,“七題猶四始”。
綜上所述,《本事詩》“七題猶四始”的提出符合了上層統治者尚經重史的要求,而它的編撰方法及其體例都源于《詩經》,內容上繼承創新了四始即風、雅、頌,更重要的是繼承和發展了四始的政治教化及其交際功能。所以說“七題猶四始”。
[1][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6:329.
[2][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0.
[3][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4]全唐文[M].北京:中華書局,1983.
[5]余才林.唐詩本事與宋代早期詩話[J].文史哲,2006(6):57.
[6]郭預衡.中國古代文學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9.
[7]胡安蓮.《詩經》“風”“雅”“頌”分類[J].南都學壇,2000(4):43.
[8]張啟成.《詩經》的社會交流功能和符號學[J].貴州社會科學,1988(10):9.
book=152,ebook=152
I209
A
1008-178X(2012)07-0073-02
2012-04-12
伍雙林(1977-),女,貴州鎮寧人,安順學院講師,碩士研究生,從事唐宋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