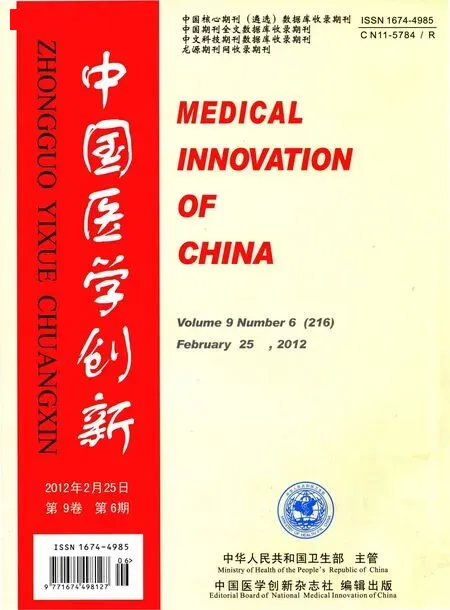COPD患者誘導痰中IL-6、TNF-α水平及其與氣流受限的關系
陳文明 黃樹紅 王桂英 喬秀榮
COPD患者誘導痰中IL-6、TNF-α水平及其與氣流受限的關系
陳文明 黃樹紅 王桂英 喬秀榮
目的 觀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誘導痰上清液中IL-6、TNF-α的濃度變化,并分析它們與COPD氣流阻塞程度是否相關。方法 隨機收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67例,通過肺功能測定將其分為0級12例、Ⅰ級12例、Ⅱ級13例、Ⅲ級15例、Ⅳ級15例五組,正常對照組15例,均作誘導痰,留取其上清液待測。ELISA法測定誘導痰上清液IL-6、TNF-α濃度。結果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各組誘導痰上清液IL-6、TNF-α水平均較正常組明顯增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Ⅳ級誘導痰上清液IL-6、TNF-α水平高于Ⅰ級和0級,Ⅲ級和Ⅳ級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誘導痰上清液中IL-6和TNF-α濃度與肺功能氣流阻塞指標FEV1%pre、FEV1/FVC%呈負相關。結論 IL-6、TNF-α參與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氣道慢性炎癥過程,并可能在氣道重塑中起重要作用。重度氣流阻塞的穩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體內存在系統性炎癥反應。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誘導痰;IL-6;TNF-α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一種以氣流受限為特征的疾病,研究證實,氣道炎癥尤其是小氣道炎癥是COPD的主要病變和發病的主要原因,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在氣道局部炎癥中起重要作用。但到目前為止,誘發和控制COPD炎癥的機制尚未清楚,可能與氣道內炎癥因子與抗炎介質的失衡,或內源性抗炎機制缺陷有關。氣道局部炎癥機制的研究方法有多種,誘導痰技術由于安全可靠等原因,更適合進行氣道局部炎癥機制的研究。為此,筆者通過測定COPD患者誘導痰液中TNF-α和IL-6的水平,以探討其在COPD發病以及氣道重塑中的作用。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09年3月~2010年12月在筆者所在醫院呼吸科就診的COPD患者共67例,其中男45例,女22例,年齡50~85歲,病程5~40年。所有病例均符合2007年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制訂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診治指南》的標準[1],并在入選前4周內未吸入糖皮質激素,3個月內未全身使用糖皮質激素治療,X線證實無肺炎者,近4周內沒有用過抗生素和無呼吸系統之外的細菌感染者。健康對照組15例,入選標準:非吸煙者,無呼吸道癥狀及心肺等疾患,入選前4周內無呼吸道感染史。排除標準:除外合并支氣管哮喘、支氣管擴張癥等其他慢性呼吸系統疾病,除外合并其他全身炎癥性疾病、過敏性疾病、腫瘤性疾病、系統性免疫功能異常等可能引起補體活化的疾病。全部研究對象均獲得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樣本采集 誘導痰的采集、處理和質量控制參照文獻[2]的方法進行。整個過程盡量在2 h內完成。取無唾液成份的痰液放入離心試管中,加4倍體積的1 g/L二硫蘇糖醇孵育,螺旋振蕩15 min,加入與二硫蘇糖醇等體積的Hank's液,再置于37℃恒溫水浴振蕩箱振蕩15 min使其均勻,3500 r/min(r=15 cm),離心20 min,沉淀細胞作痰液質量檢查,上清液于-80℃凍存待測。沉淀細胞用Hank'液懸浮,在血細胞儀上計數細胞總數,用臺盼藍染色排除法測定細胞存活率。調節細胞懸浮密度至1×106,將75 μl懸浮液置于細胞離心機450 r/min離心6 min,細胞沉渣涂片,風干,吉姆薩染色,每張涂片計數400個細胞。分類計數,鱗狀上皮細胞<20%,細胞存活率>50%提示痰來源于下呼吸道,為合格標本,可進行有關生化測定。
1.2.2 測定TNF-α和IL-6 采用ELISA法測定痰上清中TNF-α和IL-6(美國BD公司生產上海西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試劑盒)嚴格按照試劑說明書操作。
1.2.3 肺功能檢測 所有觀察對象均使用肺功能儀測定肺功能。
1.3 統計學處理 應用SPSS 11.0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計量資料以(±s)表示,兩兩比較運用配對t檢驗,相關資料做直線相關分析,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各組間肺功能指標比較 肺功能指標顯示,COPD 0級、Ⅰ級FEV1%pre與正常組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Ⅱ級、Ⅲ級、Ⅳ級FEV1%pre較正常組明顯降低(P<0.01)。COPD 0級 FEV1/FVC%、MMEF%pre與正常組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Ⅰ級、Ⅱ級、Ⅲ級、Ⅳ級FEV1/FVC%、MMEF%pre較正常組明顯降低(P<0.01)。COPD各級PEF%pre較正常組明顯降低(P<0.05)。COPD 0級RV與正常組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Ⅰ級、Ⅱ級、Ⅲ級、Ⅳ級RV%pre較正常組明顯增高(P<0.05)。見表1。

表1 正常組和COPD各組間肺功能指標比較
2.2 各組間誘導痰上清液中IL-6、TNF-α濃度比較COPD各級患者誘導痰上清液中IL-6、TNF-α濃度均較正常組明顯升高(P<0.01),COPD 0級、Ⅰ級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COPDⅣ級較0級、Ⅰ級、Ⅱ級明顯升高(P<0.01)。Ⅲ級、Ⅳ級較正常組明顯升高(P<0.05)。見表2。

表2 正常組和COPD各組體內IL-6、TNF-α濃度比較
2.3 誘導痰上清液中IL-6濃度與肺功能氣流阻塞指標FEFV1%pre、FEV1/FVC%呈負相關(r= -0.689,P <0.01;r=-0.673,P<0.01);TNF-α濃度與肺功能氣流阻塞指標FEFV1%pre、FEV1/FVC%呈負相關(r= -0.531,P <0.01;r= -0.500,P <0.01)。
3 討論
COPD是一種具有氣流受限特征的疾病,氣流受限不完全可逆,呈進行性發展,與肺部對有害氣體或有害顆粒的異常炎癥反應有關。COPD是由多種炎性細胞及其所釋放的多種炎性遞質、細胞因子參與的復雜的慢性氣道炎癥。COPD急性發作時,病毒或細菌所含的某些抗原成分或代謝產物如脂多糖、內毒素可以激活局部肺泡巨噬細胞產生 TNF-α等炎性因子[3]。這些炎性因子繼而又可促進肺泡巨噬細胞和支氣管上皮細胞產生IL-6、IL-8。由于局部產生的細胞因子吸收入血以及內毒素引起體內單核-巨噬細胞廣泛的激活,導致血中TNF-α升高。學者多次研究發現,COPD急性發作期患者血中IL-6、IL-8水平與TNF-α水平呈明顯正相關。急性感染時,通過巨噬細胞激活使TNF-α的產生增多,而TNF-α可促進炎癥細胞粘附游走和浸潤,迅速引起肺組織損傷,表明TNF-α是COPD病情加重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COPD嚴重程度的重要標志。
TNF-α是具有廣泛生物活性的炎性因子,參與了炎癥過程中中性粒細胞的聚集和活化,使COPD患者氣道黏膜中大量的中性粒細胞浸潤。研究發現,COPD患者誘導痰和血漿中TNF-α水平均較非 COPD患者明顯增高。目前為止,COPD炎癥機制尚未明確,可能與炎性因子和抗炎遞質的失衡有關[4]。隨著局部炎癥的好轉,患者癥狀改善,病情趨于緩解。
本實驗結果顯示,COPDⅠ~Ⅳ級 TNF-α、IL-6表達水平高于正常組,COPDⅠ ~Ⅳ級 TNFα、IL-6表達水平與FEV1%pre值呈直線負相關,提示這些指標在炎性反應的發展過程中均發揮了作用并與氣道重塑有關。
[1]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學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診治指南(2007年修訂版)[J].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2007,30(1):8 -17.
[2]曾勉,劉凌云,張式鴻,等.各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誘導痰細胞成分與肺功能的關系[J].中山大學學報:醫學科學版,2007,28(4):422-425.
[3]Hacker TL,Holloway R,Holqate ST,et al.Dynamics of pro - inflammatory and anti-inflammatory cytoline release during acute inflammation in cllrom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an ex vivo study[J].Respir Res,2008,9(1):472.
[4]王卓,夏國光,姚婉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病原學研究[J].中國全科醫學,2009,12(11):1942.
10.3969/j.issn.1674 -4985.2012.06.007
251800山東省陽信縣翟王衛生院(陳文明);山東省陽信縣人民醫院(黃樹紅,王桂英,喬秀榮)
黃樹紅
2011-12-07)
(本文編輯:梅宏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