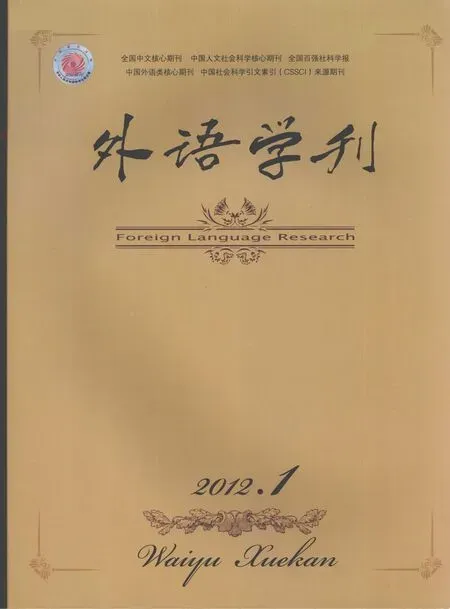論日本文學譯作中的注釋問題
——以山崎豐子作品為例
宿久高 鮑 同
(吉林大學,長春130012)
1 引言
在文學翻譯作品中,每當涉及原作的文化風俗、歷史背景以及語言表達特點等問題時,譯者常在“引用”、“替換”的同時做某些說明,這就是注釋。(王忠亮1991:56)呂叔湘曾經指出:“必要的注釋應該包括在翻譯工作之內。魯迅先生譯書時就常常加注,也常常為了一個注文費許多時間去查書”(林煌天1997:845)。
注釋是由接受主體與原著之間的文化差異而產生的必然現象,同時又是豐富本國語言、固定外來新詞的有效手段。通過固定這些詞匯,我們可以直觀地了解被譯介國家的獨特文化、先進理念和尖端科技。這些獨特文化、先進理念和尖端科技,由翻譯主體——譯者譯介過來,并在譯介過程中根據對接受主體——讀者的接受情況的判斷,做必要的注釋;之后還要觀察讀者的反應,確定新詞的固定程度。隨著不同文明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交匯,注釋作為對原始信息和譯作內容的一種補充,愈發起著重要的作用。
本文在歸納、梳理日本文學譯作中注釋的特點和變化的基礎上,以日本作家山崎豐子作品的中文譯本為例,通過對調查結果的分析,進一步論述譯作中的注釋問題。
2 日本文學譯作中的注釋及其變化
2.1 相對滯后的日本文學譯介
注釋是文學翻譯中最細微的部分,是對原作信息和譯文內容的補充。它將譯文內容(語句)所含信息具體化,使讀者從譯文中最大限度地準確獲取原作信息;另一方面,注釋對原始信息起到制約作用,在保證原作真實性和完整性的同時,更起到規范讀者思維的作用,使各類讀者對譯文信息的認識基本統一。
在我國的外國文學譯介中,俄語專家們較早注意到了注釋問題。王忠亮(1991:56-60)認為:注釋不僅起到解釋、說明的作用,更是“文藝美學的組成部分之一”,是“文學譯著的藝術補償表達”,注釋的作用分為釋源、深化和追加三種形式。“為保持原著的面貌和再現原著的藝術,在文學翻譯中注釋有時不僅完全必要,而且極其重要”。(胡志揮 1980:41)但是,添加注釋應十分慎重,既不能“到處設防”,也不能“畫蛇添足”。
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很長一段之間,與前蘇聯的交流幾乎成為我國國際交流的全部,俄蘇文學的譯介興盛一時;而日本文學的譯介卻相對滯后,對文學翻譯的理論研究更顯不足。另外,在文學作品的選擇上也有失全面,過于強調思想的導向性、文學的社會功能和教化作用,使讀者無法領略到日本文學的全貌。
日本文學的譯介,以“文革”為界分為兩個時期:前一時期中的1953至1965年間,是“日本文學翻譯的最繁榮的階段。……受到特別重視的是戰前和戰后無產階級文學及左翼文學的翻譯。……這些‘應時’作品的翻譯出版,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當時我國的政治文化氣候”。(王向遠2007:182-183)該時期譯作的翻譯風格基本一致,用詞單一化、模式化。“文革”結束后的10年間,我國人文科學逐步恢復,對日本文學的譯介熱情迅速升溫。同時,兩國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不斷壯大了日本文學的讀者群,數量和結構也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到1995年前后,……(日本文學)翻譯的重心向名家名作和流行作品轉移,出版的方式由單本作品向文集化、系列化發展”。(王向遠2007:225)
為了適應這些變化,譯者們在日本文學的翻譯實踐中積極探索語言創新、語體運用及譯法的合理性等翻譯技巧,充分借鑒西方的翻譯理念,不斷總結讀者閱讀習慣的變化,逐步形成了日本文學翻譯的相關理論。伴隨著大量信息的導入,注釋已成為日本文學譯介中最微小的、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2.2 譯者注釋策略的變化
譯者注釋并非出現在原作中。注釋的繁簡多寡,在不同時期、不同題材的譯作中差別十分明顯。其范圍、數量及內容,無疑源于譯者對原始信息——原作的理解和對讀者閱讀水平的判斷,同時也與譯者本身的知識儲備有關。
①于是便知道氏康…,已經切腹(譯者注:用刀橫剖腹部的自殺)而死的事。(魯迅2007:201)
②擦著了火柴,吸一支朝日(譯者注:紙煙的名目)。(魯迅2007:132)
例①②是魯迅譯作中的例子。從中不難看出注釋的精致與細膩,充分考慮到讀者的知識結構。今天看來,“切腹”等注釋完全可以省略,但在當時,讀者與原作的距離較大,這樣的注釋仍然不可缺少。但“朝日”的注釋則無必要,譯成“吸一支朝日煙”即可意蘊皆出。早期譯作中的注釋基本以常識性知識為主,是一種被動的介紹,帶有當時翻譯文學的時代共性,缺少譯者的個性。
隨著時代的變化,文學譯介被賦予了更大的自由,注釋也開始融入譯者的個人偏好。尤其是伴隨著譯文的“異化傾向”,許多新鮮、時尚的詞匯出現在譯文中,注釋的內容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改革開放以后,對作家、作品的介紹更加全面,尤其是女性作家的作品,從純文學擴大到大眾文學,其中對社會派作家、作品的譯介尤多。山崎豐子便是其中之一。
山崎豐子的許多作品敢于直面社會現實問題,徹底剖析社會陰暗面,因而成為日本社會派代表作家。其代表作《浮華世家》(三卷本),1981年由葉渭渠、唐月梅翻譯出版,后又被多次重譯;《白色巨塔》最早于1994年由李成起、何乃英等人翻譯出版,2006年、2009年被重譯,引起我國讀者的廣泛關注。短篇小說《陪嫁錢》、《遺物》,長篇小說《女人的勛章》、《女系家族》、《兩個祖國》、《不毛地帶》、《不沉的太陽》等陸續被譯成中文出版。比較山崎作品的譯作可發現,同一部原作,因譯者不同,翻譯出版的時間不同,注釋的數量和內容也大相徑庭。

表1 山崎豐子作品譯作注釋比較

表2《白色巨塔》譯作注釋分析
如表1、表2所示,《浮華世家》的兩個譯本前后相距25年,由于譯者相同,注釋幾乎未發生任何變化。其中有些注釋內容,如“期貨”、“外務省”、“信用購貨卡”、“壽司”、“新干線”等已為中國讀者所熟知,完全可以省略。而《白色巨塔》的兩個譯本,出自不同譯者之手,時間跨度也長達10年之久,與1994版譯本相比,2006版譯本注釋數量多了近一倍,相同的僅有6處。在2006版譯本中,譯者省去了“近畿”、“厚生省”、“安樂死”等很多基礎詞匯的注釋,取而代之的是更為專業的醫學術語,如“胸廓成形術”、“法洛氏四重癥”、“細胞診”等。這樣的注釋大約25處,約占注釋總數的三分之一,體現出譯者對作品不同角度的解讀和個性化的翻譯風格。
除專業術語以外,譯者用詞的“異化傾向”也是注釋增加的原因之一。在《白色巨塔》2006版譯本中,譯者在詞語的使用、搭配等方面盡量貼近原作,對日語中的漢語詞匯采用了字形直譯的方法。
③(又一)その上、花街の小唄や長唄の會へは必ず顔を出し、…(山崎豊子2002(一):73)
譯文1:此外,每逢花街柳巷舉辦什么長、短歌會時,他也必定露面,…(1994:43)
譯文2:而花街的小唄、長唄(譯者注:日本傳統的音樂藝術)聚會,他也一定參加,…(2006:29)
④(又一)ごぼごぼと咽喉を鳴らして番茶を飲み、…(山崎豊子2002(二):32)
譯文1:咕嘟咕嘟地大口喝起粗茶,…(1994:274)
譯文2: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喝著番茶(譯者注:一種品質較差的日本茶),…(2006:181)
⑤丹前を著た野坂が姿を見せた。(山崎豊子2002(二):82)
譯文1:不久身穿和服棉袍的野坂出現了。(1994:304)
譯文2:不久后,穿著丹前(譯者注:日本人在家穿的御寒棉袍)的野坂走了出來。(2006:200)
⑥(慶子)「まるで、明治時代の異人館ね、…」(山崎豊子2002(二):331)
譯文 1:“這里簡直是明治時代的洋人公館,…”(1994:455)
譯文2:“這里簡直就像是明治時代的異人館(譯者注:外國人的公館),…(2006:295)
例句中的“異化”處理,在讓讀者感受到日本風情的特有表現的同時,引導讀者從最直觀的角度理解作品的審美取向,體會作者的創作意圖。一些直譯詞匯在漢語中尚不多見,因此在讀者完全理解之前必須添加注釋予以說明。
2.3 讀者形態的變化與注釋
譯作的服務對象是讀者,注釋是幫助讀者更好地欣賞文學作品的一種手段,應依據讀者群中大多數人的欣賞水平,適應讀者的需要。但是,在研究翻譯理論時,翻譯的服務對象——讀者對譯文的反應往往被忽視。眾所周知,一部文學作品的讀者群構成十分復雜,既有對日本文學懷有濃厚興趣、深諳日本文化的讀者,也有僅對某部作品感興趣的讀者。譯作的最終目的是將原作的全部信息最大限度地傳遞給讀者。因此,一部譯作的翻譯情況不僅要咨詢專家的意見,更要搜集讀者的反應,傾聽讀者的聲音。也就是說,譯者應該站在作者和讀者兩個角度去思考,去創作,而不應單純從學者的層面去探討。如今,對日本文學譯作的評判一般主要依據發行量和專家的評論,而對于讀者群結構的變化、讀者的理解水平、接受程度等實際閱讀情況,則鮮有人運用合理手段進行調查研究,也少有詳盡資料可供佐證。
相同類型的文學作品,其讀者群也不斷變化。以山崎豐子的小說為例,許多讀者是首先欣賞到由原作改編的影視作品后才重新閱讀原作的。她的16部長篇小說中已有大半被以各種形式搬上銀幕。國人最早接觸山崎是在上世紀70年代,通過觀看根據其同名長篇小說改編的電影《華麗的家族》而實現的,直到1981年才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小說的中文譯本;同年6月,中國電影出版社編寫的《外國電影劇本叢刊》第5期中,收錄了聶長振翻譯的劇本《不毛之地》。進入2000年后,山崎的《白色巨塔》、《女系家族》、《浮華世家》、《不沉的太陽》、《不毛地帶》等5部作品被拍成連續劇。在取得高收視率的同時,也讓許多中國觀眾一飽了眼福。不少青年觀眾在觀賞劇作之后產生了閱讀原作的興趣。讀者中,許多人并非從事與日語相關的工作,僅僅是對日本文化感興趣而已。這些讀者缺乏必要的知識,即使對一些經常接觸到的文化現象(詞匯),大多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有必要通過注釋等手段為他們提供基本的信息補充。另外,由于日語的表達偏向曖昧,往往某個特定詞匯的出現會影響一句話甚至是整段內容,若不能讓讀者理解透徹,便會嚴重影響原著含義的傳達。
3 譯作注釋相關的幾個問題
3.1 注釋效果的檢驗
日本文學作品的翻譯者多是精通日語和相關知識的專業人員。他們不僅能從語言文字上充分體會原作的韻味,更能通過原作的寫作目的、寫作背景等原始資料挖掘出作品的獨特魅力,加之在翻譯過程中的反復研讀,對作品理解幾近貼近作者。因此,在邏輯關系、詞語調配、情感表達等方面都希望將譯文錘煉得盡善盡美。但是,讀者能否從譯文的字里行間獲得同樣的感受,翻譯中的“異化傾向”是否更有效地拉近了讀者與原作之間的距離,則需要認真檢驗并加以探討。目前,譯文的檢驗基本上是由業內的專門人士進行。“征求意見的對象往往只限于‘專家們’,而由于這些專家總喜歡用專業的眼光來看待語言交際,因此有時對譯文能否真正為一般讀者所理解的問題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譚載喜1999:246)
譚載喜(1999:250)依照奈達的翻譯理論曾提出檢驗譯文質量的標準有三:一是“忠實原文”,能使讀者正確理解原文信息;二是易于理解;三是形式恰當,吸引讀者。當然,作為必須忠實傳遞原作信息的譯者,需要兼顧作者和讀者的知識水平和接受能力,不是將原作的信息用直觀、簡潔的方式翻譯過來就能使讀者順利地欣賞作品,而是應該站在大多數讀者的立場上,充分考慮譯文的用詞會在讀者閱讀時發揮怎樣的效應。運用各種手段清除讀者閱讀中的障礙,也是翻譯工作的重要一環。因此,有必要充分考慮讀者群的實際情況,為便于理解和辨別詞義加入合理的注釋。
3.2 “文化空白”與注釋
近年來,“文化空白”成為翻譯理論研究中熱議的話題,“主要體現在詞匯的空缺上,……如何來填補這些空白則成為譯者的義務和職責”。(陶振孝2005:102)中日兩國雖然同屬漢文化圈,所謂“同文同種”,但“異”是絕對的,兩國有著各自不同的文化與傳統。作為島國的日本,其文化尤其體現出島國特有的“內在發展的自律性和外在交流的主體性”。(葉渭渠2005:294)這樣的文化特質,不可避免地給日語中的漢語詞匯附著上了獨特的含義,如度量衡單位詞匯,以及日本人創造的漢語詞匯等。在將這些詞語以同形詞的形式直接植入漢語時,有必要、而且必須加注進行解釋和說明。魯迅先生在翻譯菊池寬的歷史小說《三浦右衛門的最后》時就使用了這種方法。
⑦在去這里四五町(譯者注:三百六十尺為一町,合中尺三十四丈;三十六町為一里)的那邊的街道上,…(2007:197)
⑧揮十八貫(譯者注:一貫約中國六斤四兩)鐵棒如芋梗的勇士,…(2007:204)
葉渭渠、唐月梅翻譯山崎豐子的名著《浮華世家》時也使用了這種方法。
⑨它的幾千町步(譯者注:一町步約等于一公頃)的山林財產就是屬于萬俵家的。(1981:19)
⑩面積達一萬坪(譯者注:一坪為三十六平方尺),…(1981:20)
[11]鋪面有十間(譯者注:一間約為1.8米)寬的太平超級商店門前,…(1981:72)
[12]政府預定在這家三反(譯者注:一反相當于999.7平方米)大小的土地上,…(1981:253)
[13]而且凈是大野豬,每頭凈重(去內臟)三十四貫(譯者注:一貫相當于3.75公斤)。(1981:424)
再如:
[14]北アルプスの峰々が望まれ、鋭い稜線が雲一つない冴えきった空を明確に區切っている。(山崎豊子2002(五):136)
譯文:可以望見北阿爾卑斯山脈的銳利棱線劃開萬里晴空的美景。(2006:351)
例14○是《白色巨塔》中財前五郎在日本金澤出席癌癥學會的一幕。提起“北阿爾卑斯山”,廣大讀者的第一印象往往會聯想到位于歐洲大陸的綿延雪山,而很難想到素有“日本屋脊”之稱的飛驒山脈。類似這樣的詞匯在山崎作品的漢譯本中還有很多,特別是她的晚期作品,很多場景以世界各地為舞臺,涉及的地名、場所繁多。這些對于我國讀者來說并不熟悉的內容,均可以理解為“文化空白”。所以,為保證不使讀者產生誤解,必須要加注說明。
還有一種“文化空白”現象值得深入思考。日語原作中一些用漢字書寫的日本文化名詞,其字形、字義均與漢語相差無幾,采用字形直譯應該是比較理想的手段;但是,恰恰是這些與中國共通的文化名詞,反而成了讀者閱讀理解的薄弱環節。比如:
[15]銀婚式祝いの名目で集めた鵜飼邸の書庫新築費を…(山崎豊子2002(二):390)
譯文:(財前)銀婚而增建書庫的名義籌措到的祝賀金…(2006:317)
[16]特診患者からのお中元だそうだが、…(山崎豊子2002(一):268)
譯文:“這是特診患者送的中元賀禮,…”(2006:108)
首先,銀婚屬于西方傳統文化,傳入我國的時間不長。雖然被認知和推廣的速度很快,但對于一般的中國讀者來說,“銀婚”一詞的概念卻不十分清晰,屬于“文化空白”,需要加注。更應引起重視的是對“中元”一詞的理解。農歷七月十五為我國傳統的中元節,俗稱“鬼節”。佛教與道教對這個節日的意義各有不同的解釋。調查結果表明,很多讀者誤認為是八月十五日。這說明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傳統文化正在受到沖擊。因此,在文學譯作中對該類詞匯加以注釋,不僅可以幫助讀者理解字面的含義,增強譯文的文化底蘊,更是一種傳承我國傳統文化的有效手段。再如譯作中的“玄關”、“中庭”、“伊丹機場”、“懇談(會)”、“知事”、“津輕海峽”等直譯的漢語詞匯,在沒有注釋的情況下,讀者需要借助其他手段了解其含義,影響對作品的欣賞。
3.3 讀音與注釋
日本的出版物對文字要求嚴格,處理周全。出版了山崎豐子全部作品的新潮文庫,對日文漢字的發音尤為重視。其文字使用原則規定:考慮到少年讀者閱讀方便,對難讀的漢字以及固有名詞、專有名詞盡量標注讀音。這項原則惠及的不單單是日本的青少年讀者,也為外國讀者提供了閱讀和研究的便利。在《白色巨塔》2006版譯本中,許多日文漢字被原封不動地翻譯過來,并未加任何注釋。
[17]今津走出南海線的諏訪之森站檢票口,…(2006:200)
[18]終于在丼池筋的布料批發街中擁有了自己的店面。(2006:269)
[19]詢問過辻先生的座位后,…(2006:366)
例17○[18][19]中的三個漢字分別讀作“諏(zōu)”、“丼(jǐng)”和“辻(shí)”。這樣的漢字雖僅僅表示名稱,但發音卻極難掌握,尤其是“丼”這個字,《現代漢語詞典》中沒有收錄;它的基本讀音為“jǐng”,意同“井”;通過網絡搜索可以了解到,江蘇省常州市有個“窯丼村”,用于此地名時讀作“dōng”。此類不常見的詞匯在翻譯時應該加注并標明漢語讀音。
另外,文學作品中的一些表達人物神情、感官、特質等的書面詞匯,其形、意和漢語基本一致,經常被直譯過來。仍以《白色巨塔》為例:
[20]…又一は、揶揄するように云った。(山崎豊子2002(二):50)
譯文1:…又一,用揶揄的口氣說。(1994:284)
譯文2:…又一揶揄地說道。(2006:188)
[21](慶子)一切のものを睥睨しているような強さに満ち充ちているわ、…(山崎豊子2002(二):333)
譯文1:“充滿了睥視一切的力量。”(1994:456)
譯文2:“有種睥睨一切的堅定。”(2006:296)
在上述例句中,被直譯過來的書面詞匯顯得生硬,但若出于文體需要也無可厚非。然而,對于部分讀者而言,對“揶揄(yéyú)”、“睥睨(pìnì)”的發音并不完全掌握、詞義也一知半解,所以,必要的讀音注釋是不可缺少的。由此可見翻譯中注釋的重要性,作為翻譯過程中最細小的工作,會直接影響原著信息的有效傳遞。
4 結束語
譯作注釋的首要功能是信息功能,通過在譯作中添加注釋,不僅可以豐富漢語表達,更是傳播異國文化的有效手段,所以,注釋現象將在譯作中長期存在。隨著中日兩國交流的日益頻繁,日本文學譯作讀者群對日本的了解不斷深入,在今后的日本文學譯作中,注釋現象會不斷發生變化。一方面,介紹傳統文化、基本概念的注釋會逐漸減少;另一方面,隨著翻譯風格的“異化”及原作中新詞的出現,注釋又會出現穩定的新舊更替現象。可以預見,在今后的一段時期內,注釋數量不會發生明顯的增減,但注釋的內容定會由常識向知識轉變,由一般性信息向富有日本獨特文化內涵的深度信息轉變。這也是文學翻譯注釋發展的內在規律和必然趨勢。文學翻譯注釋發展的這一規律和趨勢,對翻譯者的知識積累和判斷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譯者首先要重視注釋的作用,并在注釋添加的基本認知上取得共識。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發揮橋梁作用,增進中日兩國的相互理解,最大限度地拉近兩國文化的距離。
胡志揮.略談文學翻譯中的注釋[J].外國語,1980(6).
李在輝.早期受控之魯迅的翻譯選擇[J].外語學刊,2011(3).
林煌天.中國翻譯詞典[Z].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魯 迅.魯迅譯文選集(短篇小說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
山崎豐子.女系家族[M].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7.
山崎豐子.女系家族[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
山崎豐子.白色巨塔(上、下)[M].南京:譯林出版社,1994.
山崎豐子.白色巨塔(第一部)[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
山崎豐子.白色巨塔(第二部)[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
山崎豐子.浮華世家(上部)[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
山崎豐子.浮華世家(上卷)[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
譚載喜.新編奈達論翻譯[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9.
陶振孝.現代日漢翻譯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王向遠.日本文學漢譯史[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
王忠亮.關于文學翻譯中的注釋問題[J].外語學刊,1991(2).
葉渭渠.日本文化史[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康東元.日本近現代文學翻譯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趙稀方.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新時期卷[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
山崎豊子.白い巨塔(一~五)[M].東京:新潮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