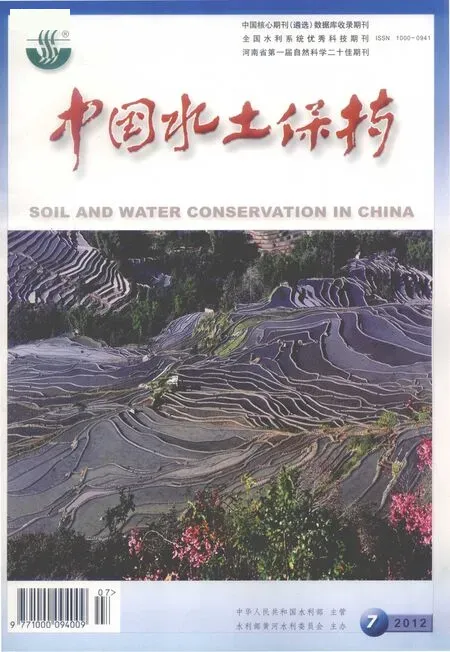侵蝕紅壤區不同水土保持措施的土壤改良效果研究
喻榮崗,楊 潔,王 農,張靖宇,魏 偉,付 濤
(江西省水土保持科學研究所,江西南昌 330029)
侵蝕紅壤區是我國土壤侵蝕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土壤侵蝕面積達25萬km2,占東南部紅壤面積的22%,是我國水土流失治理的重點區域之一。因此,開展侵蝕紅壤區水土保持措施的環境效應研究,不僅可以豐富我國水土保持學科的研究內容,加深對侵蝕紅壤區水土流失治理效果的認識,而且可以為區域土地整治提供重要的理論依據和技術指導,具有重要的科學意義和實踐價值。
在水土保持措施的多種效益中,土壤改良效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水土保持措施最直接、最基本的一項效益[1]。土壤肥力是研究土壤改良效益的重要指標[2-9],是水土流失區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和土地生產力提升的重要基礎。本研究以江西省水土保持生態科技園的牧草、耕作、梯田等水土保持措施的不同處理小區為研究對象,分析了不同水土保持措施的土壤肥力分異情況,旨在為紅壤侵蝕區高效水土保持治理措施的選擇和植被恢復的土壤改良效果提供評價依據。
1 研究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試驗布設在位于博陽河西岸的江西省水土保持生態科技園內(115°23'—115°53'E,29°10'—29°35'N)。研究區海拔30—100 m,坡度小于25°,屬淺丘崗地。年均降雨量1 469 mm,年均氣溫16.7℃,日照時數1 700~2 100 h,無霜期249 d,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區。土壤為第四紀紅色黏土,森林植被為常綠闊葉林,植物種類繁多,但由于長期過度開發利用,因此地表植被遭到破壞,水土流失嚴重,其流失面積占土地總面積的85.6%,且土壤侵蝕以水力侵蝕為主。
1.2 試驗小區設計
在同一坡面上布設標準小區(5 m×20 m),小區坡度12°,坡面植被類型為果園。試驗設牧草、耕作、梯田和對照4個處理,各個處理的重復數分別為6、2、4和3個。牧草處理采用牧草(百喜草、雀稗草、狗牙根)覆蓋坡地,小區植被覆蓋度為80%~95%;耕作處理播種黃豆和蘿卜,每年4月12日至8月10日種黃豆,8月12日至次年3月12日種蘿卜,不施肥;梯田處理梯壁植百喜草,田面植柑橘樹;對照處理為全區裸露。小區管理均按《水土保持試驗規范SD239—87》部頒標準進行。
1.3 土壤樣品采集和分析
2006年9 月在研究區內采集0—20 cm表層土壤樣品。采樣時,去除表層未腐解的枯枝落葉,每個小區隨機選取5點用土鉆采集土壤樣品并混勻風干,分別過1 mm和0.25 mm篩備用。
測定土壤樣品的有機質、全氮、全磷、全鉀、速效氮、速效磷、速效鉀、pH值,分別采用丘林法、開氏法、酸溶-鉬銻抗比色法、氫氧化鈉熔融法、火焰光度計法、堿解蒸餾法、Olsen法、火焰分光光度計法和酸度計法測定。
方差分析(ANOVA)、相關性分析(CORR)、主成分分析(PRIN COMP)通過SPSS軟件進行。
2 結果與分析
2.1 侵蝕紅壤區坡地裸露對照區土壤養分流失特征
表1為研究區坡地裸露對照區2001年與2006年土壤pH值及養分對比情況,通過比較可以看出,從2001年到2006年土壤酸度加大,養分含量下降,土壤肥力退化嚴重。經過5年侵蝕后,土壤pH值降低了0.17個單位,有機質、全氮、全磷和全鉀分別降低24%、26%、13%和7%,土壤速效氮、磷、鉀分別降低了44%、23%和2%。

表1 裸露對照區2001年與2006年土壤pH值及養分對比
2.2 不同水土保持措施對土壤性質的影響
圖1為不同處理措施下的土壤性質,表2為不同處理措施下的土壤性質方差分析結果。由圖1、表2可看出,不同水土保持措施顯著改變了土壤pH值和有機質、全氮、堿解氮、全磷、速效磷含量,但對土壤鉀素狀況影響不顯著。

圖1 不同處理措施下的土壤性質

表2 土壤性質方差分析結果
本研究中不同水土保持措施顯著改變了土壤pH值(圖1、表2)。牧草處理和耕作處理顯著增加了土壤pH值(增幅分別為15%和8%,p<0.05),梯田處理也增加了土壤pH值(增幅2%),但是其增加不顯著(p>0.05)。土壤pH值的顯著增加表明牧草和農作物的生長有利于阻止侵蝕條件下的土壤酸化,這可能與這兩種措施對土壤鹽基離子的截留和保持有關。在侵蝕紅壤區,土壤酸化的主要原因是土壤鹽基離子減少。在牧草和農作物生長的條件下,植物根系對土壤起到了固持作用,減少了土壤顆粒的流失,也減少了土壤中鹽基離子向下層土壤的淋溶以及流失,從而緩解了土壤的酸化,因此與對照相比,土壤pH值顯著升高。對于梯田來說,土壤流失可能比較少,但是梯田截留的雨水比較多,這部分雨水沿坡面流出小區的部分較少,就地入滲的較多,其土壤中鹽基離子向深層土壤的淋溶也強于其他兩種處理,因此梯田土壤pH值低于牧草和耕作處理而高于對照處理。另外,不同處理措施下土壤pH值的差異還與土壤有機質狀況有關。
不同水土保持措施下土壤有機質含量差異顯著(圖1、表2)。牧草和耕作處理土壤有機質含量分別高于對照處理36%和44%且均差異顯著(p<0.05),梯田處理有機質含量高于對照處理11%但差異不顯著(p>0.05)。土壤有機質不但與土壤肥力狀況有關,而且在土壤抵抗侵蝕作用方面有著重要作用。研究結果表明,牧草和耕作處理可以顯著改善土壤有機質狀況,表明這兩種措施可以改善土壤肥力,提高土壤抗蝕性。牧草和耕作處理措施下土壤有機質的改善主要與植物根系生長有關:一方面,根系生長過程中與土壤顆粒密切結合在一起,形成網狀結構,可以明顯降低侵蝕過程中的土壤流失,從而保護了土壤中固有的有機質;另一方面,根系在生長過程中的分泌物可以補充土壤中的有機質,加上根系周轉過程中對土壤有機物質的補充,土壤有機質含量得到顯著提高。此外,牧草和農作物收獲后的殘茬及枯枝落葉也是土壤有機質的一個重要來源。對于梯田土壤來說,梯田建設減少了隨徑流流失的土壤顆粒,因此減少了這部分土壤的有機質流失,從而使其有機質含量高于對照。但是與牧草處理和耕作處理相比,梯田土壤沒有有機物料來源,其土壤有機質得不到補充,因此含量低于牧草和耕作處理。
不同措施對土壤氮素的影響總體來說與土壤有機質相似,即牧草和耕作處理全氮和堿解氮顯著高于對照,這兩個處理的全氮分別比對照高34%和48%(p<0.05),堿解氮比對照高19%和55%(p<0.05),而梯田處理土壤全氮和堿解氮與對照處理接近(p>0.05)。牧草和耕作處理對土壤氮素的影響除與植物根系對土壤顆粒的保持所保持的氮素和根系分泌物釋放、根系和植物殘體補充的氮素有關外,還與植物對土壤保護后增加的氮素固定有關。地表植物生長后改善了土壤微環境以及地表的微氣象環境,有利于土壤固氮菌的活動,從而增加了土壤自生固氮能力。而農作物中的豆類植物本身就具有固氮作用,其生長過程顯著補充了土壤氮素含量,因此耕作處理氮素含量也高于牧草處理,也因此區別于不同水保措施對土壤有機質的影響趨勢。這些結果表明牧草和耕作處理可以顯著提高土壤氮素水平及其有效性。
牧草和耕作處理土壤全磷和速效磷含量顯著高于對照,這兩個處理的全磷含量分別比對照高23%和54%(p<0.05),速效磷比對照高109%和229%(p<0.05)。梯田處理土壤全磷和速效磷含量高于對照11%和24%,但是差異不顯著(p>0.05)。在侵蝕條件下,土壤磷素主要通過徑流損失,牧草和耕作處理中植物根系對土壤顆粒的固定和保持顯著減少了土壤磷素的損失,因此其全磷和速效磷含量顯著高于對照;梯田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土壤顆粒的流失,其土壤全磷和速效磷含量也高于對照。此外,牧草處理和耕作處理土壤磷素差異較大,這可能與不同植物對土壤磷素的吸收強度有關。這些結果表明牧草和耕作處理可以顯著提高土壤磷素水平及其有效性。
與對土壤pH值、有機質和氮磷素養分含量的影響不同,不同水土保持措施對土壤鉀素狀況的影響不顯著(表2、圖1),表明研究區在侵蝕條件下土壤鉀素不會成為土壤養分的限制因素,在以后該區土壤養分狀況研究中可以忽略鉀素因子。
2.3 土壤肥力指示指標篩選
本研究選擇pH值、有機質、全氮、全磷、全鉀、堿解氮、速效磷、速效鉀等8個指標來衡量試驗區域的土壤肥力水平。土壤養分性狀指標的相關性分析(表3)表明,大部分土壤指標之間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其中土壤有機質、全氮、全磷、堿解氮、速效磷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另外,pH值與有機質、全氮、速效磷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速效鉀與全鉀之間有一定相關性,但兩者與其他土壤養分指標的相關性不明顯。

表3 土壤養分性狀指標相關性分析
在主成分分析中(表4),因子1、2的特征值都大于1,分別解釋了總方差變異的59.250%和21.249%,累計貢獻率超過80%。公因子方差也表明,除了全鉀外,各變量的解釋方差都超過了80%(表5)。在因子1上,土壤有機質、全氮、全磷、堿解氮、速效磷等都有較高的正負載,由于因子1所包括的變量都與有機質顯著相關,所以將其命名為“有機質”因子;在因子2上,速效鉀有較高的正負載,雖然全鉀也有較高的正負載,但后兩者公因子方差小,所以將其命名為“速效鉀”因子。

表4 不同措施土壤化學性狀指標主成分分析的特征值與負荷量

表5 不同措施土壤化學性狀指標主成分分析
通過主成分分析,將指標歸結為兩個因子,不同措施下養分性狀指標的差異可以通過兩個因子的綜合值體現出來。“有機質”因子(因子1)值越大,土壤有機質、全氮、全磷、堿解氮、速效磷含量越高,土壤肥力水平越高;“速效鉀”因子(因子2)值越大,則土壤速效鉀、全鉀含量越高。本研究中,由于不同措施對土壤鉀素含量影響不顯著,而且土壤肥力狀況不受鉀素限制,不同措施下土壤有機質變化趨勢與其他養分指標變化趨勢相似,因此在研究區可以利用有機質因子作為衡量土壤肥力狀況的簡化指標。
3 結語
研究結果表明,不同水土保持措施顯著影響侵蝕紅壤區坡地土壤pH值和有機質、全氮、堿解氮、全磷、速效磷含量,但對全鉀和速效鉀含量影響不顯著。牧草和耕作措施可以顯著提高土壤pH值和有機質、全氮、堿解氮、全磷、速效磷的含量,可以顯著改善土壤肥力狀況。研究區土壤肥力狀況不受鉀素限制,可以利用土壤有機質作為衡量土壤肥力狀況的簡化指標。
[1]沈慧,姜鳳岐.水土保持林土壤肥力及其評價指標[J].水土保持學報,2000,14(2):60 -65.
[2]史德明,韋啟潘,梁音,等.中國南方侵蝕土壤退化指標體系研究[J].水土保持學報,2000,14(3):1 -9.
[3]沈慧,姜鳳岐.水土保持林土壤改良效益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J].北京林業大學學報,2000,22(5):96 -99.
[4]康玲玲,王云璋,劉雪,等.水土保持措施對土壤化學特性的影響[J].水土保持通報,2000,23(1):46 -48.
[5]謝錦升,楊玉盛,陳光水,等.嚴重侵蝕紅壤封禁管理后土壤性質的變化[J].福建林學院學報,2002,22(3):236-239.
[6]劉暢,云麗麗,葛成明.遼東山區不同森林類型土壤改良效益分析[J].防護林科技,2005(1):21-22.
[7]柳云龍,王人潮.低丘侵蝕紅壤墾種綠化后土壤結構、養分積聚和持水性能[J].水土保持學報,2000,14(4):79 -82.
[8]邰通橋,杭朝平,楊勝俊.果園套種綠肥對果園土壤改良的效果[J].貴州農業科學,1999,27(1):35 -37.
[9]王震洪,段昌群,文傳浩,等.滇中三種人工林群落控制土壤侵蝕和改良土壤效應[J].水土保持通報,2001,21(2):2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