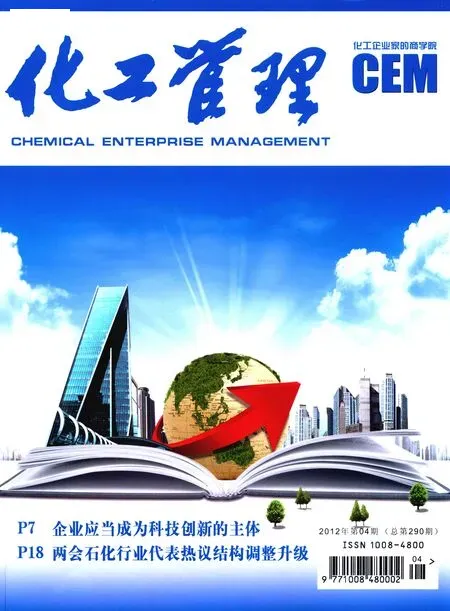從兩會看中國未來經濟走向
文/陳二厚 劉 錚 等
2012年的“兩會”已經勝利閉幕,總結今年的兩會,一個聲音越來越響亮,即抓機遇、促改革、謀發展。這是兩會凝聚的共識,也是人民的心聲,更是預示中國未來走向的鮮明信號。
一種意識更加迫切:應對挑戰時抓住機遇,全球變革時用好機遇,穩定和諧時創造機遇
當時光的列車駛進2012年,中國發展又處在一個關鍵節點:本世紀頭20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已經過半,前半段“賽程中”,從鄉村到城市,從個體到國家,一扇扇機遇之門被打開,緊緊抓住機遇的中國人,不斷創造發展奇跡:中國經濟實現年均10%的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居世界首位。
與此同時,困難和挑戰迎面而來環顧國際,金融危機陰霾未散,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持續發酵,主要發達經濟體仍然深陷泥潭,外部環境更趨復雜嚴峻;審視國內,經濟增長下行與物價上行壓力并存,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部分企業經營困難,緩解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更為迫切,難度更大。“我們還有沒有機遇”,“還有多大機遇?”面對復雜嚴峻的形勢,兩會內外,“中國機遇”成為人們關注、討論和思考的話題。“從發展的要素看,中國潛力巨大。只要發揮出來,足以支持我國經濟20年快速增長。”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基于對經濟增長潛力的定量分析,拿出一份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賬本”。
“中國經濟發展潛力不可估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對鄭新立的看法深表認同。“關鍵是要通過調整和改革,向潛力要機遇,把它變成實實在在的發展支撐。”鄭新立說。

歷史發展證明,抓住機遇,就能爭取主動,贏得發展;喪失機遇,就會陷于被動和落后。失去的將不僅僅是時間和財富,也可能是國家的強盛和民族的尊嚴。
“在當代中國,穩定和諧是最大的機遇。”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教授胡鞍鋼認為,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不僅能創造巨大的機遇預期,也是實現一切機遇的基礎。反之,社會大局不穩,已經抓住的機遇也會失去。
“經濟上不能大起大落;政治上不折騰;社會上不折騰;生態上不折騰;國際上不折騰別人,別人折騰我們要理性回應。”胡鞍鋼說,“面對紛繁復雜的內外部環境,守住這五個底線,中華民族就一定能夠創造偉大復興的戰略機遇。”
一股動力已經積蓄: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改革,以更周密系統的頂層設計攻堅克難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經濟學家厲以寧在談到改革時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經濟好比人的身體。宏觀政策的調整是通過外力對經濟起作用,就如同人生病了靠吃藥來恢復。而改革是讓經濟這一“肌體”依靠制度制約,具有內部調整和促進發展的功能。“從外生轉變為內生,改革解決的就是這樣一個問題。”
和厲以寧委員一樣,兩會期間,“改革”成為代表委員審議討論中出現頻率最高、觸及面最廣的話題之一。
3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我國生產力得到空前發展,成為支撐中國發展奇跡的根本動力。今天,已過而立之年的改革,為何再掀熱議?
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有了繼續推進改革的共識,但前行的道路并不平坦。代表委員認為,當前改革面臨三重困境:協調利益分配難、推動政策落實難、很多問題久拖不決且矛盾重重。
中國正面臨雙重轉型:既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現代化社會,同時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兩個轉型疊加在一起,而且第二個轉型在世界發展史上沒有先例可循。“這些因素決定了在中國改革的艱巨性。”厲以寧說。
改革開放初期,發動一項改革往往能找到普遍受益點。“現在這個點很難找。”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所長聶高民說,“當時存量動不了動增量,現在增量和存量是聯動的,怎樣對待既得利益是改革的難題。”
破解難題,需要更大的決心和勇氣。
“政府工作報告中出現了70次‘改革’。改革就是要有政治勇氣,下定決心。要想找一個所有人都贊成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情。經過充分論證后,多數人認為正確,就是下決心的問題了,下決心后改革是可以推進的。”鄭新立說。
破解難題,需要更科學周密的謀劃和設計。
“30多年前的改革,無論是聯產承包制、鄉鎮企業改革還是股份制,都是摸著石頭過河,由民間自發、‘自下而上’式的改革。”厲以寧說,“今天的改革,更需要的是‘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這就要求改革的決策者要具備戰略家的眼光,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將整個戰略布局做得更好。”
不過,厲以寧同時強調,“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是改革中無法分開的兩面,在統籌考慮通盤問題的同時,當然要吸收群眾的智慧。“不調動民間蘊藏的積極性,改革將無法進行。”
破解難題,需要更清晰的路徑。
深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推動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深化價格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積極穩妥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加快推進政府改革……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了今年改革的重點任務。
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理順中央與地方及地方各級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理順城市與農村的關系,理順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關系,理順政府與公民和社會組織的關系。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把理順五大關系,作為今后一段時期改革的重點和關鍵。
“有了適合的水分、濕度、光照等環境條件后,蘑菇自然會成群長出來。政府不要自己種蘑菇,也不要希望從中挑選蘑菇。”徐冠華委員用“蘑菇論”比喻政府職能的轉變。他說,要打破計劃經濟延續的舊體制、舊思維,資源配置不是由政府主宰,而是要由市場來主宰,政府來創造環境。
共識已經凝聚,動力不斷積蓄,路徑更加清晰。
用科學發展破解“發展瓶頸”,避免“發展陷阱”,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0.5 個百分點!這個看似不起眼的數字,兩會期間吸引了海內外關注的目光。
政府工作報告將中國經濟增速預期目標定為7.5%,這是8年來首次低于8%。
站在更寬廣的歷史背景下審視,GDP增速只降半個百分點,絕非無關緊要,在發展的坐標上,這是一個信號,意味著中國走更加科學的發展道路。
經過30多年來年均增速接近兩位數的經濟增長,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重大成就,但發展的瓶頸制約也逐漸加劇:國內外新的形勢,決定著原有的過于依賴出口、過于依賴資源能源消耗、過于依賴要素投入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已經難以為繼,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日益凸顯。
世界經濟發展史還表明,在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由于經濟發展的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或受外部沖擊,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跌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難以自拔。
如何破解發展瓶頸?如何避免跌入發展陷阱?道路只有一條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實現科學發展。
在厲以寧委員看來,科學發展觀與傳統發展觀有四大區別:傳統發展觀重物輕人,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傳統發展觀重生產輕生活,科學發展觀生產是為了人,人不是為了生產,不斷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傳統發展觀只重視GDP、GDP至上,科學發展觀認為GDP是重要的,但絕不唯GDP是從,總量固然重要,結構更重要,增長是有質量的;傳統發展觀不重視可持續發展,科學發展觀重視社會的可持續性,走的是綠色、低碳的經濟發展之路。
在59歲的農村婦女辛喜玉眼里,科學發展就是她正在做的“清潔養殖、清潔種植、減農藥、減化肥”。
走科學發展之路,必須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步伐。
“下一步中國發展的重中之重,是‘轉型’。”鄭新立說,“要調整需求結構,擴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要調整產業結構,重點發展第三產業;要調整要素結構,通過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來推動經濟增長;要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建立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機制來加快農業的現代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要處理好內外經濟關系,由引進來為主轉變為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
走科學發展之路,必須更加凸顯“以人為本、民生優先”“發展到了一定程度,更需要妥善解決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比如征地拆遷、安全生產、食品藥品安全、收入分配、道德誠信等方面問題還很突出。”吳焰委員說,“解決這些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更需要科學發展,真正把人作為發展的主體和目的,解決好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保障好基本民生,讓人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嚴。”
走科學發展之路,必須由“單向推進”走向“整體協調”,“一條腿再長,也走不好路。要改變單純發展經濟的思路,下大力氣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胡鞍鋼說,“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更長時期、更高水平、更好質量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