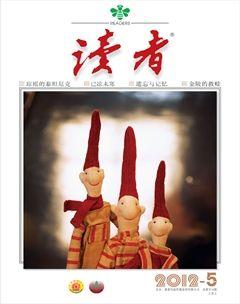遺忘與記憶
押沙龍

博爾赫斯在一首叫《邊界》的詩里寫道:
在黎明我仿佛聽見了
一陣繁忙的喃喃之聲,
那是遠去的人群;
他們曾經熱愛我,又遺忘我;
……
這幾句詩寫在大約80年前,但它如同給互聯網時代寫下的注腳。有人說詩歌是永恒的,也許就是這個意思吧。在互聯網上,我們每天都能看到“繁忙的喃喃之聲”。這些喃喃之聲表達著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熱愛與憤怒——當然,還有遺忘。被人遺忘的一具具網絡化石,安靜地躺在數碼流之下。我想如果它們能開口的話,也會說出這樣的話:“他們曾經熱愛我,又遺忘我。”
即使如舉國關注的動車事故,在微博上,也會很快退出熱點話題榜。人們曾追問一件事:是誰的責任?答案尚未得出,追問的熱情已趨消退。至于“7·23”之前的郭美美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我是沒搞明白,但是現在也成了網上的陳年往事。如果我們再往前推,3年前的膠濟鐵路撞車,現在還有幾個人記得它?而4年前的“周老虎”“重慶釘子戶”呢?即使是驚天動地的汶川地震——如果你沒有生活在四川,還會經常想起來嗎?
他們在搞接力賽,我們在看連環畫,這就是網絡現實。大家對熱點的關注是有期限的,老話題總是被新話題取代。我看過一份《網絡輿情熱點事件的特征與統計分析》,里面對網絡熱點做了一次統計,它的結論是:每個網絡熱點議題的平均存活時間是16.8天,然后就慢慢地被遺忘了。小時候大家都聽過狗熊掰玉米的故事。網絡就像一塊巨大的玉米地,我們則是那只愉快的狗熊,胳膊下面夾著兩個玉米,身后一片狼藉。
據說魚的記憶只有7秒。如果在魚缸里放一個會放電的球,它每次碰到球就會被電一下,那么它也最多會躲避這個球7秒。7秒過后,它又會在魚缸里樂呵呵地游著,直到自己被電得遍體鱗傷,再也游不動為止。它是水缸里的魚,我們是網絡里的人,我們進化到了16.8天。我們壓倒性地戰勝了魚,但我不知道這事是應該慶祝,還是應該傷感。
因為生物的本性就是如此。一幅再優美的畫,你能站在前面心滿意足地欣賞一年嗎?一個再正義的人,能對著一件事熱情高漲地憤怒一年嗎?一般人的小宇宙強大不到這個地步。憤怒是一種力量,但要正確運用這種力量,還需要有別的東西。
在這里,我想停下來講一件美國往事。現在,我們認為美國官員是相對廉潔的,但在100多年前,美國政壇腐敗得驚人。坦慕尼大廳是紐約市民主黨的權力中心,也是一個腐敗的老窩。它的老大是特威德,他手下的貪污集團統治紐約長達10年。從市長到司庫到法官,全是這個集團的人。他們把紐約市民當肥豬一樣宰。承包商做任何投標,都要向他們交付10%的回扣,而且這個百分比不斷攀升——15%、50%、60%,在有些合同中,竟高達85%。
他們主持修建紐約法院大樓的時候,買個溫度計就花了7500美元,買掃帚花了41190美元;5個死人被他們邀請出來領工資。到了最后,整個大樓的成本是英國議會大廈的4倍!這樣“奮不顧身”的貪污取得了“豐碩成果”。據歷史學家估計,這個集團總共貪污了約5000萬~2億美元——這可是150年前的美元。
許多紐約市民對此感到憤怒,卻想不出什么辦法趕走特威德。直到1871年,事情出現了轉機。《紐約時報》編輯喬治·瓊斯掌握了特威德集團貪污受賄的材料,都是真實有效的影印件。特威德向他出價500萬美元購買這些影印件,瓊斯拒絕了。他在《紐約時報》上公布了這些證據,這引發了一次憤怒的狂潮。特威德始終保持沉默,希望把這件事拖過去。如果怒潮一直保持無序狀態,他確實可能逃脫。但轉折點很快到來了。70位市民代表自發組成委員會調查特威德集團的犯罪活動,這標志著無序怒潮轉化為正式行動。此時的特威德已在劫難逃。緊接著開始啟動司法程序,大陪審團以120條罪狀指控特威德,他于1871年12月16日被逮捕,并被判處12年監禁。特威德集團隨之土崩瓦解。
從紐約人的憤怒到特威德集團的崩潰,中間有兩個最關鍵的因素。一個是喬治·瓊斯。他的背后是《紐約時報》,它具有公信力,又有能力做深入調查。這恰恰是互聯網所缺乏的。喬治·瓊斯把民間模糊的憤怒轉變為一記結結實實的重拳,但是特威德依舊可能躲過這記重拳,紐約人的憤怒同樣可能變成遺忘,這就需要第二個關鍵因素:70位市民代表組成的調查委員會。憤怒通過正式渠道轉變為行動,這個行動又啟動了司法程序。
魚就是這樣躲過了電擊。憤怒也就是這樣戰勝了遺忘。
(紫菱洲摘自《博客天下》2011年第24期,劉 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