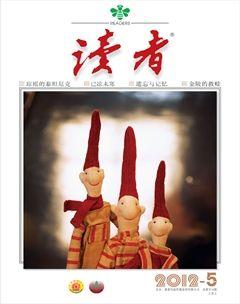和你在一起
素貓

一
感謝今年夏天的那場暴雨還原了真相。
7月26日,我從出差地北京回廣州。因為沒買到直航的機票,又要趕著回去上班,我選擇了在長沙中轉。
傍晚時分,飛機降落在長沙。從長沙飛往廣州的飛機,等了足足3個小時,依然沒有起飛。外面暴雨如注,我決定干脆先不走了,回家看看老媽去。
到家時,擔心老媽已經睡了,我直接掏了我的鑰匙開門——2005年去廣州工作之前,老媽特地囑咐我要帶上家里的鑰匙。她說,人在外面漂著,有把家里的鑰匙,心里就踏實。
一個人在外面又苦又難覺得再也混不下去的時候,我就想想老媽的這句話,像她說的,怕什么,大不了就回家。
鑰匙塞進鎖孔,輕輕旋轉,我推開了門。可是,我的一只手卻停在了脫鞋的動作上。房間里沒開燈,電視早已沒了節目,只余下沒有聲息的雪花點在屏幕上閃動,灰白夾雜,正映著對面沙發中沉沉睡去的老媽——她蜷縮在沙發上,腳上的拖鞋掉落了一只,還有一只半掛在腳上。曾經年輕的她總是要攬著我的肩膀,帶點嘲笑地指指我的頭頂,說還夠不到她的下巴呢。她怎么一下子就變得這么瘦小單薄了呢?
屋里潮濕又黏膩,大概是出了汗,她的衣服緊緊地貼在身上。一切都靜悄悄的,只有墻壁上那只模樣老舊的石英鐘在走,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
我重重地吸了一下發酸的鼻子,她驚了一下,轉過身來。看到我意外出現,她半錯愕半高興地對我說,怎么招呼都不打就回來了,接著慌里慌張地趿拉上拖鞋,走過來接我手里的東西。
有些疑問溜到了嘴邊,又被我咽了回去:就在我上飛機之前給她打電話時,她還在電話那頭興高采烈地對我說,她今天剛去泡過溫泉,晚上準備舒舒服服睡一覺。很明顯,她沒去泡溫泉,是沒成行,還是根本就沒有這個計劃?
我心里的疑問還有很多。
二
給爸爸料理完喪事,我不顧媽媽的勸阻,把她接到廣州住過一陣子。那時候,我跟肖勇戀愛一年多,我們租住在天河區一套一室一廳的房子里。
我和肖勇工作都很忙。我怕老媽無聊,特地裝了有線電視,還硬塞給她500塊錢,讓她去跟小區里的那些老太太們一起搓搓麻將。
有天下午,我采訪時崴了腳,跟主任告了假回家。還沒走到小區的小花園,就聽到一幫老太太把麻將搓得嘩啦響,間雜著歡聲笑語。我想,老媽這下找到組織了。可是當我走近,轉頭望向那個小花園時,發現老媽正一個人坐在角落里的排椅上,望著幾株扶桑花發呆。
我走上前,拍拍媽媽的肩,這時我才發現,她懷里正抱著爸爸的遺像。我想說點什么緩和一下氣氛,但是,話卻卡在了喉嚨里。從那之后,再有需要加班的采訪,我盡量跟主任告假。這樣的情況多了,我開始明顯感覺到主任有意見。而工作量的減少帶來的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我那個月的收入從七八千元一下子減到了兩千多元。
起初,肖勇對放在客廳里的遺像沒有什么表示,但是一個半月后的一天,他似乎是鼓足了勇氣,又欲蓋彌彰地指著放爸爸遺像的博古架位置說:“小娟,你說要不要在這里放一盆綠蘿啊?”我狠狠地剜了他一眼,同樣欲蓋彌彰地放大了聲音說:“不行!”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件事最終促使老媽離開了廣州。總之,一周之后,老媽回了株洲,臨走前,她還給了我2000塊錢,我給她的那500塊錢就在里面,原封未動。
老媽再也沒有跟我們一起住過。不過,自從從廣州回去,她倒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電話打過去,不是和朋友在附近爬山,就是正在朋友家聚餐,又說要跟隨區里的老年模特隊去大連表演。每次聽到她在電話那端快活的聲音,我的心一下子就晴空萬里。她說,她現在想開了,該吃吃,該喝喝,要把以前虧欠的日子給補上。我舉雙手表示贊同。
可是,在這個因大雨滯留的夜晚,我在床上輾轉反側,老媽的生活真的像她所說的那樣嗎?
三
第二天一早睜開眼,我最愛的牛肉粉已經買回來放在桌上。
“吃吧!”她給我打包,“時間太緊,沒什么可給你帶的。”她裝了一兜干湯粉,又裝了一袋子豆絲,都是我愛吃的土特產,把行李箱塞得滿滿當當的。
出門的時候,她說:“不送你去車站了,今天我忙著呢,約了老朋友們去跳舞。”
我給她打電話:“走了。”她嗯了一聲:“走吧。”
9點多的時候,老媽從小區里走了出來。隔著幾十米的距離和人群,我偷偷地跟在她的后面。是的,我沒走,我改變了我的行程安排,我只想弄明白她的一天究竟是如何度過的。
10點,她去了菜市場,花了大半個小時在菜市場里轉來轉去,最后買了一小把青菜。出了菜市場,她就徑直去了江堤公園。早上的江邊,風獵獵的,老媽就坐在江邊的木頭凳子上,看著老年舞蹈隊的人跳舞,吃隨身帶著的蘋果,偶爾逗逗路過的小狗小貓,或者和推著嬰兒車的老大媽搭上三言兩語。
兩個多小時里,她一直這樣打發著時間。
直到這時,我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傻:家里的幾門親戚早隨兒女舉家遷去了沿海或發達城市,她工作幾十年的廠子倒閉后,幾個要好的同事來往得越來越少。我怎么就能輕易相信她描述的那些生活呢?
中午1點多,人漸漸多了起來。我看著母親的背影,她到底老了,背有點微微駝起。風吹起來,她那單薄的灰白頭發在風里像一把稻草。
這時老媽終于起身活動。她徑直走到公園角落里的一個女人面前,看得出來,她們很熟絡。老媽順勢坐在她面前的小板凳上,就絮絮叨叨地說開了。隔得遠遠的,我聽不見她在說什么。但是她想要說的話顯然很多。她幾乎沒有停歇地說啊說,我遠遠地看著她的嘴巴一動一動的。我從來沒想到老媽的話竟然如此之多,她一貫對我言簡意賅,主題明確,從不拖泥帶水,她也一直都是這么教育我的。
我瞅了瞅周圍,除了老媽,角落里還零星地坐著幾個年齡不等、面相和善的女人。她們的面前,也坐著一些人,多半是些老人。
而離我最近的一個女人,她的腳邊立著一個小瓦楞紙板,上面寫著:陪聊天,一小時十五元。
我愣住了。
四
沒有舞蹈隊,沒有模特隊,沒有充實得快飛起來的生活,甚至連個坐在對面說說話的人都沒有——原來什么都沒有。
我疾步走到老媽面前,剛喊了一句“媽……”就泣不成聲了。她有些手足無措,我拽住她的手就走。后面的那個女人說:“哎,還沒給錢哪!”我塞給她一張20元的鈔票,拽著老媽朝家里走。我一邊走一邊哭,她在找話題,一個勁兒地說:“你怎么沒走呢?”“你看看你這孩子!”“你說你哭什么啊?”最后,她小心翼翼地說:“唉,也不是沒朋友,以前也參加活動,但就是覺得,干什么都提不起勁。”
我陪她去菜市場買了菜,挽起袖子下廚房,做了她最愛吃的梅干菜扣肉,又溫了一壺老酒。我們面對面喝著。我看著墻上的鐘,它還是滴答滴、滴答滴地走著。這一刻,我和她就像是站在時間的兩頭。我正年輕,她卻已經老去,一點點地,老得像一個懵懂的小孩。
那天晚上,我陪她坐在沙發上翻舊相冊,一張又一張地,跟她回憶以前的事情。她睡后,我偷偷打電話訂了機票。這一次,我沒有征求她的意見,也沒有跟肖勇說,但是我打定了主意,我不能再讓她一個人待著,因為來日并不方長,我不想在失去她之后再去后悔我沒有好好孝順她。以后的日子里,也許會有困難,也許會有矛盾,但是一起經歷和承擔,總好過天各一方地隱瞞和思念。
當天晚上我就收拾東西打好了包。第二天,她一萬個不愿意隨我走,怕我忙,怕肖勇不高興。她還想說什么,被我打斷了,我指指地上的包:“快,提著,跟我走!”
長沙的雨停了。飛機舷窗外的天藍得很,老媽靠在椅背上睡著了。
我期待著即將在廣州開始的新日子,我要和她在一起,一起經歷,一起生活,把那些流失的時間一點點地找回來。
(辛普摘自《女報》2012年第1期,張 弘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