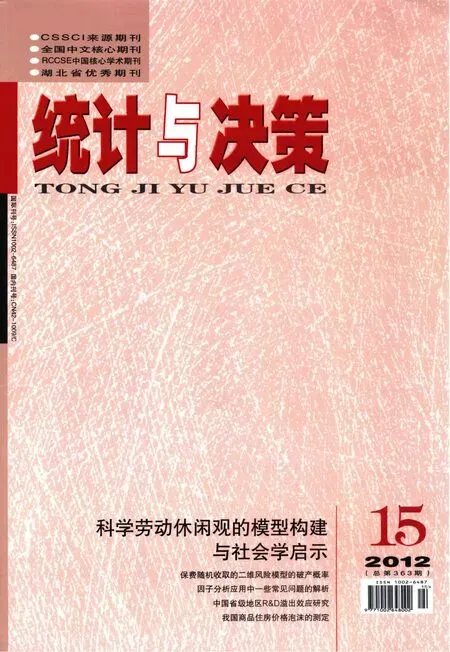我國各地區(qū)FDI吸收能力測度的指標體系
宋 平
1 指標體系建立及SEM模型
1.1 吸收能力測評體系
對吸收的準確理解是:接受并消化,所以僅僅以地區(qū)FDI接受量作為考評指標是不恰當?shù)摹τ谖罩笜梭w系,已有不少理論成果,如尹華(2008)分別建立了接受和消化兩個不同的FDI指標體系,即兩個二級指標。筆者認為這樣做有助于對體系的準確理解,但在實際計算過程中并不需要進行明確分類,只要指標間無顯著相關(guān)性即可以進行結(jié)構(gòu)方程處理。李杏(2007)利用pooldata模型測算了29個地區(qū)的FDI吸收能力與影響因素之間的關(guān)系,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資本、經(jīng)濟開放度、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等。實際上接受與消化的影響因素之間存在一定的交叉關(guān)系,例如經(jīng)濟協(xié)同化水平的高低直接決定了外商投資量的大小,也決定了在接受投資后能否順利將投資轉(zhuǎn)化為實際運作,所以按照接受和消化能力進行體系劃分缺少一定的科學(xué)性。根據(jù)對相關(guān)研究文獻的總結(jié),本文將評價體系分為三個層次,3個二級指標和15個三級指標,并且為了簡潔敘述,按照科技吸收能力、經(jīng)濟及政策支撐能力和基礎(chǔ)設(shè)施支持力將指標確定為15個:區(qū)域人均學(xué)歷層次(K11)、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K12)、試驗及研究經(jīng)費強度(K13)、科研機構(gòu)數(shù)量(K14)、專利發(fā)明量 (K15)、經(jīng)濟協(xié)同度(K21)、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K22)、投資增長速度(K23)、經(jīng)濟增速(K24)、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投資占GDP比重(K31)、公路網(wǎng)密度(公里/萬平方公里)(K32)、第三產(chǎn)業(yè)增加值占GDP比重(K33)、貨物周轉(zhuǎn)量(K34)。高新技術(shù)企業(yè)占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比例(K35)、出口總額占GDP比重(K36),具體如表1。
數(shù)據(jù)來源于2001~2010年間的《中國統(tǒng)計年鑒》《中國高新技術(shù)統(tǒng)計年鑒》及《新中國五十年統(tǒng)計資料匯編》中的31個省、市、自治區(qū)的相關(guān)數(shù)據(jù)。為了使得數(shù)據(jù)分析更接近于統(tǒng)計標準,克服不同指標之間的量綱差異,在進行具體數(shù)量處理時需要進行0-1化無量綱處理,運用(1)式進行處理,在式中j表示樣本對象,kij即代表j地區(qū)在i指標上的數(shù)值:

表1 我國區(qū)域FDI吸收能力評價指標體系

為了驗證上述指標體系的合理性,將原始數(shù)據(jù)代入SPSS13.0進行主成分、因子分析后發(fā)現(xiàn),巴特萊特球體檢驗顯著為零,表示因子分析有效,前3個主成分解釋率為75.4%,說明3個二級指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適合為結(jié)構(gòu)性方程計算做基礎(chǔ)。
1.2 SEM模型
結(jié)構(gòu)型方程顧名思義,即由不同的組成結(jié)構(gòu)構(gòu)成,一組為可觀測的可測變量,另一組為不可直接觀測的潛在變量,一般使用如圖1般的Lisrel結(jié)構(gòu)模型圖進行標示。這樣做的前提是確定兩組變量直接具有一定的邏輯關(guān)系和推導(dǎo)可能性存在。在表2中,主成分列就是考察我國區(qū)域FDI吸收能力的不可觀測變量,而第三列中的三級指標均是可以測量的可測變量。具體包括以下兩個模型。
1.2.1 測量模型
可測變量與潛在變量之間的關(guān)系,可由(2)式可進行表達:

其中,X為外源潛變量向量組;y為內(nèi)生潛在變量向量組;Λx為觀察變量與潛變量(外源)映射矩陣所代表的負荷矩陣;Λy為觀察變量與潛變量(內(nèi)源)映射矩陣所代表的負荷矩陣;ε為內(nèi)源隨機擾動觀測白噪聲;δ為外源隨機擾動觀測白噪聲。η和ξ均為潛變量。
1.2.2 結(jié)構(gòu)模型
潛在變量間關(guān)系,表達為:

其中,B為內(nèi)生潛變量系數(shù)矩陣;Γ是外源(自變量)對內(nèi)生(因變量)的作用系數(shù)矩陣;?為SEM殘差項,反映了η的無解釋構(gòu)成。
2 我國省際FDI吸收能力的估算與檢驗
2.1 SEM參數(shù)估計
本文采用2001~2010年31個省份的310個數(shù)據(jù)進行實證檢驗,軟件選用SPSS Amos 20.0,具體運行結(jié)果如圖1。K1和K2對A的貢獻達到了0.89和0.85,這說明科技吸收能力和經(jīng)濟及政策支撐能力是決定我國FDI吸收能力的關(guān)鍵因素;在K1中K14貢獻系數(shù)比較大達到了0.92,而K33指標僅為0.43,說明當前FDI吸收能力影響因素中科研機構(gòu)數(shù)量有著巨大的作用;而第三產(chǎn)業(yè)比重對吸收外商投資的能力影響不大,說明當前我國第三產(chǎn)業(yè)中現(xiàn)代化服務(wù)進程緩慢,成為FDI流入的障礙。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對FDI吸收能力影響不大,主要是因為當前“孔雀東南飛”的現(xiàn)象仍然比較普遍,全國各地的大多數(shù)具有高學(xué)歷的人才普遍集中在東部發(fā)達地區(qū),即使高學(xué)歷人口增多給中西部地區(qū)帶來的貢獻效應(yīng)也相當有限。經(jīng)濟增速也具有同樣的作用瓶頸,近年來我國中西部地區(qū)經(jīng)濟增速高于東部,但很多地區(qū)特別是西部貧困地區(qū)因此所引入的FDI總量規(guī)模仍偏小,根本原因在于西部地區(qū)經(jīng)濟總量基礎(chǔ)薄弱,即使經(jīng)濟增速較快也難以在短時間內(nèi)快速形成相當大的經(jīng)濟水平以對FDI吸收形成支撐作用。上述只是針對具體數(shù)值作出的簡單分析,實際上可以進行貢獻值排序,以分析哪些因素對特定二級指標具有較強的促進或阻礙作用,當前學(xué)術(shù)界普遍認為SEM能夠替代多重回歸、通徑分析、因子分析、協(xié)方差分析等方法,清晰分析單項指標對總體的作用和單項指標間的相互關(guān)系。

圖1 指標體系SEM模型標準化估計結(jié)果
2.2 結(jié)構(gòu)方程的檢驗
2.2.1 參數(shù)適配度
根據(jù)上述模型SEM估計結(jié)果可以得到15個自變量的方差結(jié)果,如表2所示。

表2 方差檢驗結(jié)果
根據(jù)自變量方差檢驗發(fā)現(xiàn)不存在任何負形式的方差形式出現(xiàn),通過參數(shù)適配度檢驗。同時經(jīng)過標準化的估計可以得到各參數(shù)估計結(jié)果及信度系數(shù)均處于[0,1]之間,說明各項參數(shù)檢驗結(jié)果通過檢驗。

表3 各參數(shù)估計結(jié)果及信度系數(shù)
2.2.2 模型整體適配度檢驗
結(jié)構(gòu)方程輸出結(jié)果的穩(wěn)定性取決于擬合指數(shù)和卡方準則(Hu,Bentler,1998~1999),可以采用SAS軟件進行操作。具體為擬合指數(shù)中:卡方/自由度似然比χ2/df=1.72,系數(shù)優(yōu)度GFI=0.89,調(diào)整后的擬合系數(shù)為AGFI=0.92,并且RMSEA在95%的置信區(qū)間為[0.048,0.077],NNFI=0.89。這些數(shù)據(jù)(見表3)表明SEM方程具有很好的擬合度和穩(wěn)定性。
3 我國東中西部吸收能力的測算與比較分析
根據(jù)上面因子提取及系數(shù)估算后,得到了每個自變量對FDI吸收能力的貢獻系數(shù),并且各總成因子對三個因子貢獻率的方差大小為計算權(quán)重得到了各地區(qū)FDI吸收能力的綜合得分。31個地區(qū)的得分情況如圖2所示。

圖2東中西地區(qū)FDI吸收能力估算結(jié)果
圖2 為各地區(qū)FDI吸收能力評估時間序列走勢圖,結(jié)論如下:一是各地區(qū)的FDI吸收能力整體上均屬于上升通道,東中西各地區(qū)在10年間上升幅度分別為0.068,、0.02、0.01,說明當前外商在華投資的基礎(chǔ)設(shè)施、市場環(huán)境、資源稟賦利用情況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二是地區(qū)吸收能力差異有擴大趨勢,在2001年東部比西部得分分別高0.112、0.172,而到2010年這個差距變?yōu)?.16和0.23。三是從變化趨勢上看中西部地區(qū)的變動趨勢為波動狀,如西部地區(qū)2001年0.28得分變?yōu)?002年的0.265,然后在2003年又升為0.282,而后每年以0.01個百分點進行波動,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地方歷史發(fā)展水平、資源稟賦、地理優(yōu)勢、地方傾斜政策較東部地區(qū)有較大劣勢。由于中西部地區(qū)勞動力素質(zhì)、資源開發(fā)利用效率與發(fā)達國家FDI盡力聯(lián)系程度較低,極大的阻礙了FDI的吸收能力提升,地區(qū)優(yōu)勢產(chǎn)業(yè)所吸收的FDI存在很大的瓶頸制約。這一點體現(xiàn)在中西部地區(qū)FDI在工業(yè)中的分配結(jié)果可以看出,并且由于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相對落后,使得FDI順利發(fā)揮作用的上下級配置不足,制約了FDI的吸收和擴散。這些不足均導(dǎo)致了各地區(qū)經(jīng)濟增速的差距,進而使得可支配收入差距和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并通過基數(shù)乘數(shù)效應(yīng)使中西部落后地區(qū)FDI吸收能力增長能力進一步下降。近年來,我國政府借用的國際金融組織和外國政府貸款,也繼續(xù)向中西部地區(qū)傾斜,重點投向農(nóng)林水、交通、能源、城建環(huán)保、教育、衛(wèi)生等領(lǐng)域,加大對節(jié)能減排領(lǐng)域的支持力度,這將有助解決上述地區(qū)差異現(xiàn)象。
4 結(jié)論
本文通過構(gòu)建結(jié)構(gòu)方程模型對東中西三地區(qū)的FDI吸收能力進行測算,得出以下結(jié)論:一是科技吸收能力和經(jīng)濟及政策支撐能力是決定吸收能力大小的關(guān)鍵因素,這與盧曉勇(2011)的研究結(jié)果相同,科技與政策成為FDI吸收情況的主要決定力量。二是科研機構(gòu)數(shù)量、投資增速和高新技術(shù)企業(yè)占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比例等三級指標對FDI吸收能力有重要作用,而學(xué)歷和可支配收入增速等因素目前成為FDI吸收能力提升的瓶頸。三是東部地區(qū)的吸收能力呈明顯上升趨勢,而中西部呈現(xiàn)出一定的波動狀,并且東部與中西部地區(qū)之間的吸收力差距有拉大趨勢。
[1]傅元海.中國利用FDI質(zhì)量的評價標準研究[J].統(tǒng)計研究,2008,(10).
[2]尹華,劉春光.我國省級地區(qū)FDI吸收能力的綜合評價[J].系統(tǒng)工程,2008,(10).
[3]李杏.外商直接投資技術(shù)外溢吸收能力影響因素研究—基于中國29個地區(qū)面板數(shù)據(jù)分析[J].國際貿(mào)易問題,2007,(12).
[4]盧曉勇,金艷清.國中部地區(qū)FDI吸收能力的因素分析與評價[J].南昌大學(xué)學(xué)報,2011,(6).
[5]楊東偉,胡騰,程琛.中國利用FDI地區(qū)差異因素分析[J].經(jīng)濟研究導(dǎo)刊,2009,(19).
[6]侯杰泰,溫忠麟,成子娟,張雷.結(jié)構(gòu)方程模型及其應(yīng)用[M].北京:教育科學(xué)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