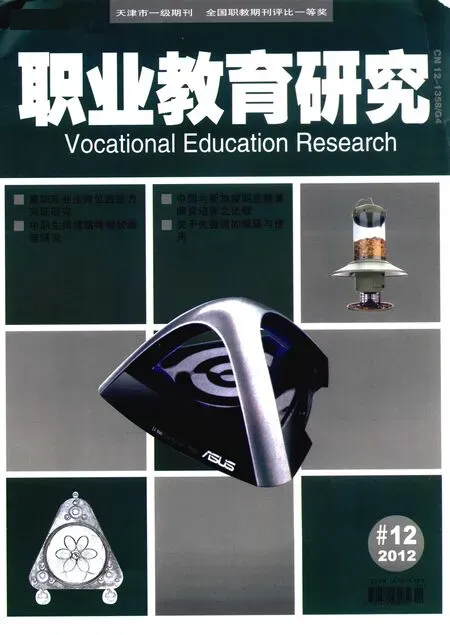高職畢業生崗位勝任力實證研究*
李德方
(江蘇技術師范學院 江蘇 常州213001)
研究目的與意義
1973年,美國學者麥克萊蘭(David Mcclelland)發表了《測量勝任力而非智力》一文。該文首先提出了“勝任力”的概念,認為勝任力是區分績效出眾者和績效平平者差異的最顯著特征,是決定工作績效持久的品質和特征,并指出了智力和能力傾向測驗的缺點,主張用勝任力特征測試代替智力和能力傾向測驗。此后的幾十年間,麥氏的理論被廣泛運用于管理學、教育學等領域。作為培養面向生產、建設、管理與服務一線高技能人才的高職院校,每年為社會輸送大量的畢業生。以2010年為例,該年度全國高職(含專科)院校共畢業學生316萬人,占高校畢業生總數的54.96%。①從某種程度上講,高職培養的人才質量既關乎中國當下及未來的人力資源狀況,又影響“中國制造”乃至“中國創造”的質量與美譽度。
崗位勝任力可用來區分具體崗位上能完成崗位任務目標的優秀人員的綜合要素。不同的崗位具有不一樣的崗位勝任力要素。這些要素既有外顯的成分,又有隱藏在表象背后的深層次特征,包括動機、價值觀、思維方式等。崗位勝任力不僅表現為特定崗位任職資格的基本要求,而且包含員工在崗位上表現卓越的充分條件。通常認為,崗位勝任力要素有三個基本特征:一是與工作績效的緊密關聯性;二是能夠區分在特定崗位上表現優異者與普通者;三是與具體的崗位特征與任務情境相聯系,具有動態性。高職院校高端技能型專門人才的培養目標定位決定了其畢業生既有區別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的素質要求,也有不同于普通高校畢業生的知識能力。簡而言之,其實踐知識應比普通本科院校畢業生強、專業理論與智慧技能應比中職畢業生好。不僅如此,其工作崗位的“承上”——將基于原理的設計轉化為具體的工程或技術方案、與“啟下”——通常直接從事(高端)技能操作工作或者與(高端)技能操作工作緊密相關——決定了傳統的重在考察智力水平的學業成績往往不具有針對性與科學性,而測量并研究高職院校畢業生的崗位勝任力,則可以更為準確直觀地反映其培養人才的質量,真正體現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的職業教育辦學方向。
高職院校畢業生崗位勝任力要素指標的確定
國內外勝任力要素指標的界定方法通常有關鍵事件訪談法、職能分析法、外部標桿法等。所謂關鍵事件訪談法,就是采用開放式的行為回顧式調查技術,通過對績優員工和一般員工的深度訪談,提取績優員工具有而績效一般員工沒有或較弱的行為特征;職能分析法更主要關注最低限度可以接受的績效。它關注實際的工作產出,焦點在工作而不是工作中的個人,通過基于分析的過程,識別出一個職能或工作所要求的產出能力;外部標桿法,顧名思義就是借鑒國內外同類“標桿企業”的成熟經驗,分析他們的優秀員工身上具備的獨特素質,并結合自身的情況來確定指標。以上幾種方法各具特色,由此構建的不同范疇、不同領域勝任力要素指標迄今業已具有較為豐富的內涵。有鑒于此,筆者在文獻研究的基礎上,采用德爾菲法嘗試確定高職院校畢業生崗位勝任力要素指標。考慮到高職院校畢業生就業崗位面向的廣泛性,難以用某一特定崗位勝任力來涵蓋整體,因而,本研究著重考察高職院校畢業生通用的崗位勝任力素質要求。具體的方法步驟是:首先,以Hay/McBer公司1996年版《分級素質詞典》(通用素質部分)為藍本,結合國內不同企業崗位勝任力模型,初步提煉并擬定高職院校畢業生崗位勝任力要素指標。然后,組織相關專家,就初步的崗位勝任力要素指標進行討論,并根據心理學家米勒的“7±2”原則,最終確定8項崗位勝任力要素指標,具體結果見表1。

表1 高職院校畢業生崗位勝任力要素指標表
高職院校畢業生崗位勝任力實證研究
(一)研究概要
對畢業生崗位勝任情況最具發言權的是錄用畢業生的用人單位,有鑒于此,筆者采用問卷調查的方法,針對高職院校畢業生崗位勝任力各項要素指標,由用人單位根據畢業生在工作崗位的實際表現,采用“好”、“較好”、“一般”、“較差”、“差”五級區分進行評定。由于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區域間高等職業教育既有相似性、更有差異性。不僅如此,高職院校本身也具有多樣性——既有三年制高職,又有初中后五年一貫制高職;既有隸屬于教育部門的職業技術學院,也有隸屬勞動人事部門的技師學院(高級技工學校)。考慮到研究的便利性和樣本的代表性,本研究選擇江蘇省內不同類型高職院校的2008、2011屆畢業生為樣本對象。這些高職院校包括23所三年制高職(包括普高后三年制和中職對口單招三年制)、11所初中后五年一貫制高職和6所隸屬勞動人事部門的技師學院。問卷調查的對象為上述樣本對象所在的300余家企事業單位,其中,大型企業93家、中型企業154家、小型企業83家、未注明單位類型的22家。共發放問卷500份,回收353份,回收率70.6%。調查時間為2011年10~12月。調查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高職院校畢業生崗位勝任力情況表
考慮到構成畢業生崗位勝任力的各項要素指標所起的作用不同,有必要依據其重要性給予相應的權重分配和賦值。不難推斷,對高職院校畢業生而言,表征其知識、能力和態度的“專業知識水平”、“操作技能”、“崗位適應性”以及“工作態度”等四項指標相對來說更為關鍵,所以分別予以15%的權重,其余的要素指標(后四項)予以10%的權重。為了方便考察并直觀比較,將每一項要素指標的評價百分率換算成相應的分值。具體的方法是,將評價等級“好”、“較好”、“一般”、“較差”、“差”分別按照100%、85%、70%、30%和-n%的比例折算。此處的“-n”中的n是指評價為“差”的對應百分率。比如,某項指標有5%的調查對象評價為“差”,那么在此項指標的分值上要相應減去5分。由此測算的各類高職院校畢業生崗位勝任力要素指標分值如表3所示。

表3 高職院校畢業生崗位勝任力要素指標分值表
將各要素指標分值進行加權統計后,可以計算出樣本地區高職院校畢業生崗位勝任力,見表4。

表4 高職院校畢業生崗位勝任力要素指標加權統計表
(二)結果與討論
從研究結果來看,樣本地區高職院校畢業生崗位勝任力平均分值為80.66(滿分100),即總體達到了良好水平。比較各類高職院校的情況,可以發現四類學校基本平衡并各有千秋。其中,普高后三年制高職和初中后五年一貫制得分相對略高,這主要是得益于這兩類學校學生在學習和工作態度方面較之其他學校略勝一籌。從樣本地區的實際來看,學生第一次分流發生在初中畢業后,一般成績較好的學生選擇就讀普通高中,反之則就讀中等職業學校。因此,不難看出,普高后三年制高職的學生實際上是初次分流的勝出者。這些學生學習習慣相對較好,學習方法與學習能力等也比較出眾,可以認為他們將自身的這些優勢也遷移到了高職院校的專業理論學習中,因而這方面效果比較明顯。初中后五年一貫制高職則有著初、高等職業教育無縫對接的學制優勢。如前所述,這些學生也經歷了如其他一般初中畢業生那樣的初次分流,但其生源構成并不像就讀普通高中和中等職業學校的學生那樣 “涇渭分明”——學習成績好的進了普通高中,反之則進入職業學校,通常大部分學生介于兩者之間,其中,也不乏成績優秀的學生出于其自身或家庭的某種考慮(比如穩定性)而選擇就讀五年一貫制高職。這些學生入學后先接受中等職業教育,然后,直接跨入高等職業教育的大門,或者說此類學校實施的中、高等職業教育之間本身并沒有布迪厄所言明的那種“區隔”,因而也就沒有通常在不同類型教育以及同一類型不同層次教育之間過渡所帶來的 “損耗”。這種“長學制”的制度安排,比較有利于從源頭科學設計人才培養方案,進而可以有效提高人才培養的效率。
從各單項要素指標來看,比較突出的單項要素指標有“操作技能”、“崗位適應性”和“工作態度”,四類學校均在良好以上。這反映了樣本地區高職院校都能緊緊把握高等職業教育的規律特點,有針對性地培養既懂一定理論、又有實踐技能的高端技能型專門人才,同時比較注重學生的職業道德教育,并取得了實效。普遍薄弱的要素指標是“自主創新能力”,得分均在7分左右(滿分10分)。這表明加強自主創新能力的培養,不僅是我國普通高校的當務之急與重中之重,也是高職院校固本強身之舉。前者如果是重點關注學生原始創新能力的培養,后者則應主要著力于集成創新能力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塑造,兩方面都十分重要,不宜厚此薄彼。
綜上,用實證的方法可以得出高職院校畢業生的崗位勝任力。這個結果不像100分試卷考出80分那樣具有確定性與絕對性。也就是說,即使對同樣的調查對象,不同的方案設計與權重賦值所得出的結果也不一定相同。因此,從這個角度講,本研究的結果具有相對性。此外,本研究是針對畢業生群體的測試,不難推斷,也可以采用本研究的方法與步驟測量畢業生個體的崗位勝任力,從而能夠真正體察學生適應社會崗位需求的素質和能力,更為直觀地衡量高職院校人才培養的質量和水平。
注釋:
①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教育統計數據》“2010年教育統計數據”中的數據計算得出。具體數據出處為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6200/index.html
[1]王懿,王中強,王振維.重點學科創新型人才勝任力探析[J].重慶醫學,2008(11):2616.
[2]高永惠,郭潤寒,梁芳美.崗位勝任力是提高大學生成功就業的關鍵因素實證探討[J].中國市場,2012(13):97.
[3]張力.崗位勝任力模型在人才管理中的運用[J].企業導報,2011(5):208.
[4]張軍.如何評估與發展員工的崗位勝任力[J].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09(5):45.
[5]馮明,尹明鑫.勝任力模型構建方法綜述[J].科技管理研究,2007(9):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