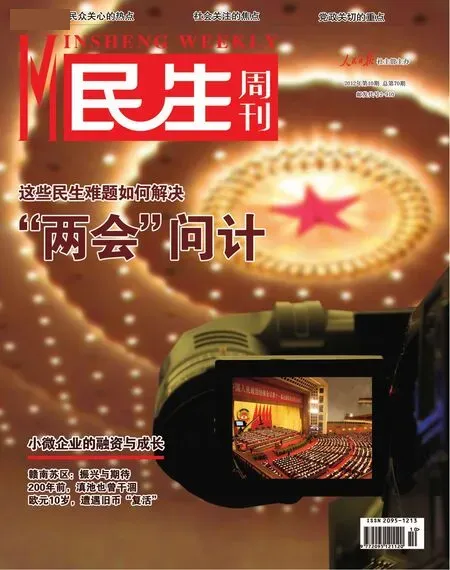治污考驗的是全社會
□ 高波濤
治污考驗的是全社會
□ 高波濤

1月31日,閩江古田縣水口鎮灣口村段,一村民看著被水葫蘆侵蝕的江水,滿臉惆悵。圖/CFP
近年來,水污染事件屢現報端,隨著一系列水污染事件的發生,我國水資源經受嚴重考驗。而在一系列污染中,工業污染正成為水污染之禍的不可承受之重。
斬不斷的水事故
2010年7月,紫金礦業發生9100立方米污水滲漏事件,引發汀江流域污染,導致永定縣境內的棉花灘庫區出現大面積死魚。2011年6月,廣東德英高嶺土場非法排放工業污水事件,造成附近村莊逾萬斤塘魚暴斃,威脅湛江數百萬人的飲用水安全。2011年8月,云南曲靖陸良化工工業廢料鉻渣非法傾倒,致附近農村77頭牲畜死亡。2012年1月,廣西龍江河突發嚴重鎘污染,水中的鎘含量約20噸,污染波及河段達300公里,引發當地居民飲用水安全危機。
我國500多條主要河流中,80%不同程度的污染源自工業廢水,而地方政府稅收的一半以上要依靠這些企業。
紫金礦業是國內最大的黃金生產企業,有中國第一大金礦之稱,位列全球500強。2010年發生事故的福建龍巖市上杭縣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紫金山銅礦,是紫金礦業的核心企業。
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上杭縣的財政收入還排在龍巖地區最后一位。2002年以來,隨著紫金礦業的迅速發展,上杭已經成為僅次于龍巖市區的經濟最發達地區。更有統計稱,紫金礦業對上杭的稅收在早些年前就已過半。
而對于龍年伊始發生在廣西龍江河鎘污染事件,源頭則來自河池市的兩家有色金屬企業。據廣西河池市發改委主任廖錦成介紹,河池市有色金屬企業規模以上的達72家,規模較小的有82家,僅去年河池市有色金屬產業值就達到168億元人民幣。有色金屬是河池市六大支柱產業之一,每年占河池財政收入的12%左右。河池的礦產資源優勢一直以來都支持這個產業發展。
顯然,這些發生事故的企業在當地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經濟上的利益。如果這些企業利益取之有道,本無可厚非,但現實卻大相徑庭。
2006年底,位于貴州省貞豐縣境內的紫金礦業貞豐水銀洞金礦發生潰壩事故,尾礦庫中約20萬立方米含有劇毒氰化鉀等成分的廢渣廢水溢出,下游兩座水庫受到污染。2007年,紫金礦業收購湖北鑫豐礦業。由于工藝的改變,含有大量殘余水分的尾礦渣成為污染隱患。2009年4月底,紫金礦業下屬的、位于河北張家口崇禮縣的東坪舊礦尾礦庫回水系統發生泄漏事故,引起部分當地居民呼吁堅決取締。
在河池市,2001年6月,河池大環江河上游遭遇暴雨,30多家選礦企業的尾礦庫被沖垮,歷年沉積的廢礦渣隨洪水淹沒兩岸,萬畝良田盡毀。2008年10月,河池市金城江區東江鎮一家冶煉企業含砷廢水外溢污染,450多人尿砷超標。2011年8月,河池市南丹縣30多名兒童患發高鉛血癥。
監管之難
屢屢發生的水污染事故,為何遲遲得不到有效治理?
身兼重點流域和近岸海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指導組組長的夏青認為,中國的問題在于“小工廠多,不規矩的多”,這應該是污染事故頻發的緣由之一。
因發布“中國水污染地圖”而被業界熟知的環保NGO組織公眾環境研究中心馬軍表示,在中國的工業結構中,重化工等重污染行業所占比重很高,總量增長很快,管理又不到位,造成了污染高發的趨勢。
早年的紫金礦業在削平紫金山山頭、采取露天開采時,就備受詬議。雖然后來紫金礦業副總裁劉榮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大爆破經過了論證,有相關手續,取得了有權部門的許可”,但很多人還是認為,與當地官員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紫金礦業,通過論證、取得許可并不是什么難事,甚至在發生事故后有人為其瞞報、遲報。
就在紫金礦業發生水污染事故的前3個月之內,當地環保局設在紫金山下的自動監測站竟然“設備損壞”,未能提供任何數據,而這次事故也是9天以后,地方政府才對外公布的。
同樣,遲到的發布在廣西龍江河鎘污染中被效仿。
事件發生后的第16天,當地官方才宣布,涉案企業是廣西金河礦業股份有限公司和金城江鴻泉立德粉廠,涉嫌違法排污的7名相關責任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河池市市長何辛幸正式向社會公眾道歉。
慶幸的是,何辛幸表示,政府監管有缺位的地方,包括履行職責上有很多不到位。另一方面,企業社會責任也有缺失,對企業不按照國家法律法規規定違法排污、超標排放,甚至偷排,要有一起查處一起,更要嚴肅地處理。
在追求GDP增長的目標驅動之下,在缺乏環境質量考核的政府追責之下,跨區域的環境和資源往往成為“公地悲劇”的產物。
據相關人士透漏,相比較大價錢的排污設備和小力度的處罰金,很多企業還是很樂意交納處罰金的。廣西河池市金城江區環保局紀檢組組長藍群峰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感嘆“很委屈”。企業之多、人手之少、監管之難,成為委屈的原因。
“網”治全國水污企業
屢屢發生的水污染事故,大多影響的是下游居民,尤其是那些漁民,而這些賴“水”為生的群體又面臨著怎樣的出路呢?紫金礦業水污染事故后,有媒體曝出,很多漁民不僅沒有得到死魚補償,而且面臨轉產困境。
事故發生后,紫金礦業委托政府以6元/斤的價格收購補償,而網箱部分則按40元/平方米補償。然而,眾多漁民抱怨,補償款還不足飼料成本。
在轉產扶持政策上,上杭縣規定每戶新植水果或茶葉達到一定規格以上,由財政給予苗木補助,用于果園道路和灌溉等基礎設施建設。得到的卻是村民更大的抱怨:山都是生態山,無山可種,轉產費也沒有。
而在廣西龍江河水污染事件中,上游河池市的企業導致下游柳州市居民飲水出現問題,也顯露水污染的跨界執法應引起重視。
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杜群表示,就國內法而言,跨界環境污染主要是指跨越行政區域(省、市、縣等)的環境污染。我國跨界污染的法律控制仍然不力,糾紛時有發生。分析其法律原因,主要問題不在立法,而在于對現有法律的執行不力。
一方面,就地環境保護執法本身存在嚴重不足。我國環境保護法已經提供了一系列環境管制措施,如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三同時”制度、排污濃度控制和總量控制、排污治理義務、排污登記和自覺監測義務等,但企業不環評就進行建設生產和排放,污染物未經處理就排入江河、大氣的情況屢屢不絕。因此,工業點污染源的就地控制不嚴,是跨界污染發生的首要原因。
另一方面,跨區域環境保護聯合執法不夠。在追求GDP增長的目標驅動之下,在缺乏環境質量考核的政府追責之下,跨區域的環境和資源往往成為“公地悲劇”的產物。環境違法企業往往在跨行政區域地帶與執法人員玩起時間差、游擊戰,致使環境違法行為屢查不止。交界處污染企業管理歸屬問題一直是跨行政區域環保部門頭疼的對象。
而隨著每次水污染事故的平息,地方政府在緊張一時之后恐怕又會放松警惕。地方性的治理遠比不了全國范圍內的整治,就像馬軍繪制的“中國水污染地圖”,如何將水污染企業控制在一個有效的“網”中,恐怕還需要在更大的范圍、以更有效的機制來長期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