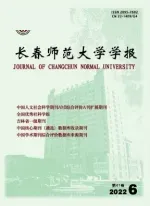論漢語中表致使義的復合使動和結果補語結構
劉長珍,張 燕,2
(1.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外語教育研究中心,北京100089;2.中國石油大學,北京100089)
論漢語中表致使義的復合使動和結果補語結構
劉長珍1,張 燕1,2
(1.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外語教育研究中心,北京100089;2.中國石油大學,北京100089)
以往對復合使動和結果補語結構的研究多從語義或句法角度進行,沒有深入到事件結構內部。通過對這兩個結構中謂詞V1、V2與它們前后名詞短語NP1和NP2的關系的探討,發現這兩個結構具有相同的底層結構,并據此從事件結構內部的句法投射角度,以最簡方案框架下的動詞殼為基礎提出新的解釋途徑。以介詞“使”為中心語的介詞短語PP連接了致力事件和結果事件,更好地展現了致使事件內部的關系。
復合使動;結果補語結構;事件結構;動詞殼;PP
“致使”可以理解為一個行為動作導致某種結果或狀態的出現。語言學界對于“致使”結構的研究是廣泛而深入的,但總的來說可以從以下三點進行歸納:從詞匯語義角度來說,“致使”結構包含兩個語義因素——“致使”(CAUSE) 和“狀態”(BECOME)[1],這一結構的詞匯語義結構可表示為(1):
(1) [[xDO]CAUSE[x/yBECOME STATE]]
從論元角度來說,一個致使結構至少包含兩個論元——致使者(Causer)和被致者(Causee),二者由動詞連接起來。從事件結構角度來說,致使結構表示事件的轉變,包含致力事件和結果事件,并且前一事件導致后一事件的出現,前為因、后為果。這三種角度從不同側面表達了致使結構的內在特征,即某一行為產生了某種結果。
漢語中的致使意義由不同的致使結構來表達。本文以復合使動和結果補語結構為例來分析漢語致使意義是如何通過事件結構和句法結構之間的相互作用來表現的。
一、復合使動及結果補語的基本句式和以往的研究
復合使動結構是指由兩個謂詞復合共同表示致使意義,也即動結結構,其表現形式可統一概括為NP1+V1-V2+NP2,V1-V2由這一結構中兩個事件的謂詞V1和V2復合而成。結果補語結構是指由動詞和“得”之后帶結果補語的一種致使句式,其表現形式可概括為NP1+V1+de+V2,V1和V2分別為這一結構中兩個事件的謂詞。二者既有共同點又有不同點:共同點是都包含兩個謂詞,活動/原因謂詞V1和結果/狀態謂詞V2;不同點是結果補語結構含有明顯的標志詞“得”而復合使動結構中卻沒有,從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
(2) a.結果補語結構 b.復合使動結構
張三哭-v1得手絹都濕-v2了。 張三哭-v1濕-v2了手絹。
結果補語結構a中,V1哭后有“得”引出結果V2“濕”;而復合使動結構b中,V1“哭”與V2“濕”之間無任何可見成分,但二者都可表示“張三哭”這一致力事件引起“手絹濕了”這一結果事件。
對上述這兩種不同的致使結構表示同一致使事件的現象,語言學家有過多種不同的解釋。下面介紹一下黃正德和鄧思穎對這一現象的分析與論證。
(一)黃正德的分析論證[2]
黃正德從句法角度入手,認為結果補語和復合使動結構在句法上以同樣的方式衍生而來,如例(3)的a句和b句由圖①a和①b所示:
(3) a.結果補語結構 b.復合使動結構
張三哭-v1得手絹都濕-v2了。 張三哭-v1濕-v2了手絹。

圖①a

圖①b
黃正德以被動句和把字句為論據支持這一分析方案。他認為,NP2“手絹”可以成為被動句的主語和把字句中“把”的賓語,如(4a-b) 和(5a-b) 所示:
(4) 結果補語結構 (5) 復合使動結構
a.手絹被張三哭-v1得都濕-v2了。 a.手絹都被張三哭-v1濕-v2了。
b.張三把手絹哭-v1得都濕-v2了。 b.張三把手絹都哭-v1濕-v2了。
(4) (5) 例中的句子意思是相同的。黃正德指出,在這兩種句式中,NP2(e.g.手絹) 和句子的其它部分存在緊密一致的語義關系。盡管它不是行為動詞V1的賓語,卻可以看作“動詞-結果”(含“V1-得”結構和“V1-V2”復合使動結構)組合的賓語。所以,在句法操作中,發生動詞移位的是整個“動詞-結果”組合而不是單個動詞。
黃正德的這一分析也不是沒有問題的。由于在此種分析中“動詞-結果”組合(i.e.V1-得和V1-V2復合詞)都是及物動詞,這使得及物動詞和不及物動詞的界限變得模糊,也忽略了“得”作為顯性結果標志詞的語法地位。
(二)鄧思穎的分析論證[3]
鄧思穎認為動詞復合和結果補語結構是從同一底層結構變化而來,這一結構如圖②所示。
從圖②可以看出,鄧思穎認為結果補語和復合使動結構共有的底層結構中存在一個功能語類F作為致力事件和結果事件的連接點。在這一假設中,結果補語和復合使動結構中都含有一個vP殼和功能短語投射(FP)。句子主語NP1在Spec-vP位置生成,及物動詞賓語位于以V1為中心語的Spec-VP位置。V1選擇功能語類F的最大投射為補語,F又以結果事件XP為補語,其中,XP的中心語是結果謂詞V2且在Spec-XP處為空代詞pro或PRO占據。在結果補語結構中,F由詞素“得”所占據,由于“得”的詞綴性,它必須要移位,與動作動詞V1構成“V-得”復合結構;隨后,“V-得”復合結構又移至最高位置的vP的中心語處,從而生成了結果補語結構,如(6)所示:

圖②

圖③
(6) 結果補語結構
[vP張三j[v'哭得[VP[V’[vP張三j[v’哭得[VP[V’tv1-tde[FP[F’tde[XPpro/PROi[X’手絹都濕了]]]]]]]]。
(7) 復合使動結構:張三NP1哭-v1濕-v2了手絹NP2。
在復合使動結構(7)中,F在表層結構無詞匯形式。如圖③所示,由于F具有強體特征,它吸引結果謂詞V2上移核查它的強特征;接著由于形態原因,V2又從FP的中心語位置移至V1處,形成復合結構V1-V2;這一復合詞最終移到上層vP的中心語位置,形成復合使動結構。在這一推導過程中,NP1在Spec-vP位置,而NP2在Spec-VP位置。
鄧提出的功能語類FP雖然體現了“得”的語法地位,但是在整個結構中沒有能夠清晰地表現出致使結構的致力事件和結果事件的內在聯系,忽略了致使這個根本義素,因此也是存在一定問題的。
二、從事件結構的句法映射角度對復合使動和結果結構的再分析
既然復合使動和結果補語結構都表達致使意義,那么它們的語義內容無疑是復雜事件,理應具有復雜事件普遍具有的內部結構。同時,作為復雜事件內部結構的子事件——致力事件和結果事件,也理應在句法上映射出來。這一部分將通過分析,找出復合使動和結果補語結構的兩個子事件——致力事件和結果事件,及其底層的語義及形式關系。在此基礎上,通過事件結構的句法映射重新分析復合使動和結果補語結構。
(一)事件謂詞V1、V2與它們前后NP1和NP2的關系
如前文所述,我們把復合使動和結果補語結構分別形式化為NP1+V1-V2+NP2和NP1+V1-得+NP2+V2。宛新政把含有V1-V2這一動補結構的句式稱為使成式,而使成句即本文中的復合使動結構。[4]宛書中指出,V1-V2中,V1是一種動作行為,表原因;V2是這一動作行為導致的結果。V1-V2的構成可以是“動詞+形容詞”或者“動詞+動詞”,V1和V2都有及物和不及物之分。當V1在語義上與NP1相關時,NP1多為V1的施事,二者有主謂關系,而V2多為形容詞或不及物動詞,且和NP2構成主謂關系,如例(8a)所示;當V1語義上指向NP2時,NP2多為V1的施事,二者有主謂關系,同時,V2多為形容詞或不及物動詞,且和NP2構成主謂關系以說明NP2的狀態或結果,而此時NP1多具有[-人]的特征,如例(9a) 所示;結果補語結構中V1、V2與NP1、NP2有類似的關系,如(8b) (9b) 所示:
(8) a.張三NP1哭-v1濕-v2了手絹NP2。 (9) a.酒NP1喝-v1醉-v2了老王NP2。
b.張三NP1哭-v1得手絹NP2濕-V2了。 b.酒NP1喝-v1得老王NP2醉-v2了。
在(8)中,NP1和V1是主謂關系,形成致力事件“張三哭”,而由于V2是不及物動詞,理應與NP2構成主謂關系,即“手絹濕了”,表明致力事件所導致的結果。在(9)中,V1這一動作是NP2發出的,二者是主謂關系“老王喝酒”,同樣,V2是不及物動詞,也是來說明NP2的,二者在深層存在主謂關系——“老王醉了”。用箭頭表示語義中內含的致使義,則這兩個事件的底層關系可表示為(8’)和(9’):
(8’) 張三哭→手絹濕了 (9’) 老王喝酒→老王醉了
兩個事件謂詞與兩個名詞短語的關系,清楚地表示出了致使結構的兩個子事件及其關系,即含動作動詞的致力事件引起了含結果動詞的結果事件;并且,在底層結構中,“→”表示[+致使]特征。
(二) [+致使]特征在底層結構中的詞匯實現形式及其詞類的界定
例 (8’)、(9’) 中的事件結構關系可與 (8”)、(9”) 中的句子互換:
(8”) 張三哭(使) 手絹濕了。 (9”) 老王喝酒(使) 老王醉了。
通過上述互換,(8”)、(9”)中的句子已變成了一種新句式——使字句(漢語中最典型的致使句);并且,這些句子與(8’)、(9’)同義,所以說,“使”與[+致使]具有同等功能,即把致使結構兩個子事件清晰地表達出來。
語言學者對使字句的標志“使”的詞類有很大爭議,但大都同意“使”在使字句中為介詞,因為它具有介詞的諸多句法特征,如“句法位置固定,只出現在某些詞的前面,起介引作用;句法上沒有獨立性;不能用肯定否定的方式提問,也不能獨立回答;沒有‘體’的標記,不能重疊,不能帶動態助詞”[4]。
(三)以介詞“使”為中心語的PP假設
復合使動和結果補語結構都表示一個復雜的致使事件,在這個事件中至少有兩個子事件——致力事件和結果事件,這兩個子事件通過[+致使]強特征連接起來。通過對事件謂詞V1、V2與它們前后NP1和NP2的關系的分析,可以看出這一復雜致使事件的底層結構實際是漢語中典型的致使結構——使字句,并且,使字句的標志“使”在語類上為介詞。因此我們可以假設,復合使動和結果補語結構是由相同的底層結構“使字句”通過某種句法操作而形成的新的致使結構。這一底層結構可表示為圖④。
在圖④這一結構中,動作動詞V1是低層VP的中心語,結果動詞V2是結果事件的最大投射RP的中心語。上層vP和底層的RP分別代表復雜致使事件的兩個子事件——致力事件和結果事件。上層vP的中心語v為輕動詞。此處我們沿用最簡方案中vP殼的設計,即vP殼中的輕動詞v并不是一個詞匯語類(lexical category),而是一個無語音形式的語綴(affix),呈強語素特征。因此,它要觸發下層VP中的動詞V進行移位且并入v來核查自身的特征。在VP與RP之間為PP,即以介詞“使”為中心語的最大投射,它連接著上層的致力事件和下層的結果事件。實際上,P的位置也允許語音及詞匯形式的隱含,并且可以有補語標志“得”與之復合。復合使動和結果補語結構都是P語音隱含的例證。Spec-PP位置為致力事件的虛設位置,因為vP所代表的事件為致力事件;中心語P(即“使”)是一個介詞,因此它具有介詞的強特征;“使”在語義上本身有“致使”義,因此在詞匯層面它又帶有[+致使]特征,即“使”的特征可表述為[P,+Cause],在圖中表現為P下分支含P及結果補語的標志詞de。二者都可以是隱含特征。RP中Spec-RP位置為NP2,中心語R位置為V2。
我們假設復合使動和結果補語結構有相同的底層結構,如圖④所示。下面將分別論證它們是如何衍生成表層結構的。

圖④
1.復合使動結構的推導
以圖④為基礎,復合使動結構的推導以“張三哭濕了手絹”為例,如圖⑤所示。
如上文所述,NP1、NP2底層結構中就分別在Spec-RP位置生成。復合使動結構中P無語音詞匯形式,也沒有補語標志詞“得”存在,只有[P,+Cause]特征,因此,它要吸引底層的動詞V2上移,與之合并來核查自身的特征。由于v[+Cause,+Become]的強語素特征,它除了要吸引V1上移之外,還要使V2繼續上移,直至特征核查結束,從而形成了復合使動結構的表層形式。在“張三哭濕了手絹”中,“濕”先移至P位置,以滿足特征核查;然后又移至V1“哭”位置,二者一起移向v位置,在完成v的特征核查的同時,完成了動作謂詞和結果謂詞的結合,形成了復合使動結構。

圖⑤

圖⑥
2.結果補語結構的推導
以圖④為基礎,結果補語結構的推導以“張三哭得手絹濕了”為例,如圖⑥所示。
結果補語從句中含有補語標志詞“得”,因此,V2不必發生移位;而“得”則需要繼續上移,先移至V1位置,之后與V1一起移至v位置,完成特征核查,從而形成V-de式的結果補語結構,實現了底層與表層結構的轉化。在“張三哭得手絹濕了”這句話的推導過程中,首先是“得”移至V1“哭”位置,然后二者受v強特征的吸引,一起上移至v位置,完成了底層結構向表層結構的轉化。
三、結語
通過探討復合使動和結果補語結構中NP1、NP2、V1和V2的關系,我們可以發現這兩種結構有著共同的底層結構,即都是包含兩個子事件的使字形的致使結構。本文在vP Shell基礎上,增添了以P為中心語的PP短語,以此來連接致力事件和結果事件。這一解決方案能更清晰地表示致使事件的內部因果關系,具有一定的實用性。當然,由于對整個致使結構分析尚不充分,復合使動和結果補語結構以及其它類似結構有待進一步探索。
[1]Hale,K.&S.J.Keyser.On argument structure and the lexical expression ofsyntactic relations[C]∥In Hale,K.&S.J.Keyser(eds).The ViewfromBuilding20:Essays in Linguistics in Honour ofSylvain Bromberger.Massuchusetts:The MITPress,1993.
[2]Huang,C.T.James.Complexpredicates in control[C]∥In R.K.Larson et al(eds.).Control and Grammar.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2:109-147.
[3]Tang,S.-W.The parametric approach to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and English[C]∥In L.C.-S.Liu and K.Takeda(eds),UCI WorkingPapers in Linguistics,Vol.3.Irvine Linguistics Students Association,1997:203-226.
[4]宛新政.現代漢語致使句研究[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77-78,98-101.
On Compound Causatives and Resultatives in Chinese
LIUChang-zhen1,ZHANGYan1,2
(1.NationalResearchCentreforForeignLanguageEducation,BeijingForeignStudiesUniversity,Beijing100089,China;2.China UniversityofPetroleum,Beijing100089,China)
The former discussions about compound causatives and resultatives used to take the semantic or syntactic perspectives,and the event structures ofthe constructions were not discussed.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ctivity predicate V1,the result predicate V2 and the noun phrases NP1,NP2.Their relationships showthat compound causatives and resultatives share the same underlying structure.Based on this underlying structure,this paper makes the proposal that there exists a PP headed by the preposition “shi”in the deep structure of compound causatives and resultatives,which connects the causing event with the result event.This proposal is based on the vP-shell structure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Minimalist Program and it can exhibit the inner relationships of the Causativityclearly.
compound causatives;resultatives;event structure;vP-shell;PP
H043
A
1008-178X(2012)01-0070-05
2011-11-20
劉長珍(1982-),女,山東臨沂人,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外語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從事句法學、社會語言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