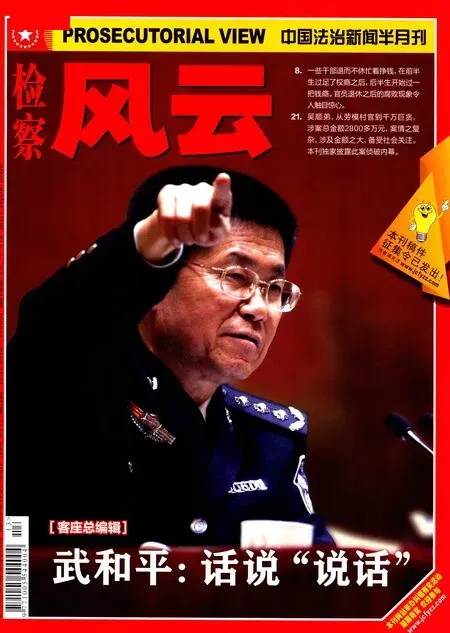標本兼治,健全法規防治腐敗期權化間接化
文/韓小鷹(海歸學者)
標本兼治,健全法規防治腐敗期權化間接化
文/韓小鷹(海歸學者)
在這個題目下,筆者主要探討解決三個問題 :我們對干部退休后的腐敗行為、干部離職后(離職經商或離職從事其他職業)的腐敗行為,以及借手他人的腐敗行為, 到底應該如何應對 ?
先說退休干部。腐敗干部在職時,利用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但并不立即收受財物,而是等離職后再收受此前約定的報酬,此舉變權力尋租“現貨”為“期權”,非常隱蔽。一般來說,非舉報人舉報,很難查實。那么,如何從法律上 ——由于我國目前的國情,不從法律上規范,則其他規范都是 “軟法”,都不能有實質上的效果 ——防治退休干部在任職時的腐敗行為 ?
從刑法上看,我國的《刑法修正案》立法中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干部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約定在其退休或離職后收受請托人財物,并在退休或離職后收受的,應該以受賄論處。
2007年6月,中央紀委制定了《中共中央紀委關于嚴格禁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若干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也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規定此類行為以受賄論處。
《意見》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離職前后連續收受請托人財物的,離職前后收受部分均應計入受賄數額。
再看退休干部的另一種腐敗行為。有的干部在職時,利用手中的權力關照相關企業、學會、協會、基金會,退休以后到這些地方任職,領取高額工資、“咨詢費”等,這實際上是一種權錢交易。
有的干部到這些地方任職后,利用自己過去擔任領導干部的影響力,特別是通過自己提攜、培養的擔任領導職務的老部下,為這些地方謀取好處,從而自己得到高額回報,這也是一種權錢交易。
國際上,部分國家也針對這個領域可能產生腐敗的問題作過一些規定,比如法國,1994年修訂的法國《刑法》就規定,官員退休五年內,不允許以任何形式、從事任何與他任職期間相關的商事活動。在其死亡前,任何相關腐敗行為都會受到與其任職時同樣的刑法追究。類似案例舉不勝舉。
針對退休干部的腐敗行為,筆者認為需要做的關鍵是完善相關制度,主要應包括4個方面 :1. 明確規定任職條件。哪些企業、學會、協會、基金會是不允許退休干部任職的、退休后多長時間才可以去任職、具備哪些任職回避條件,等。2. 明確監督機構和人員。3. 明確處置規則,包括法律責任,等。4. 司法判例,尤其是非法數額大的判例。 類似政協十一屆全國委員會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原副主任李元、原中國國土資源報社社長劉允洲(案發時已退休)這樣的案件媒體報道不多,而且,似乎未集中在專業跟進報道上。
再說離職干部。有些干部辭職“下海”,利用原來的職務影響拿高薪,少數干部直接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社會中介機構等營利性組織投資任職、入股,利用原有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謀取利益。
《公務員法》第102條規定 :“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上海出臺了《關于進一步規范本市公務員離職后從業行為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對公務員退休或辭職后的從業行為作出了進一步的規范。上海市紀委、市監察局與市公務員局也出臺了《關于進一步規范本市公務員離職后從業行為的若干規定》,要求副處級以上干部,在離職三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社會中介機構等營利性組織任職,防止其利用原來的影響謀取利益。但筆者認為三年太短,與國外部分國家相比,尤其是根據中國國情和反腐敗的現狀,應規定五年期限。
除《公務員法》第102條外,2004年4月頒布實施的《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也規定 :“黨政領導干部辭去公職后三年內,不得到原任職務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內的企業、經營性事業單位和社會中介組織任職 ;不得從事或者代理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經商辦企業活動。”
還有的干部離職后并不直接經商。其實, 其實質與上述兩種情況一樣,不管這些干部的身份如何變化,法定的腐敗行為都是相同的。可惜的是,每當有人屢屢突破此限制時,部分行政與司法單位的介入都不及時,更不到位,甚至還允許這樣的“灰色地帶”長期存在。于是,中國特色的“法不責眾”又變相地鼓勵了后來者的“以身試法”。如此惡性循環不止……
所謂到位措施的關鍵是什么 ?
關鍵就是,要切斷“期權腐敗”的“變現”之路,不能單純寄希望于某一項措施,而必須建立多層次、多元化的防治體系。上海率先走出了一步。但是,效果如何,還取決于該《規定》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執行的力度、懲治的力度。按照慣例(以往的習慣做法。比如,在浙江省),懲治的力度大多是不到位的。
上海市對離職公務員的管理除了按《公務員法》辦事外,還補充規定“離職公務員不得從事可能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活動”,就是一種維護市場公平競爭規則的 “細則”,值得肯定。

最后,借手他人的腐敗。我國《刑法》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在立法上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關于這個罪名,雖然學術界有爭議,但其實施總體狀況還是符合我國國情的。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裸官”。我國公民獲外國國籍或獲得國(境)外永久居留權,是我國法律允許的。值得關注的是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而本人仍在黨政機關和公共機構任職的公職人員,已構成明顯利益沖突,涉嫌違法犯罪,可能或已經危及國家利益,就應采取應對措施。
從近期查處案件看,有的干部利用職權出賣國家利益,為配偶子女定居國謀利益從而獲得私利 ;有的干部將非法財產逐步轉移出境,涉嫌洗錢犯罪 ;有的干部將國有財產擅自移到本人或家人境外戶頭,以便擇機出逃 ;更有甚者充當間諜,為國(境)外敵對勢力收集情報。
再來看看國外的情況。以法國為例,雅克·勒內·希拉克,法蘭西共和國前任總統,出生于法國巴黎,他曾于1977年至1995年間3次連任巴黎市長,并于1995年5月第一次當選為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第五任總統。他又在2002年5月,以81.5%對18.5%的絕對優勢擊敗極右翼領導人勒龐(Jean Marie Le Pen)連任。2011年12月15日,在他離開總統職位的2年后,因挪用公款、濫用職權等罪名被司法機關判處兩年有期徒刑,緩期執行。
此案影響巨大 :不僅因為他是唯一一位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前總統被判刑的,而且還因為他所犯的是他在卸任總統后、近20年前的行為、而并非在他的總統任期上, 最后,還因為他在被判刑時,其民望遠超過第五共和國的前總統和現總統。
前總統如此,法國其他官員卸任后、再犯經濟罪被判刑的更是屢見不鮮。關于卸任后再任職的部分, 國外也有法律制約的“灰色地帶”,但關鍵是必須嚴格按照法律從重判決。為什么要從重 ? 很簡單,因為你曾經做過官員,即,知法犯法 ;你犯法比一般公民更容易得逞、犯法成本太低 ;而且對國家政權的侵襲腐蝕更嚴重。
因此,筆者認為,要加強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干部管理,就需要準確劃定管理目標群體,根據維護國家安全、防止利益沖突、有效預防腐敗的原則,采取防治應對措施 :
第一,黨和國家機關、人民團體、國有獨資、控股或參股企業、事業單位的干部主管部門(組織部、人事處),應該對其管理的干部進行逐人申報統計,每年將變更情況匯總報上級主管部門和相關部門。
第二,管理目標群體應是在上述機構單位擔任一定職務(目前可暫設定為正科或副處以上,含)的公職人員。在其配偶或子女移居國(境)外的規定期限內,須向干部主管部門書面報告規定的全部情況。
第三,管理措施不僅要全面掌握干部及其移居國(境)外配偶子女的私人財產及其流動情況,而且在干部從業及工作崗位限制、出國和護照簽證辦理,以及干部管理的有關程序等方面,都要按專門規定,嚴格執行并強化監管。
在現階段,中央頒布的《關于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是否得到嚴格執行,是防治這類干部腐敗的關鍵。
如果標本兼治的話,則急需健全法規,完善《公務員法》。退休干部到企業任職,《公務員法》中已經有明確規定。上海市對離職公務員的管理除了按《公務員法》辦事外,還補充規定“離職公務員不得從事可能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活動”,就是一種維護市場公平競爭規則的 “細則”,值得肯定。各地都需要對退休公務員的行為依法依規予以規范。
除了遵守《公務員法》以外,還需要對公務員退休經商進行限制,明確退休公務員違法違規經商的處罰細則。針對退休公務員管理難度大、監督困難的問題,作出周到的安排,依法對公務員“期權腐敗”的違規經營行為進行監督、規范。
其次,消除“灰色地帶”,就要對干部實行終身監督。制度漏洞和法律不完備,是退休干部失控的主因。雖然《公務員法》作出了規定,但范圍明顯偏窄。相關方面至今沒有具體操作規定。
第三,現行的相關監督條例,主要針對在職干部的,對退休干部的追蹤監督,目前基本上還是盲區。干部退休以后,往往成為“平民” 而避免了程序化的被監督。所以,對干部來說,根本性的防治腐敗應對措施,必須實行“監督終身制”。只有這樣,才能標本兼治地防止干部在退休以后利用其影響力腐敗作惡。
第四,關鍵是要及早制定和實施 “干部收入申報制度”, 宜早不宜遲。此制度既是上述應對措施的配套,又是預防干部腐敗的核心措施。技術層面應該沒有問題,關鍵是國家決策層的決心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