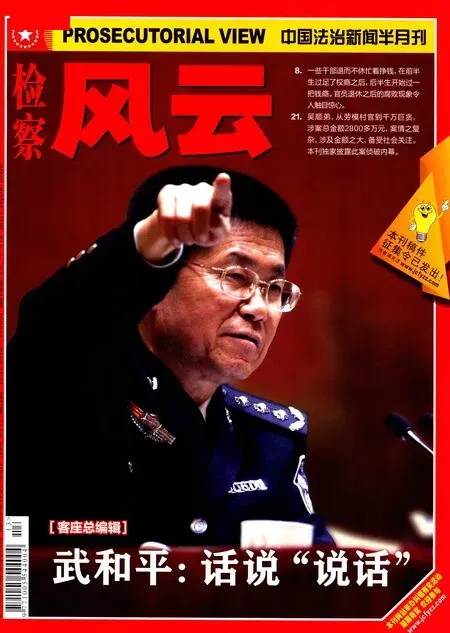還“能見度”于民才能遏制權力期權化
文/湯嘯天(上海市法學會副秘書長,上海政法學院編審)
還“能見度”于民才能遏制權力期權化
文/湯嘯天(上海市法學會副秘書長,上海政法學院編審)
權力期權化是更為隱蔽的權錢交易
形象地說,權力期權化就是延時兌現的權錢交易。官員在位期間,以公權力埋單的方式合法地付出投入,待其退位以后再安全地收回利益。相關的調查表明,權力期權化只不過是把任上權力操控的結果留待任后享受。權力期權化的特殊之處在于,行為人放公權力的“長線”,釣個人私利的“大魚”,獲取證據的難度更高了。原上海建設黨委書記、上海市房地產行業協會會長陳士杰,原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長、上海土地學會會長殷國元等,都是退休后“下海”撈“大魚”的實例。以房地產開發為例,開發商投桃報李向公權力掌控者輸送利益的方式可以分為即時兌付模式、遠期兌現模式,以及前兩者兼有的混合模式三大類型。即時兌付,在操作上類似于“一手錢,一手貨”,只要事情一辦成,商家必須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直接把利益交付給官員本人或其親朋等事實上的代理人。遠期兌現,是指開發商得到官員的“關照”之后,根據官員的暗示,采取從長計議的策略,等干部離任或下海后再給予“好處”。即時兌付與遠期兌現的混合模式,是指商家既要馬上滿足官員的欲望,又要對官員離任后的利益獲取作出不動聲色的安排。仍以殷國元為例,他在2005年退休后擔任上海市土地協會會長。此后直至案發,他仍然索取、收受巨額賄賂。受賄最多的一筆竟達1300多萬元,一天之內可以輕輕松松地收進7套房子。由于官員在任職時利用職權作出的投入是“無形”的,其退休后狂收“期權”的行為往往隱蔽較深,僅僅知曉一般情況的人員很難獲取證據。盡管我國近年來反腐敗斗爭成績顯著,打擊力度不斷加大,但從整體上看,對權力期權化的遏制是不力的。

領導干部權力期權化,作為一種以權力為資本參與社會物質利益再分配的腐敗,最大特點是不直接涉及金錢,沒有“一手權、一手貨”的對價過程,交易時間向后延伸,空間和權力“尋租”的交易標的物更加不確定,形式異常隱蔽。加之我國反腐敗斗爭的傳統手段局限于舉報、查賬、雙規“三板斧”,客觀上形成了權力期權化比一般腐敗行為暴露率更低、懲處率更低的局面。從犯罪學的角度看,犯罪也有成本收益問題,當犯罪的收益大于成本時,行為人就會竭力追求,反之就會放棄。權力期權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無本萬利”的犯罪,其作為資本投入的只是在土地拍賣、工程競標、規劃修改等環節的公權力“關照”,是不需要耗費任何私人財產的。況且,這種來自公權力的“關照”,有的經過當事人事先策劃,有的是雙方心照不宣,特別是雙方經過利益均沾的多次合作之后,暴露的概率反而降低了。
政府信息公開不到位與遏制腐敗不得力是互為因果的復雜關系。坦誠地說,如果所有官員都以敬畏之心在眾目睽睽之下工作,權力期權化就沒有存在的市場。
“制度+科技”是突破口
近年來,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已經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共識,不少地方已經提出了將“制度+科技”作為反腐倡廉工作的突破口的思路。應當充分肯定,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從決策和執行等環節加強對權力的監督,保證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就可以遏制權力期權化的蔓延。所謂制度,是指體現某種理念的規則體系,是無一遺漏地約束和規范所涉范圍主體行為的規則及其執行和實現。通俗地說,制度不僅是規則體系,更為重要的是得到無一例外的執行。制度如果得不到一體遵循,就是合法地“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提出用“制度+科技”打擊腐敗,首先要有把公權力這只“老虎”關進“籠子里”的制度設計,加之科技力量的作用才可能做到“用無私的電腦管住有私的人腦”。
(一)制度不能是貼在墻上的裝飾品
制度是基礎,是建立綜合性約束體系的根基,只有當制度處于不可替代、不可逾越的重要位置時,制度才能夠發揮正向的引導作用。制度如果不能實實在在地操作,那怕制定得再好的制度也只能是貼在墻上的一紙空文,除了能夠應付檢查考核之外就沒有任何作用。以澳大利亞為例,責任性、透明性、公正性是澳大利亞政府為防范腐敗而堅持的三個重要原則。責任性是指政府及其官員必須對其政策、決定和行為負責;透明性是指政府的構成、工作程序和決策必須公開接受公眾監督;公正性是指政府及其官員的決策必須基于客觀標準而不能帶任何偏見和成見。根據責任性、透明性、公正性的原則,澳大利亞制定了一整套操作性很強的制度,形成了內部與外部、行政與司法、官方與民間既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約的有效監督機制。當前,在我國的問題是,并沒有人公開反對“把公權力關進籠子里”的理念,而實際上公權力并沒有得到有效的限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幾乎成了公開的秘密。我國的反腐敗斗爭之所以至今缺乏根本性、全局性的突破,也是和頂層制度設計的不堅決、不得力有關的。例如,我國早就有領導干部申報收入等事項的制度,但是,實際操作中基本上變成了“照抄工資單”。2010年重新修訂和頒布的《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中也做了一些規定,包括要申報個人收入、子女配偶的從業、房產、投資等情況,但也沒有能夠起到從根本上遏制腐敗的作用。
(二)不能坐等條件成熟再制定科學的反腐敗制度
我國反腐敗斗爭的事實已經證明,靠中央派員調查、憑舉報信突擊整治,都不是高效率的制度機制發生作用。依靠小偷等偶然因素的介入發現腐敗分子更是被動到了極點。事后而為的嚴厲查究雖然對腐敗分子有一定的震懾力,但是,“查到誰、誰倒霉”的事后查究,既不能達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提醒腐敗分子謹慎行事的作用。權錢交易在我國并不是鮮為人知的腐敗手段,但由于雖然有“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聲勢,對權錢交易的制度約束一直偏軟偏弱,權錢交易也相應地從一般形態發展到了權力期權化。其實,無論是即刻兌現利益的權錢交易,還是延后支付報償的權力期權化,正在或者曾經執掌公權力的官員都得到了豐厚的利益回報。轉移財產的過程本身就是新痕跡遺留的過程,只要痛下決心從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開始抓起,真正敢冒險搞權錢交易的官員人數一定會下降。如果說,在我國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尚有社會誠信體系與信息統計體系兩大缺失的難處;同時就必須認識到,發揮我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傳統,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社會誠信體系與信息統計體系缺失的困難可以戰勝,遏制權錢交易的制度體系建立也指日可待。

在我國,并不是沒有制度設計比較堅決、執行得比較好的制度,但恰恰不在反腐敗領域。例如,酒駕入刑在我國提出時也曾經遭遇反對的聲音。有的人公開表示,每個人的酒量不同,以統一的標準衡量什么是酒后駕車、什么是醉酒駕車缺乏科學性。但是,由于有關方面頂住壓力,完成了醉駕入刑的立法,使得2011年全國酒后駕駛案件較2010年同期下降45%。一般而言,人們總是“先有規則、后有游戲”的,但隨著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也確實存在“在游戲過程中制定規則”的情況。從任何人都存在人性弱點的基本規律出發,遏制人性弱點的規則一定是在履行公務、監督權力的過程中逐步制訂、逐步完善的。鑒于人性的弱點與權力的結合會給社會帶來超乎尋常的破壞力,對人性弱點的遏制必須以公權力掌控者為主要對象。同時,我們既不能奢望遏制人性弱點的制度體系一旦建立就能夠完全地遏制腐敗,也不能奢望反腐敗制度建設會有自然形成的基礎性條件。從某種意義上說,反腐敗制度體系的建設“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
(三)不能奢望科技力量能為疲軟的制度“加鈣”
對在位官員的權力缺乏有效的監督是權力期權化產生的根本條件,提出用“制度+
科技”遏制腐敗必須解決制度的虛假
化和疲軟化問題。在腐敗問題已經遭致公眾憤怒的今天,絕大多數腐敗分子都會以“好話說盡、壞事做絕”隱蔽自己,任何有正義感的人都會感到制度是虛假、疲軟、管下不管上的。編織反腐敗的法網當然需要借助科技手段,但科技手段僅僅是可以利用的工具,科技手段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對腐敗產生遏制力。科技手段可以就制度的執行狀態作出如實的記錄,同樣,科技手段也可能利用制度的漏洞把腐敗掩藏起來。如果制度本身是疲軟的,特別是權力結構層面的問題不解決(例如對一把手的監督問題),無論在微觀層面使用多少科技手段,腐敗的蔓延只能有增無減。高科技手段類似于槍支彈藥,關鍵是要看掌握在誰手里、為什么而使用。從某種意義上講,在缺乏民主制度的環境中,越是依賴高科技往往越容易造成腐敗。
信息公開是關鍵
按照“制度+科技”的思路,對行政權的監督必須達到“權力邊界與權力運行程序公布于眾,權力運行痕跡每一環節可查,權力運行全程受監控,權力責任人終身可問責”的程度才可能真正發揮作用。顯然,信息公開與保守秘密的矛盾必須妥善解決。
近年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依法理,所有執掌公權力的部門和公務人員,都要為自己的所為承擔提供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的責任,并接受公眾質詢。公信力意指使公眾信任的力量,核心是信任。沒有公開、公平、公正,就不會有信任。公信力是社會成員基于信任、信賴而匯聚成的巨大力量,基礎是公開的真實告知。通俗地說,公信力是因為持之以恒地公開、公平、公正所匯聚在民心中的神奇力量,是不可能人為制造的。據中國社科院2011年法治藍皮書發布的《中國政府透明度年度報告(2010)》,我國政府信息公開情況喜憂參半,至少存在七大問題。特別令人關注的是,個別地方政府的信息公開工作存在退步現象。我國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14條規定:“行政機關不得公開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政府信息”。這一提法與世界上幾乎所有建立了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所規定的免除公開條件十分相似,但在實踐操作中“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恰恰變成了“以不公開為原則,公開為例外”。從世界各國政府信息公開的經驗看,無一不是堅決地采用陽光法則,以最大限度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作為維護社會穩定的根本手段。如果憂慮公開政府信息會引起混亂,“維護社會穩定”就可以成為阻止政府信息公開的最大理由。反之,如果認識到政府信息公開的虛化更會引起混亂,維護社會穩定就是推進政府信息公開的最大動力。時至今日,我們應當認識到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政府信息公開是社會穩定的最佳增效劑。以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的實現,從信息公開不到位與遏制腐敗不得力的被動局面中解脫出來。
政府信息公開不到位與遏制腐敗不得力是互為因果的復雜關系。坦誠地說,如果所有官員都以敬畏之心在眾目睽睽之下工作,權力期權化就沒有存在的市場。正因為政府信息公開至今還有相當大的距離,人民群眾雖然具有理論意義上的監督權,但由于政府信息公開的“能見度”不夠,監督就只能是“霧里看花”了。“能見度”本來是氣象學名詞,是反映大氣透明度的一個指標,即具有正常視力的人,在當時的天氣條件下還能夠看清楚目標輪廓的最大距離。其實,公權力的運作也有能見度問題。在社會管理領域“能見度”完全是人為控制的。如果以涉及“保密”或者“敏感問題”而遮蔽本應當公開的信息,實際上就是擴大了腐敗分子的自由度,加大民眾監督的難度。面對產品質量亂象叢生,民眾曾經呼吁“借我一雙慧眼吧”;針對反腐敗斗爭的嚴峻形勢,大聲疾呼“還能見度于民”應當是順理成章的。
編輯:陳暢鳴 charmingch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