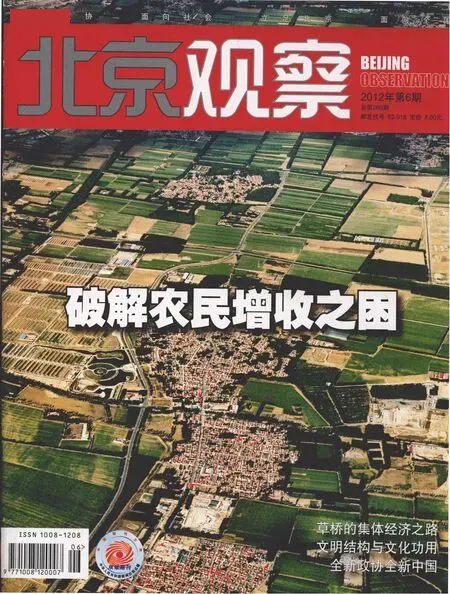郭老的回信
文/高 平
郭老的回信
文/高 平
之所以珍藏郭老這封信,是基于對他的尊敬。尊敬他是我國新詩的奠基人,是偉大的作家、學者,杰出的書法家;更因為他是在關鍵時刻鼓勵我走向生活、走向文學的長者。
在我家客廳的墻上,一直掛著一個不大的鏡框,里邊鑲著一封用毛筆豎寫的信。這封信我已經保存了62年多了,它可不是在房子里、箱柜里存放著的,而是曾在我的背包里、帳篷里隨我行軍,伴我過冰河、走過雪山,躲過了雨雪風霜的侵蝕,逃過了“文革”抄家的劫難,能夠保持住原件的完好,真不容易。它就是郭(沫若)老寫給我的回信。他寫這封回信的時間是1949年7月15日,地點是北京飯店。
我在出席中國作家協會的第七次、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都住在北京飯店,每次從走廊經過郭老住過的房間,我的眼前就會出現他在這里寫這封信的的身影。可惜,他早已遠行了。
我之所以珍藏這封信,當然是基于對他的尊敬。尊敬他是我國新詩的奠基人,是偉大的作家、學者杰出的書法家;更因為他是在關鍵時刻鼓勵我走向生活、走向文學的長者。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我知道了我的舅舅李孝勖是清華大學電機系的中共地下黨員(和朱基、李錫銘在同一個黨小組)。我作為—個向往新生活、新天地的濟南師范學校的學生,毅然辭別父母,只身從濟南奔向北平,來到舅舅身邊,住進了他的宿舍新齋804號。記得隔壁住的正是著名作家、教授李廣田先生。1992年4月我到昆明時,曾特意去他在“文革”中被逼自沉的蓮花湖憑吊。
7月1日,北平市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了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的大會。郭沫若在會上朗誦了一首新的詩作,題為《七—頌》。

7月2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正式揭幕。7月6日上午,毛澤東主席到會講話,他說:“今天我來歡迎你們。”“因為你們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們是人民的文學家,人民的藝術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學藝術工作的組織者。”
大約在7月8日左右,我給郭老寫了一封信。因為我寫信從來不打草稿,無底稿可留可查,那時的日記也已焚于“十年浩動”,所以那封信的具體內容我已記不全了。但是從郭老的回信中可以反映出其中的兩點內容,那也就是我給郭老寫信的動機和緣由。一是當時我從報上公布的中華全國文代會的代表名單中,看到有許多我所崇敬的革命文藝家,也有和工農兵距離較遠的文藝家,特別是當我從平津代表第二團的代表中看到了張恨水的名字,知道他是被劃為“鴛鴦蝴蝶派”的,而毛澤東在講話中統稱代表是“人民的文學家”。我大惑不解,想就此“討個說法”。那時的我把革命看得神而又神,把革命的文學看得純而又純;不懂得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更不懂什么統一戰線,屬于列寧批評過的那種“左派幼稚病”的感染者。所以,我在給文代大會總主席郭沫若的信中問道:不熟悉工農生活也能算人民作家嗎?暗指的就是張恨水。由于我沒好意思點出張恨水先生的名字,致使郭老必然地誤以為是我自己既不熟悉工農生活又想當人民作家了。于是郭老直接對我作了熱心、耐心的回答和教導。至于我在信中因什么問題而使用了“棘手”一詞,我就想不出了,但郭老是把它和我的提問聯系在一起來回答的。二是我讀到了《人民日報》上發表的他的《七一頌》,覺得有些標語口號式的傾向,政治性壓倒了藝術性,不大符合一個大詩人的水平,那時的我才17歲,“初生牛犢不怕虎”,就在信中對郭老提出了批評。這就是為什么他在回信中寫最后那樣一句話的根由。
信從清華園寄出不幾天,就收到了郭老的回信。投遞者前來時我不在,是從門縫里投進室內的。我從城里回來后撿起信封一看,那漂亮已極的毛筆字,那“北京飯店郭”的字樣,真叫意外驚喜!

郭老的回信全文如下:
高平同學:
不熟悉工農的生活斗爭是很難成為一個“人民作家”的。真正想做“作家”總要有豐富的生活體驗,決心進工廠農村當然最好。先埋頭學習一時吧,不要那么著急,便感著“棘手”。我的七一頌只表達我對七一文告的一時感興而已。
郭沫若 七.十五
從這封回信中可以看出,郭老對于一個無名小青年是多么地認真關懷,對自己的作品是多么謙遜,對批評意見是多么有涵養。這些都令我深深感動,歷久不忘。
郭老回信的1949年7月15日,正是全國文代會休會的日子,各代表團分別討論文聯全國委員會候選人名單。郭老正是在百忙之中,借用這個時間給我寫回信的。
郭老的教導,加上我舅舅的建議,使我決心離開我的出生地北平,毅然走上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當即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奔向解放戰爭最后的戰場。離開北平的前夕,也正是共和國成立的前夕,我向郭老致信告別,表示了一定在文學創作上做出成績的決心,在信的末尾還許下了10年以后向他匯報的諾言。
10年之后,正值共和國成立10周年,郭老早已躋身于領導人的行列,而我雖然已經出版了《大雪紛飛》等三本詩集,在文學創作上有了一點成績,卻剛被打成“右派”,正在農場勞動,怎好給他寫信履行諾言呢?
今年是郭老120周年的冥壽。我謹以這篇短文,寄托對他的緬懷。
作者系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名譽委員
責任編輯 劉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