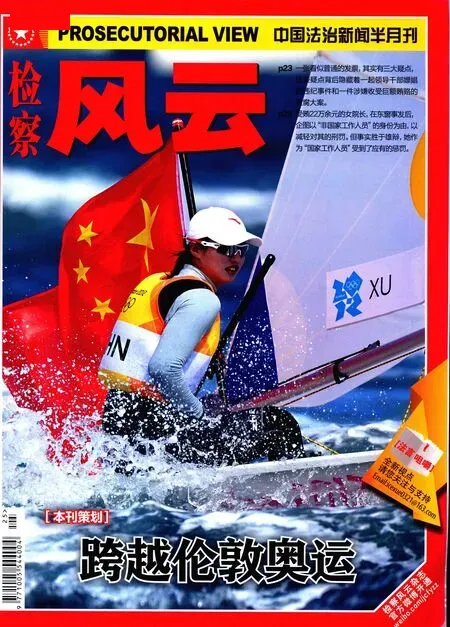國企改革路線圖
文/朱敏 衛祥云
國企改革路線圖
文/朱敏 衛祥云
在國企改革尚未突圍的情況下,能否真正消除民企心理障礙,引導大量民營資本入場,產生促進市場化改革的“蝴蝶效應”,仍是未定之數。

從中石化天價酒,到中國鐵路天價宣傳片,國企改革的爭議一度甚囂塵上。而近期浙江、重慶等省市高調“挺私”,且國資委、鐵道部、交通運輸部、衛生部、銀監會等部門也紛紛為落實“新36條”一同打出組合拳,其中“國資14條”規定,民間投資主體可參與國有企業改制重組。凡此種種,真的宣告民間資本的春天即將來臨?國企改革在新的框架下又重新啟動?
不過,在不少觀察者看來,與兩年前政府方面的高調相比,近年來民間資本的動向似乎未有實質性變化:壟斷國企依舊強大,民間資本仍在“四處游蕩”。由于高高豎起的“玻璃門”,使得試圖打破行業壟斷的政策一次又一次地成為“一紙空文”,民間資本的存在及擴張空間被壓縮。如今,在國企改革尚未突圍的情況下,能否真正消除民企心理障礙,引導大量民營資本入場,產生促進市場化改革的“蝴蝶效應”,仍是未定之數。
以史為鑒:國企改革的真問題
縱觀中國近代經濟史,貫穿始終的首要問題便是對經濟參與主體的定位與分工,即由誰來辦企業,由什么來配置資源。從洋務運動到改革開放初期,官商合辦、官督商辦、官辦三種模式在中國歷史的不同階段此消彼長。但無論哪種模式,權力始終居于核心位置,既制定游戲規則,又直接配置資源。如果說有差異,僅在于不同歷史階段主導經濟的力量在形式和程度上有所差異,而這些差異主要源于中國所處的歷史階段和當時的國際環境。今天的國有企業改革,究其本質,仍是這一歷史問題的延續。
無論中國歷史上的儒家文明,還是西方啟蒙運動時的社會契約論,政府的本分都是維護公平正義的管理者,而不是與民爭利者,所謂“政府應以義為利,而非以利為利”。因此,公共領域和資源壟斷行業由政府經辦,競爭性領域由民間經辦,由市場配置資源成為既符合契約精神又符合經濟原則的模式。中國封建社會的鹽鐵專營,歐美國家成熟的市場經濟模式無不如此。這是我們今天比較一致的認識,但這種認識是建立在獨立的民族國家和成熟的經濟體系的前提下,也是中國在經過上百年探索試錯并付出沉重代價后才換來的教訓。關于中國企業的模式,漢學家費正清、費維愷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指出,涵蓋官商合辦、官督商辦、官辦三種企業形式,三種形式之間,是一種不斷改進的過程,表明進入近代以后,中國企業的發展形式,由起初的政府和企業同時參與,退化到后期單純的政府直接操控。這其實是按照黃仁宇大歷史的視野對中國百年企業史的一種總結,但縱使今天,國有企業仍未徹底走出歷史的陰影。
比如,政治意義上的鐵道部是國務院一個部,經濟意義上則是一家可以稱之為中國鐵路總公司的央企,但實質上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回顧歷史竟然發現這正是洋務運動時期國家興辦鐵路模式在今天的翻版。再如,在國企問題上一邊是李榮融卸任國資委主任時自詡實現了央企增值保值的“無愧于心”,一邊是輿論媒體對“國進民退”和國企壟斷的口誅筆伐,政府對國企的錯誤定位讓管理者成為兩頭受氣的風箱耗子,即便如此,像中糧收購蒙牛這樣劣幣驅逐良幣的案例時有發生;在官商問題上,一邊是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在經濟活動中的如影隨形,一邊是每倒下一位企業家必帶出一批“有問題”的官員,權力對市場的干預所滋生的腐敗讓權力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但人人又希望依附于權力而從中食利。可見,很多本該超越意識形態而無需爭論的問題在現實中卻與常識的距離總是很遠,背離常識的結果必定是對經濟規律的扭曲,而片面甚至錯誤的認知則容易被固化積淀成社會問題,最終又反過來挑戰常識。就像國企問題上,很多在現代企業理論上荒誕可笑的事情,在現實中卻成為尊重歷史傳統,維護政治正確性的選擇,這也是研究國有企業改革不能只顧理論的與時俱進,而忽視歷史的原因吧。
今天國企數量不但大幅減少,其規模和盈利能力也今非昔比,而私企和外企早已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力量。《物權法》、《反壟斷法》等法律法規的出臺,也成為市場經濟的有力保障。但是,一個更加嚴峻的問題是,在經濟改革的同時,腐敗、不公平也非常嚴重,這些問題究竟是改革的副產品,還是需要通過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的問題。長期以來,在社會穩定與意識形態的挑戰下,在速度和規模的刺激下,“大政府小市場”所導致的結果是資源的低效率配置甚至是錯誤配置,在經濟管理體制上,“重審批,輕監管”導致的是經濟秩序混亂和信用體系的急劇萎縮,在市場化程度上,產品的市場化而非要素市場化讓政府仍然牢牢地掌控著經濟主導權。這才是問題的根源,但很多人卻把板子打到市場經濟的屁股上。具體到國企改革,國企之所以存在腐敗,低效率,不分紅等問題,這當然與國企內部的治理結構有關,但這不是根源問題。
今天的國有企業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改革開放以來國企改革后的“第三次改革”,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從產品的市場化向要素的市場化轉型的必然要求。雖然,我們已經站在全球化和中國市場經濟的背景下討論國企改革,但從歷史淵源上看,國有企業實質上是一個政治與經濟的混合體,國有企業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國家政治經濟史的縮影。“國有”包含了國家、國民、國體、領袖、軍隊、意識形態等政治要素,“企業”包含了產品、市場、分配、管理等經濟內容。因此,國有企業的改革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企業改革,而是對政府介入程度,對國企進行定位的問題,這是國企改革的源頭性問題,或者說是國企改革的真問題。
以人為本:競爭性國企如何退出
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正確定位體現在兩個層面上,首先是政府不能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其次才是如何當好裁判,但前者并不是國企存與廢那樣的形而上學,而應是國情與規律的結合。對于國有企業改革,基本的原則就是分類管理,首先要把壟斷領域的國有企業和競爭領域的國有企業區分開來,其次才能分類研究國有企業其他方面的改革。可見,國企改革的本質并不是國企該不該存在的簡單選擇,而是在哪些領域以何種方式存在的問題,轉型意義上的國企改革首當其沖的問題并不是國企作為一般意義企業的改革,而是國企的定位問題,這既要考慮市場對資源配置效率的要求,更要考慮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歷史延續。經過多年的摸索和試錯之后,我覺得,分類管理應該成為國企改革的基本思路,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探索科學的管理體制,而不是把適用于私企的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照搬到所有國有企業中。具體而言,商貿、建筑等一般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必須通過改制逐漸退出;金融、保險、證券等由央企壟斷的金融行業,要對民間資本逐步開放,實行國企和私企的公平競爭;公共領域和資源壟斷的非競爭性領域,由于投資規模大,收益周期長,協商成本高,不但要實行單一的國有體制,還要實事求是地探索符合國情的管理體制和激勵機制,而不是疊床架屋式地復制現代企業制度。

國企改革不但要體現效率和公平,而且要考慮到風險與可操作性。競爭性領域國企的效率明顯低于私企,其資產構成比較簡單,評估與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和權力尋租的問題不會太大,退出后的巨額資金可通過轉持全民社保基金來填補社保資金缺口。經濟領域的改革支持了社會的發展,這和“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完全吻合,而且整個過程不存在政策和法規方面的障礙。目前來看,競爭性國企的退出是一個爭議不大的問題,其退出只是時間問題,關鍵在于如何平衡因退出引發的利益調整,這需要決策層的勇氣和政治體制改革的跟進。金融行業對民間資本的放開,不但是金融改革的應有之義,也是把慣于四處炒作的游資“蝗災”引導為服務于經濟建設的金融資本的必然選擇。2010年5月,國務院出臺的《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正式允許民間資本興辦金融機構。這一領域需要正確引導和加強監管。非競爭性國企的轉型和改革,關鍵在于三方面:一是該領域只能采取國有形式,二是非競爭的國企不能復制現代企業制度,三是探索科學的管理模式和激勵機制是唯一出路。這需要深化認識和制度創新,也需要下文做簡單闡述。
以退為進:非競爭性國企如何改革
公共領域和資源壟斷行業分屬行政壟斷和資源壟斷,其資產價值具有自然增值和經營增值兩種屬性,且自然增值屬性可以無限大,如果對這些領域進行價值評估必然會導致利益輸送和國有資產流失,如果搞不好還存在前蘇聯那樣巨大的政治風險。因此,這些領域必須實行單一的國有形式。這不是改革過程中的妥協,而是一種理性選擇,即使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在這些領域也不是徹底的放棄國有。
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是“股份制”,股份只有兩個基本要求,一是產權明晰且要落實到自然人,而國有壟斷企業的資產是全體人民的,無法落實到每個自然人;二是企業資產可以交換、轉讓和出售,而國有壟斷企業的資產交換、轉讓和出售如果遵循現代企業制度中股東多數同意原則,不但交易成本昂貴,而且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如果強行植入現代企業制度的話,制度的執行必然流于形式。作為資產所有者的全體民眾、資產監管者的國資委、資產經營者的國企高管這三大主體間的關系看似清晰,實則不倫不類,其矛盾難以調和。如果這樣,那么央企“地王”頻現,央企高管及員工的高薪酬和高福利又無可厚非,因為現代企業制度追求的首先是公司的治理而非社會的公義。
科學的管理體制必須著眼于解決以下問題:一是理順壟斷國企租金、稅收、利潤三者之間的關系;二是理順國企高管的激勵機制。租金、稅收和利潤是三個不同的經濟范疇,反映的是不同的經濟關系。國企改革從統收統支變為照章納稅,把稅收和利潤兩個范疇分開了,但是,“租金”和“利潤”仍然沒有分開。租金屬于要素價格,而利潤屬于經營收益。張曙光說:“由于沒有資源租金的概念,由于不向占用大量資源要素的國有企業收取租金,出現了兩個荒唐的結果:第一個結果是,國有企業把資源要素租金據為己有,租金變成了企業利潤,提高了企業的市場價值,也使得對國有企業經營者的監督和考核失去了客觀的依據。如此一來,如果有外國投資者參股,就可白白多得股息紅利;如果并購重組,也會發生扭曲,特別是國企和民企合資重組,必然高估國企價值。第二個結果是,由于國有企業將國家租金據為己有,成為經營者經營努力的成果。這樣,就為一部分人無償占用全體人民的利益打開了方便之門,資源要素租金養肥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可見,盛洪所說“國企利潤來源于不繳租金”很有道理,但國家對于資源壟斷行業征收遠遠高于普通行業的特別收益金(俗稱“暴利稅”)也是事實,這樣的結果是各方都有怨氣。因此,制定科學的租金征收標準,對壟斷國企征收租金;減輕稅負,實行國企私企稅收標準上的統一;利潤同樣轉持全民社保基金。這樣,在理順租金、稅收、利潤三者關系的同時,又體現了公平,且便于操作。
近年來,隨著媒體對國企高管的高收入的頻頻曝光,國企高管的激勵機制問題浮出水面。大型國企,特別是央企的高管,往往是由政治局會議討論后經組織部門任命產生,而且高管直接調任黨政領導位置的例子比比皆是,這說明國企高管的產生,主要是基于政治邏輯而非商業邏輯,那么,在激勵機制上理應納入黨政系統的考量,而非財富與權力的先后通吃。
將國企按照分類管理的原則分為壟斷性國企與競爭性國企,并分別采取國有獨資形式和逐步退出的不同路徑進行改革,最終的目標都是一致的,即要讓國有資產和其創造的價值能夠真正落實到全國人民。
不容諱言,目前關于這方面的研究,以陳志武、張維迎為代表的一批著名經濟學家和學者提出了相當有見地、有水平的觀點,當然也有不同的思想和言論。我們雖對此觀點堅定支持,但認為對此大可不必以進、退為界;以左、右標簽;以好、壞分野。而應該允許發言、允許討論、允許質疑、允許提出更好的見解。只有通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真理才能越辯越明,越能為國企改革的決策者起到警示和參考作用。
縱然目標明確,路經清晰,國企改革仍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做好“頂層設計”,分階段的有序推進。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從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有進有退”的戰略方針,到國務院前總理朱镕基主持的“抓大放小”改革,再到目前的繼續改革,每個階段應根據不同情況,實事求是地提出和執行不同改革方針和政策。應該說,到目前為止,國有企業改革進入了一新的發展階段,面臨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尤其是對一些敏感問題的探討和解決,確實到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深水區”。對于國企改革的決策者來說,采取快刀斬亂麻的措施和方法確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虞。而前人之鏡,可為后人之鑒,但“前人”不可能代替“后人”審時度勢,進行決策。則是淺顯明白的道理。國有企業的決策者尤其需要根據“天時、地利、人和”做好現階段的頂層設計。
總之,國企改革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之一。我們的研究一定要秉持獨立、客觀和理性,切忌發表情緒化的言論和未經深思熟慮的觀點,如“打倒壟斷國企”和“國企紅利分配是偽問題”等。至少從目前國有企業存在和經營的現狀看,壟斷性國企尤其是公益性國企還是客觀存在的,也是應該上繳紅利的。這也是國企改革階段推進繞不開的議題。我們一定要盡力避免制造對抗氣氛和人為地制造矛盾,以免“欲速不達”,甚至連傳播思想的作用也被抵消。
(作者衛祥云,國資委商業科技質量中心主任)
編輯:陳暢鳴 charmingch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