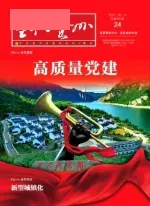城市小網格 民生大舞臺
——湖北宜昌網格化管理創新樣本探析
文 Ⅰ 周倫 李學會
城市小網格 民生大舞臺
——湖北宜昌網格化管理創新樣本探析
文 Ⅰ 周倫 李學會
編者按:近年來,社會管理創新成為各級政府部門轉變政府職能、提高行政效率、提升服務質量、優化發展環境的重要路徑。湖北宜昌在全市推行社區網格化管理,重構基層管理和服務架構,建立和強化了個體之間有效聯結的微觀組織單元,實現了政府公共服務的有效投遞。這一鮮活經驗,具有借鑒意義。
江水出峽,其勢浩蕩!
2010年10月,中央政法委、中央綜治委確定了35個市、縣(市、區)作為全國社會管理創新綜合試點,湖北省宜昌市是其中之一。一年后,全國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工作座談會在宜昌市召開,社區網格化管理的“宜昌經驗”,再次攪動荊楚大地,吹皺了中國社會管理創新的一池春水。
城市需要網格化管理
當前,我國正處于城市化加速推進的發展階段,大量人口匯聚大中城市,社區人口規模不斷增加,社區工作者工作壓力隨之增大,原有的社區劃分已不能滿足現有經濟社會要求。調查顯示,我國街道的平均規模已達3.5—6.5萬人,居委會平均擁有人口數為3127人、969戶。而從國際經驗來看,發達國家城市中社區一般不超過1000人、300戶。因此,正是在這種“結構緊張”的狀態下,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大量發生和積累在社區,從而直接影響社會穩定,社區正在面臨著難以承受的重任。
事實上,現代社會中單位小區淡出,商品房小區成為社區主體,陌生人社會不斷替代熟人社會,社會互動的應然性逐漸降低。如果個體之間缺乏組織互動,就會出現社會原子化,這不僅使個人缺少確定性、安全感和價值歸屬,還使整個社會陷入整合危機。
隨著信息化網格技術的不斷演變,網格同空間地理技術相結合,從而開始應用到城市地理信息系統建設中來。其實,網格化管理并不是宜昌首創,但宜昌把網格化和信息平臺有機結合起來,卻是開了先河。
2010年以來,宜昌市在充分借鑒北京、深圳等地網格化管理基礎上,創新體制機制,通過“政府直接購買服務”的路徑,向廣大社區群眾投遞專業化和規范化的社會工作服務。
通過公開招考選聘網格管理員進入城區每個社區,為市民提供“零距離”、“多方位”服務。他們向社區群眾傳達黨和政府的聲音,宣講各種惠民政策,服務居民衣食住行;深入社區服務管理最前線,采信息、除隱患、調矛盾;做好事、美環境、送關愛……社區群眾送給他們一個好聽的名字——“格格”。
有專家指出,依托數字化城市所建立的社區網格,正是打破傳統意義上的大社區格局,重構了基層管理和服務架構,建立和強化了個體之間有效聯結的微觀組織單元,實現了政府公共服務的有效投遞。還可以實現管理對象的全覆蓋,并加強對高危環境、人群和弱勢群體的監控。

網格管理員織就民生網
宜昌市按照“街巷定界、規模適度、無縫覆蓋、動態調整”的原則,把城區121個社區劃分為1110個網格,每個網格配備一個管理員,負責250戶或300-500人的服務與管理。通過自上而下建立統一的新型社會服務機構和隊伍,依靠社區E通數字化平臺,全面履行信息采集、綜合治理、勞動保障、民政服務、計劃生育、城市管理、食品安全等七項綜合信息服務職責。網格管理員猶如敏感的神經元,延伸至整個社會肌體的最末梢,織就血脈暢通的一張關愛民生網。(如圖)
李慧是宜昌市西陵區中書街社區的一名“格格”,她的管轄范圍為15049平方米,其中有240戶居民,3條小巷。
一天清晨8點,李慧剛走到童家巷口,78歲的大媽楊忠秀就迎了上來。“巷子那頭的垃圾收拾晚了,臟死了!”楊大媽邊抱怨,邊拉著她來到巷子深處的垃圾堆放點前。李慧蹲下身來,將垃圾照片和具體位置通過手中配發的社區E通發送到市網格管理中心。
上午10點15分,李慧轉到了汪家巷,社區志愿者冀學云告訴她:17號治安探頭壞了。
下午4點30分,到了孩子們放學的時間。李慧守在學校門口,將20多個孩子接到社區。
傍晚6點,李慧再次轉到上午報告的問題發生地,發現垃圾已經被清走了,探頭也已經修好。此時,已是華燈初上。
正是通過李惠這樣普通的網格管理員,在城市小網格這個民生大舞臺上不斷展演著一個個生動的故事,政府與群眾的溝通互動渠道暢通了,社區工作人員工作負擔減輕了。更為可喜的是,通過這種貼身式的服務,讓政府和老百姓的心貼得更近,也讓居民之間組織互動日益緊密。
政府直接購買實現公共服務的有效投遞
發端于英美的“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已成為一項流行全球的制度性樣本。政府購買服務是指“政府通過直接撥款或公開招標方式,交給有資質的社會服務機構來完成,最后根據擇定者或者中標者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來支付服務費用。”
我國自上世紀末引入這一制度后,各地在公共交通、居家養老、醫療衛生、社工服務、公交服務、行業性服務等多個領域迅速展開,上海、無錫等多個城市更將其視為最重要的制度創新而加以大力推進。
但是,這一制度在我國同樣面臨著不可回避的問題,一方面是政府購買服務本意是政府職能外包,實現獨立關系競爭性購買。事實上,政府與社會組織還存在著雙方地位不清、角色不明、能力欠缺、購買過程缺乏規范、監督和評估缺乏、公共責任得不到體現。另一方面,我國社會組織不但數量少,而且很大一部分依附于政府,公共服務能力比較弱,也缺乏提供公共服務的實踐經驗。
以湖北為例,社會組織仍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量小質弱。目前全省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3.6個,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每萬人50個,也低于發展中國家的每萬人12個。顯然,我國政府和社會組織都還沒有為迎接這一新型制度做好準備,各種購買過程和結果中存在顯而易見的風險。
宜昌市面對這兩大顯性問題,創新路徑,提出和建構全新的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模式,即政府作為直接購買主體,通過合同制形式,向符合相關條件的自然人購買社會公共服務與管理等活動的過程。具體到網格化管理上就是政府通過建立市社區網格監管中心,各區成立網格監管分中心,跳過委托社會中介組織這一環節,使用市區兩級財政,直接向招錄在崗的網格管理員公開購買社會工作服務。
通過這一模式建立和維持,不但強化政府公共責任意識,轉變政府職能,提升政府公信力,依靠社工專業化服務拉近政府與百姓之間的距離,而且更好地杜絕“服務供給方”缺陷和競爭性購買不足等難癥,從而實現更加高效、清晰、專業的公共服務投遞。
宜昌市通過網格化管理,帶動街辦、社區管理職能變革。現在,宜昌城區所有街辦都成立了便民服務、綜治信訪維穩和網格管理“三個中心”。
與之相對應,原來的社區諸多科室部門也隨之“瘦身”,整合成便民、維穩、網管三個站,同時擁有社區專職工作者、網格管理員和社區志愿者三支隊伍。
基于這種基層治理模式的革新,加強了政府基層力量,整合了部門分散資源,提升了社區服務水平,使政府從越位、錯位回到正位,從而最終實現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更為重要的是,在抓好社區公共服務供給的同時,也為推進社區自治提供了空間和環境,確保“議行分設”逐步展開。正如宜昌市政協主席、市社會服務管理創新綜合試點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李亞隆所言:“通過網格化管理,為推進城市社區和街道兩個層面的改革埋下了很大的伏筆,為以后體制層面的改革打下了基礎。”
培育社區公眾參與精神
民主單位越小,公民參與的可能性就越大,而民主單位越大,公民參與的積極性就越低。宜昌市通過在社區設立網格,構建網格管理員這一黨委政府與社區群眾橋梁和紐帶,劃小了民主單位,加強了網格內住戶居民的聯系互動,增強社區居民與社區利益的關聯度。交往越頻繁,居民對社區的歸屬感便越強。
網格員積極發動黨員和群眾、志愿者力量,開展有特色的文體活動,以此加強與居民群眾的密切聯系。例如,社區開展的趣味運動會以網格為參賽方陣,網格管理員為方陣組織者,廣泛發動群眾,許多上班族、年輕人從高樓中走出來,加入到社區活動中來,增加了社區居民之間的信任團結。
此外,社區居民還主動將身邊的問題和生活中的諸多不便告訴網格員,使居民身邊的瑣事通過他們成為政府案頭的大事,激發了居民參與城市管理的熱情,形成了市民與政府良性互動、互促互動的格局,為構建和諧社會打下了堅實基礎。
2011年12月,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來宜昌考察,就盛贊到該市在加強社會管理創新中走在全國前列。201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在宜昌考察時說到:“以網格化管理為基礎,把管理與服務直接覆蓋到居民、到住戶的做法,很有新意,很有成效,希望繼續探索創新,為全國社會管理創新積累更多經驗。”
(作者單位:中共宜昌市委黨校;南京理工大學紫金學院 責任編輯/李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