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浩添——八零后眼科英才
本刊記者 劉玉杰
林浩添
——八零后眼科英才
本刊記者 劉玉杰
編者按:今年年初,國際頂尖醫學雜志《柳葉刀》(《The Lancet 》)在線刊登了中山大學中山眼科中心研究人員的最新研究成果,該研究首次收集、跟蹤并完善了結膜吸吮線蟲病的臨床資料,并成為該雜志一月份在線閱讀點擊量最大的文章。該研究成果的第一作者就是我國眼科后起之秀林浩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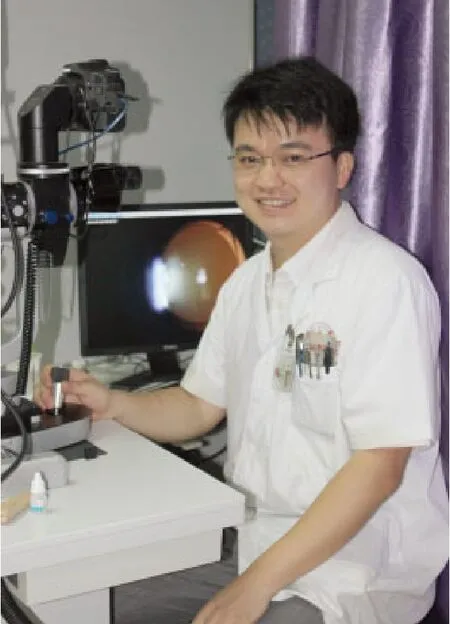
專家簡介:
林浩添,中山大學中山眼科中心臨床醫師,博士,眼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研究人員,是中山大學重點培養的青年科研人才之一。以第一或聯合第一作者發表SCI論文13篇,在國內核心期刊第一作者發表論文10篇,參與編寫或翻譯眼科專著4部;作為負責人承擔科研課題5項,同時參與了衛生部臨床重點項目等6個課題;擁有中國專利2個和美國專利1個;任7個國際著名眼科雜志的特約審稿人,廣東省醫學會會員,中山眼科中心《眼科通訊》編委;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和學術交流近20次,包括2011年歐洲眼科年會和2012年美國小兒眼病和斜視會議。
眼睛是心靈的窗戶,是視覺系統的載體。對于中山大學中山眼科中心醫師林浩添來說,守護眼睛的健康更是他一生的追求,是他所熱愛的臨床科研的職責所在。為了人們的眼睛健康,他將自己年輕的熱血與激情傾注于一間普通的醫療室、一方小小的實驗臺,在青春的大好年華里取得了一次次的突破與創新。
天生我才,厚積薄發
林浩添大學時所修的是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臨床醫學專業(七年制本碩連讀),高考時成績本來可以報考清華或北京大學,但因受當中醫的父親影響,從小立志當一名醫生的他最后選擇了中山大學醫學院,就這樣,林浩添走上了這條漫長的“不歸路”。
學生時期,相對于喜愛戶外活動的其他同學,林浩添更喜愛一個人在宿舍里讀書(現在時髦定義為“宅男”),尤其是對專業課的自覺涉獵,使他在醫學知識和科研思維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大二時,喜愛鉆研的林浩添利用暑假時間參加了學校的暑期科研活動,并在老師的指導下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完成了科研生涯的第一篇論文,成功發表在中山大學學報的醫學版上。這無論是在當時還是現在,對本科生來說都是十分難得,也體現了林浩添在科學研究上的優厚天賦。
除了天資以外,林浩添談到,自己走上今天正確的科研道路是與老師們的啟發與挖掘分不開的。從中山醫學院的基礎課學習到中山眼科中心的臨床和科研工作,他得到了很多老師的竭力指導,如指導他在《柳葉刀》報道特殊眼科病例的梁小玲教授、帶領他進行小兒白內障研究的全國白內障知名專家劉奕志教授和陳偉蓉教授等。林浩添還清楚記得當年組胚老師在第一節課上說的話:“教育不是灌滿一桶水,而是點亮一盞燈。”這對林浩添有很大啟發,他發現學習的意義不在于能夠記住多少東西,而是理解了多少東西;“看問題要長遠,不要因為過程的一些小失敗和小挫折就否定掉自己。知識是厚積薄發的,一個人能有多成功就像一個桶能裝多少水一樣,取決于最短的那個板。能力的競技是長時間的,真正能笑到最后的往往是那些腳踏實地、扎扎實實的人。”林浩添如今也這樣和他的師弟師妹們分享自己的成長體會。
青年壯志,碩果頻出
盡管從事臨床治療與科研時間不長,林浩添科研興趣廣泛,并已在眼科研究中取得了多項創新性突破,填補了一些國際空白,豐富了我國眼科科學的研究現狀。
角膜淋巴管之謎
角膜堿燒傷是臨床上最常見的致盲性化學性眼外傷,已有研究表明眼化學傷是角膜移植預后較差的眼病。然而傳統認為,角膜是無血管和無淋巴管的組織。長期以來的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角膜新生血管上,而有關角膜新生淋巴管的研究較少。通過研究,林浩添不僅證實了角膜堿燒傷后有角膜新生淋巴管的存在,而且動態檢測了堿燒傷后角膜新生淋巴管和血管的變化,闡明了二者之間的關聯;同時,推測在角膜免疫排斥反應中,新生血管和淋巴管構成了角膜的“免疫雙臂”,新生血管提供了免疫效應細胞進入角膜的通路,而淋巴管則加速角膜抗原物質進入引流區淋巴結,是角膜免疫的“出口”,抑制角膜新生淋巴管對提高角膜堿燒傷的臨床治療有著重要的意義。這一研究揭開了角膜淋巴管之謎,為臨床上眼部病變(角膜病和胬肉等)的治療提供了新的思路。
圍絕經期婦女干眼癥之患
圍絕經期指近絕經時從出現與絕經有關的內分泌、生物學和臨床特征起至絕經后1年的期間。女性在圍絕經期由于卵巢功能的退行性改變,雌激素水平下降,引起神經內分泌功能失調,免疫功能下降和植物神經系統功能紊亂而出現一系列癥候群,稱為圍絕經期綜合征,它不同程度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水平。林浩添認為圍絕經期婦女雖然干眼發病率高,但診斷應慎重。通過對圍絕經期婦女的眼部臨床資料和圍絕經期特征的性激素水平檢查以及可疑免疫性疾病患者的排查研究,林浩添發現有眼干燥癥狀的圍絕經女性的干眼確診率高,但仍存在干眼診斷性試驗假陽性。干眼患者的角膜厚度、結膜杯狀細胞數量和印跡細胞學的眼表特征改變,可協助與圍絕經期綜合征鑒別。林浩添還對圍絕經期女性通過不同方案的個體化診治和隨診觀察,找出對這個特殊人群難治性干眼的個體化治療方案,并同時通過蛋白質組學等基礎研究進一步探討出干眼與性激素的關系,為解決圍絕經期婦女干眼癥之患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艾滋病眼部合并之癥
艾滋病患者可發生多種艾滋病眼部合并癥,包括了視網膜病變和并發性白內障等。HIV-1gp120是位于病毒顆粒和受感染細胞表面的高度糖化的親水性包膜糖蛋白,而APOBEC3G是宿主體內一種新穎的抗病毒因子,能使HIV在逆轉錄過程中脫氨基化和產生超突變,從而使病毒喪失活性。通過研究,林浩添不僅探索了HIV-1gp120在艾滋病視網膜病變的發病過程中的作用,而且首次提出了眼部IFN-APOBEC3G信號通路可為防止HIV等病毒破壞血-視網膜屏障并徹底清除病毒儲存庫提供有效策略;聯合APOBEC3G和microRNA的相互作用研究,林浩添還提出從分子機制上預防并發性白內障的發生。此方面的相關的研究成果已經在眼科學基礎研究的國際權威雜志IOVS上發表。
眼內寄生蟲之象
結膜吸吮線蟲是一種專門寄生于狗、牛等動物眼睛里的寄生蟲,也可寄生于人的眼中,于1910年首次被發現,由此蟲感染的疾病叫結膜吸吮線蟲病,是一種罕見的人畜共患疾病。由于該病多發生于亞洲地區,故稱為東方眼蟲病。人眼寄生了結膜吸吮線蟲后,輕者導致眼睛刺癢、有異物感,重者造成眼內感染,甚至失明。
雖然結膜吸吮線蟲病在我國已有數百例報道,但在正規醫學文獻中幾乎為空白。2010年惠州市一名女性患者因右眼有蟲子蠕動感到中山眼科中心就診,林浩添就該病例拍攝了相關圖片,在進行診治和隨訪的同時,記錄和保留了結膜吸吮線蟲病完整的臨床資料,包括臨床癥狀、治療過程、圖片等。這些詳細完整的臨床資料于今年一月份被英國著名醫學雜志《柳葉刀》認可并予以發表報道,引起了國內各大媒體的關注和報道,包括健康報、南方日報、廣州日報、中國醫學論壇報和人民網等近20家主流媒體。
然而,林浩添認為以往的工作僅僅是自己科研道路起步的一些嘗試,他目前最感興趣的是劉奕志教授帶領的先天性白內障的臨床研究項目,期待不久的將來有更大突破。
路在腳下,日夜兼程
當問到是臨床操作技能重要還是科研工作重要時,林浩添說,其實臨床和科研是可以相輔相成的。“我們可以做一個純粹的科學家,在實驗室里面做各種動物實驗;或者做一個醫生,只管治好病人的病;而如果我們做一位具備科研思維的臨床醫生,除了對病人負責,還從臨床工作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改進甚至創新出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方法,就把科研和臨床聯系起來了。”事實上,林浩添也是這樣踐行的。
生長于農村,林浩添自從選擇了醫學院,十多年來刻苦求學和從醫,雖然成長的過程是艱辛的,然而他始終堅持“要把每件事情做到最好”。都說“當醫生苦,當醫生累,當醫生沒覺睡”,林浩添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由于臨床工作中的繁瑣和日常事務的環繞,他只有利用晚上深夜清靜的時間看文獻、搞科研,經常工作到凌晨兩點鐘,幾乎沒有下班和放假的概念。林浩添愧疚地說,他甚至一周都抽不出半天時間陪自己年幼的女兒,即使在她生病非常需要父親關愛的時候他也在忙于工作。然而他也說,不是家庭不重要,休息沒必要,但是有些事情就是必須現在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