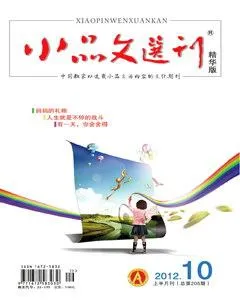莫須有的好學校
路文彬
暑期即將結束,女兒即將升入小學。親朋鄰里無不很是關心地詢問:要去哪所小學就讀?所謂幼升小、小升初這類在我看來極為尋常的事情,在國人尤其是北京人的眼里,似乎簡直就是天大的事情。所以,當我回答說就近入學,并不考慮擇校時,他們無不感到愕然。或是以為我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或是以為我沒把孩子的前途當回事。
其實,我也許是太把自己的孩子當回事了,故而才會做出這種不加選擇的選擇。在我看來,哪里有什么好學校一說,有的只是好老師罷了,而有了好老師,就必然會有好學生。但是,首當其沖的好老師可不是在學校,而是在家庭;如果父母做不了孩子的好老師,僅僅指望學校能有好老師,那可實在是異想天開的撞大運之舉。家庭教育永遠勝過學校教育,因此,一直讓我深感壓力的,從來都不是學校和老師,而只是為人父母的我們自己以及我們所組建的家庭關系。實際上,那些所謂的好學校最依賴的還不是好生源?好生源哪里來?還不是要從良好的家庭教育當中來。
現代學校之所以很難培養出天才,就是因為它所能夠提供的僅僅是平庸的共性教育,在老師們的眼里,所有的孩子全都是一樣的;而只有在父母的眼中,他們的孩子才會是獨一無二的。天才的個性來自于個性的家庭,但共性的學校則往往只知道去打壓此種個性。不然,愛因斯坦也就會是一個優秀的小學生了;這樣,愛因斯坦也就注定成為不了愛因斯坦了。梁啟超的子女們個個優秀,可這與其說要歸功于他們所就讀的學校,還毋如說應該感謝身為父親的梁啟超所能給予子女們充滿智慧的家庭教育。
從歷史上看,學校總是最讓天才們感到壓抑的地方。可耐人尋味的是,我們今天所謂的好學生在學校里卻個個如魚得水。聽父母的話,聽老師的話,是這代好學生的共同特點,但他們注定永遠不清楚自己是否有話要說。父母與學校合謀,早早地就扼殺了孩子的個性可能。當然,這些父母也不是不敢奢望自己的孩子可能成為天才,他們只不過是更加的世故和更加的功利而已,明白只有積極迎合學校的一切體制規定,才可能讓孩子順順當當地在社會這架巨大機器身上謀得一個牢靠的螺絲釘的位置。在他們看來,如果社會是一個大糞堆,那便只能將自己的孩子往蒼蠅那個形象上謀劃。這時,他們一點兒也不羨慕蜜蜂,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花叢的想象力。也正是基于這個原因,他們寧可讓自己的孩子成為蒼蠅而不是蜜蜂,畢竟,此時做蒼蠅要比做蜜蜂來得安全且又省力。想象力的貧瘠使得這些父母從來想象不到創造花叢的幸福,因而他們也就理解不了成為蜜蜂的幸福。我們的社會肯定是更需要蜜蜂而非蒼蠅,怎奈家庭和學校皆不鼓勵孩子去勇敢地成為蜜蜂。然而,要改變這樣的現狀,首先取決于的卻又只能是家庭教育的力量。
居里夫人不僅是個科學創造的天才,同樣也是一個家庭教育的天才,身為天才的她比誰都更懂得一個天才所需要的教育成長環境。所以,對于學校,她向來不夠放心,雖然那么繁忙,還是念念不忘著要和同行們組成一個團隊,在家里教育他們自己的孩子。后來,居里夫人的女兒同她一道摘得了1911年的諾貝爾化學獎。我相信,倘若沒有居里夫人與眾不同的家庭教育,無論多么著名的大學也不可能讓她的女兒取得這樣非凡的成就。不是嗎?
居里夫人是個好母親,也是個好老師,這中間沒有什么令人感到驚奇的成分,好父母就應當是好老師,好老師也應當是好父母。我們如今的所謂好老師之所以一概顯得不那么真實,原因就在于他們往往算不上是什么好父母。故此,當有人說好學校里好老師的概率畢竟會大些時,其實,他們是既不知道何謂好學校,也不知道何謂好老師。兼顧學習成績和素質培養,這并非就是好學校抑或好老師了。要知道,如果在這一過程中,學生沒有享受到愛與自由的情感,領會不了創造的激情和喜悅,而一味只是為了用生硬的知識和素質武裝自己以擊敗他人,那么,學校自然也就淪為了殘酷的角斗場,老師自然也都只配被稱為可惡的教唆犯了。如此墮落的教育,又奢談什么好學校和好老師呢?豈不無知得可笑?
選自“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