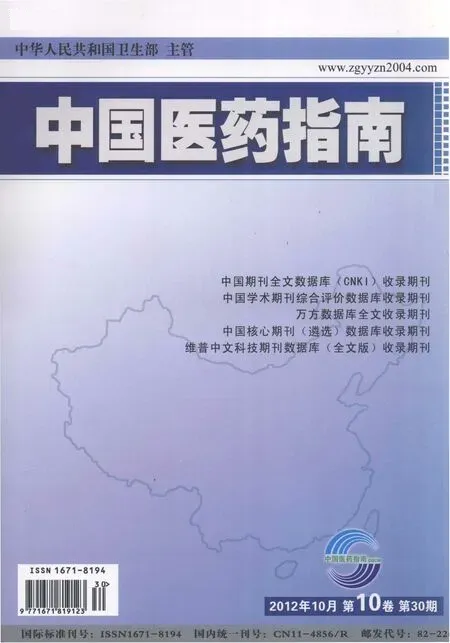海綿竇內側壁的顯微解剖學研究
曾 一 劉 月
(包頭市中心醫院,內蒙古 包頭 014000)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料
15例(30側)福爾馬林固定的經雙側頸總動脈灌注10%的紅色乳膠成人尸頭標本。大體解剖器械、神經外科常規和顯微手術器械、磨鉆(最高1萬轉/分)、手術頭架、手術顯微鏡(放大6~25倍)、柜式吸引器、游標卡尺(精確0.02mm)、兩腳規、量角器、手術無影燈、數碼照相機(1000萬像素)、SPSS13.0統計軟件。
1.2 方法
沿中腦上部水平去除整個大腦和間腦。采用從外向內的方法逐步暴露內側壁,逐步的除去上壁和外側壁以及穿行于海綿竇CS的顱神經,在進行切除的過程中同時對海綿竇的垂體、內側壁和頸內動脈等部位的結構進行密切的測量和觀察,然后沿著顱底的中線將顱底鋸開,觀察蝶竇外側壁與海綿竇的的關系。將所得的數據用SPSS13.0統計學軟件進行處理,測量值用均數±標準差(±s)(Min-Max)來表示。
2 結 果
3.1 內側壁硬膜結構
傳統觀念認為顱底的硬膜由內外兩層組成,硬膜在中顱窩三叉神經的外側部位分離為內外兩層。其中腦膜層即為內層,向上延伸形成了外側壁的淺層,繼續向前延伸,繞過前巖床韌帶延續為鞍隔和上壁的淺層。骨膜層即為外層,在海綿竇的外側壁下界即在上頜神經的上緣部位又分為兩層,其中一層向上形成一層上壁、鞍隔、外側壁的深層。 另一層 緊貼在蝶骨部位覆蓋鞍底和頸動脈溝。深層又和構成鞍隔的腦膜層從鞍隔游離緣向下包繞著垂體,形狀與垂體的外型相適應,因此又被稱之為“垂體袋”[1]。即為鞍隔硬腦膜的延伸,硬腦膜層形成CS內側壁上部。但隨著顯微解剖研究發展,研究者們發現CS內側壁的解剖絕非如此簡單。CS的膜性結構也因此成為目前研究和爭議的熱點。本研究顯微鏡下發現垂體與CS之間,僅為垂體包膜和一層很薄的疏松的結締組織,和Kehrlit及Dietemann的研究結果一致。本研究顯微鏡下發現垂體囊為垂體自身包膜,并非鞍隔或其他部位的硬腦膜延續,因此CS內側壁是由鞍旁骨膜和垂體包膜構成[2、3]。CS的內側壁為單層,垂體包膜部非常薄,這是垂體病變易侵犯CS的原因。研究還發現CS內側壁與垂體囊之間有一較窄的間隙,6.67%(2側)的垂體囊則呈小舌狀伸入頸內動脈,20%(6側)的垂體囊與頸內動脈緊密接觸。
3.2 內側壁
CS內側壁前界從蝶骨體和視柱的聯合向下直到達圓孔的上界;后界是從后床突向下延伸到巖斜裂的上端;上界從蝶骨體與視柱的連合水平向后沿著鞍隔延伸到后床突;下界是從圓孔的上界向后延伸到巖斜裂的上端。它是由垂體包膜與鞍旁骨膜與構成的。垂體包膜與頸內動脈間借助3~4條的纖維組織進行連接。骨膜部是由蝶骨體骨膜與頸動脈溝兩者構成的。蝶骨體骨膜分隔海綿竇和蝶竇內的靜脈叢及頸內動脈。覆蓋在蝶骨體上頸動脈溝的骨膜構成了蝶骨體骨膜,向后延伸直到巖斜裂。見表2。

表2 CS內側壁各界線的邊長 (Min-Max)(mm)
3.3 頸內動脈與內側壁和垂體的關系
垂體呈橢圓形,她的位置為位于蝶骨體之上的垂體窩內,借助于垂體柄與下丘腦相連,前后徑的范圍在8.02~11.78mm(10.49 mm±1.10mm),垂直徑的范圍在4.68~9.06mm(6.59 mm±1.00mm),左右徑為12.54~18.40mm(14.90 mm±1.51mm)。以垂體超越頸內動脈的內側作為側突的標準,在本研究中,有2側垂體向外突出,占6.67%。頸內動脈CS段(cavernous segment of the internal carotid artery,CSICA)由破裂孔進入CS,穿CS上壁出CS,可將其分為鞍旁部和斜坡旁部,其中鞍旁部可進一步分為前升段、前曲段、水平段和后曲段;斜坡旁部為后升段。頸內動脈在水平段可向下或外側彎曲,有46.67%(14側)的ICA與垂體外側壁直接相貼,53.33%(16側)兩者之間有間隙存在,測得兩者的間距為(2.67±1.03)mm。
3.5 內側壁與蝶竇外側壁的關系
CS內側壁蝶骨部與蝶竇外側壁相鄰。蝶竇外側壁較薄,前部鄰接視神經管和眶內側壁后部,頸內動脈CS段與蝶竇外側壁的中后部上2/3的后部與密切相鄰;上頜神經與蝶竇外側壁中后部的下1/3的后部緊密相鄰。血管和神經附著在蝶竇側壁的顱腔面,在骨壁上形成壓跡,并突入到蝶竇腔內形成隆起,三者呈上、中、下排列。視神經和頸內動脈在蝶竇外側壁上形成的隆突主要分為三型:①隆突型,突入竇腔內的部分不到周徑的50%;②管型,頸內動脈和視神經的50%以上的周徑突入到竇腔;③無隆起型,僅貼近蝶竇壁外。本研究實驗僅是按照有無隆起來測量,測得視神經和頸內動脈的隆起率分別為53.33%和83.33%。蝶竇氣化越完全,隆起便越明顯,隆起處骨壁亦就越薄,是蝶竇和鞍區手術嚴重并發癥的解剖因素[4]。
4 討 論
在對CS內側壁硬膜結構的研究中,發現垂體與CS之間,僅為垂體包膜和一層很薄的疏松的結締組織。垂體囊為垂體自身包膜,并非鞍隔或其他部位的硬腦膜延續[5],這與張慶榮[6]的觀點相一致。Chi和Lee等觀察56例胎齡4周至40周的垂體標本,認為垂體包膜是胚胎階段由Rathke囊周圍間質細胞分化而來,包裹腺垂體及稍后發育的神經垂體。因此CS內側壁是由鞍旁骨膜和垂體包膜構成。垂體包膜和一層很薄的疏松的結締組織構成垂體與CS之間唯一屏障,而非鞍隔或其他部位的硬腦膜延續。垂體腫瘤易于侵犯CS,可能與CS內側壁這一解剖學特點有密切關系。垂體瘤的CS侵襲性生長與CS的內側壁的解剖特點密切相關,并非全部因為腫瘤具有侵襲性所致。本實驗研究發現6.67%(2側)的垂體囊呈小舌狀伸入頸內動脈,20%(6側)的垂體囊與頸內動脈緊密接觸。因此只有CS侵襲達到一定的程度,腫瘤突破垂體囊的包裹突人CS內才能說明垂體瘤具有侵襲性[7]。蝶竇的氣化與頸內動脈和視神經在蝶竇的外側壁的隆起呈正相關關系,蝶竇氣化與隆起處的骨壁的厚度與呈負相關關系[8]。因此,在進行經蝶手術時,如果頸內動脈和視神經和的隆起率越高,隆突越明顯,形成隆突的骨壁就越薄,蝶竇的氣化越好,越容易進入蝶竇暴露鞍底,這種情況是是蝶竇和鞍區手術嚴重并發癥的解剖因素。熟悉和掌握蝶竇外側壁與頸內動脈、CS、視神經等解剖毗鄰關系,對經鼻蝶入路鞍區手術有很重要的意義。
5 結 論
①垂體與CS之間,僅為垂體包膜和一層很薄的疏松的結締組織。垂體囊為垂體自身包膜,并非鞍隔或其他部位的硬腦膜延續,CS內側壁是由鞍旁骨膜和垂體包膜構成。②垂體腫瘤易于侵犯CS,可能與CS內側壁這一解剖學特點有密切關系。③熟悉和掌握蝶竇外側壁與頸內動脈、CS、視神經等解剖毗鄰關系,對經鼻蝶入路鞍區手術有很重要的意義。
[1]朱廣廷,馮燕,于春江,等.垂體窩及其毗鄰結構手術相關顯微解剖學研究[J].中華微侵襲神經外科雜志,2002,7(3):157-161.
[2]Yasuda A,Campero A,Martins C.et al.The medial wall of the cavernous sinus: microsurgical anatomy [J]. Neurosurgery, 2004,55(1);179-190.
[3]Kim JM, Romano A, Sanan A, et al. Microsurgical anatomic features and nomenclature of the paraclinoid region [J].Neurosur gery,2000,46(3):670-682.
[4]羅俊生,席煥久,于春江,等.擴大經蝶手術人路相關的顯微解剖學研究[J].中華神經外科雜志,2005,21(9):553-556.
[5]Yokoyama Shunichi M.D.,Hirano Hirofumi M.D.,et al.Are nonfunctioning pituitary adenomas Extending into the caver- nous sinus aggressive and/or invasive?[J]. Neurosurgery,2001,49(4):857-863.
[6]張慶榮,史繼新,張紹祥.海綿竇斷層解剖研究及其臨床意義[J].中華神經醫學雜志,2006,5(3):258-261.
[7]胡佳,曲元明.海綿竇內側壁的解剖特點及其對于垂體腺瘤侵襲性診斷的意義[J].臨床神經外科雜志,2007,4(3):140-141.
[8]孫敬武,汪銀鳳,陳曉紅,等.經鼻腔內窺鏡蝶竇鞍區手術解剖及其臨床應用[J].中華臨床解剖學雜志,2000,18(3):199-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