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人的因素貫穿始終的書史研究
○姚伯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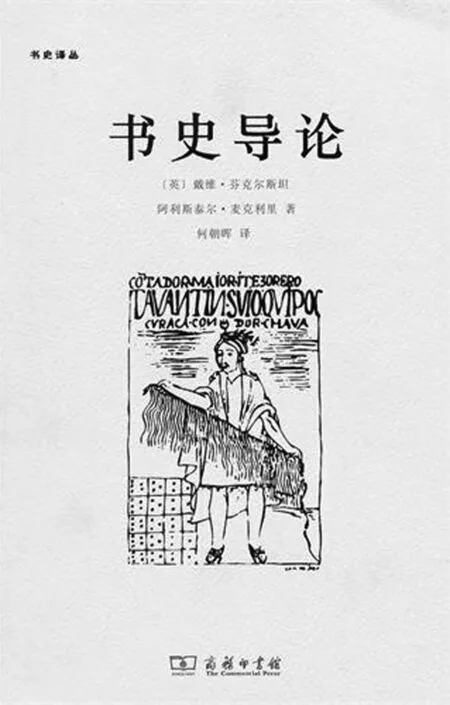
《書史導論》,(英)戴維·芬克爾斯坦、阿里斯泰爾·麥克利里著,何朝暉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5月版,36.00元。
《書史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Book History)是一部關于圖書歷史的著作。兩位作者,一位是戴維·芬克爾斯坦(David Finkelstein),為英國愛丁堡瑪格麗特女王大學社會科學、媒體與傳播學院的傳媒與印刷文化教授,一位是阿里斯泰爾·麥克利里(Alistair McCleery),為英國愛丁堡納皮爾大學的文學與文化教授、蘇格蘭書籍中心主任、蘇格蘭印刷與出版史資料中心主任。中文翻譯者何朝暉,是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博士后,現(xiàn)為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古典文獻研究所教授。著譯者都是書史學界的專家學者。
西方書史學對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示是,他們在書史研究中全面系統(tǒng)地引入了人的因素。就以這部《書史導論》為例,我們不妨看一下這本書的目錄。
第一章 書史理論
第二章 從口頭到書面
第三章 印刷的誕生
第四章 作者、作者身份與權(quán)威
第五章 印刷商、書商、出版商、代理
第六章 讀者與閱讀
第七章 書籍的未來
這樣一部比較典型地反映西方書史學架構(gòu)體系的普及性讀物,僅僅七章的篇幅中,關于人的論述就占了整整三章。從作者、出版商到讀者,人的因素幾乎貫穿了對書籍生產(chǎn)和傳播過程研究的始終。這本書告訴我們,西方書史研究中對“作者”身份的關注,來自于人文主義的興起,它有助于對圖書的認知和歸類。為什么要研究印刷商、書商、出版商、代理人呢?書中的解釋是“對珍稀罕見、令人著迷、不同尋常的圖書制作過程背后的歷史和人物的了解,常常與評估書籍的物質(zhì)價值密不可分”。至于讀者和閱讀,這是西方書史最近幾十年才開始重視起來的。作為圖書的受眾,讀者對圖書的選擇、閱讀的方法、閱讀的能力,都成了書史學不可忽視的研究內(nèi)容。作者清醒地認識到:“書籍史既研究個體的閱讀情況,也利用范圍更廣的統(tǒng)計資料,以及書籍,來創(chuàng)造閱讀的歷史。”該書的最后一句話,更是精辟地指出了書史學的社會意義:“研究書史,就是研究我們的人性,研究支撐整個社會的知識搜集與傳播的社會交流過程。”基于這樣一種理念構(gòu)建起來的書史學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在我們看來真是別開生面。
中國書史的敘述,似乎已經(jīng)有一個固定的套路,就是從甲骨文開始,繼之以青銅器銘文、竹木簡冊、帛書帛畫,然后是造紙術的發(fā)明。接下來講紙本書,論制作方法,有手工抄寫、雕版印刷、活字印刷、鉛印、石印、膠印等;論出版時代,有宋本、元本、明本、清本等等;論裝幀形式,有卷軸裝、經(jīng)折裝、蝴蝶裝、包背裝、線裝、精裝、平裝等。這種講法看似天經(jīng)地義,其實說的只是中國書籍制度史,注重的只是圖書的物質(zhì)形式和生產(chǎn)技術,而缺少對許多相關重要因素的關注,例如圖書的編纂、圖書的傳播、圖書的使用,對圖書的文化意義和圖書背后的社會史的研究更無所措意。反映到教學上,我們傳授給學生的只是知識,而不是文化;學生只需要接受,而不需要思考。
對比西方的書史學,我們意識到,中國書史不能僅僅講成書籍制度史,它應該有更豐富的內(nèi)容和更深刻的內(nèi)涵,更應該是中國圖書文化史。圖書與社會、思想、文化、政治、經(jīng)濟等周圍環(huán)境的關系,圖書所產(chǎn)生的社會影響,以及這種社會影響在圖書中的體現(xiàn),都應該是中國書史研究的內(nèi)容。
一旦我們的眼界放寬,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中國書史有太多的內(nèi)容需要我們?nèi)パ芯浚那熬笆侨绱藦V闊,它的意義是如此重大。在全球的視野下,我們會更清楚地知道中國書史應該研究什么,怎樣研究,為什么研究。在全球的視野下,中國書史的研究者將更加注意與國際同行的交流與合作,更加關注外部世界的變化和進步,同時將中國燦爛悠久的書文化更多、更普遍地傳播介紹到世界上。
其實,長期以來,歐美書史學界的研究視野基本上也是局限在西方世界的認識范圍內(nèi),“在西方學者建立的書史研究框架里,幾乎沒有西方之外的各種書文化的位置。”(《書史導論·譯者前言》)對于中國書的歷史,他們知道得很少,也很少關注,只是在不能不提的時候當作一個幾乎與世隔絕的部分偶爾來說上幾句。1925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美國人卡特著的《中國印刷術的發(fā)明及其西傳》(T.F.Cater’s The InterventionofPrintingin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有商務印書館1925年版中譯本)稍稍改變了西方書史學界的一些錯誤認識。英國人李約瑟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由錢存訓先生執(zhí)筆的《紙和印刷》(Paper and printing,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有科學出版社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合作出版的中譯本)一書,才第一次為西方世界系統(tǒng)地講述了中國書的演進過程,做了一次中國書史的普及宣傳。
但翻閱著《書史導論》這部2005年才第一次在美國出版的新作,我發(fā)現(xiàn)即使在今天,西方學者對于中國書史常識的無知,也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是非常嚴重的。例如原書作者在專門為該書中文版所做的序中說,“到公元150年,紙張的使用和制造已經(jīng)傳到土耳其斯坦”,不知依據(jù)為何?說到墨的起源,竟然是“最初中國人用它來拓印刻在石頭上的文字,后加以完善而成”。誰都知道拓印是造紙術發(fā)明以后的事情,而墨在造紙術發(fā)明之前很久就在使用了,否則,幾千年前的竹木簡上的文字是用什么寫上去的呢?
此書的譯者何朝暉教授對于此書在中國內(nèi)容上的欠缺是有感受的。他在該書的《譯者前言》中非常中肯地指出:“一個真正完備的書史理論體系,應該能夠反映世界上各種優(yōu)秀的書文化成果。中國、印度、埃及、伊斯蘭世界、印第安文明中的瑪雅文化都有著悠久燦爛的書文化,但在這本以《書史導論》為題的書中卻鮮有論列,這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何教授進一步指出:“中國書史能夠為世界范圍書史學科理論、方法的構(gòu)建提供許多新的資源。任何不能反映中國書史豐富而有典型意義的歷史實踐的書史理論體系都是不完整的。作為一個有著悠久燦爛圖書歷史的書文化大國,中國理應在國際書史學界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取得應有的話語權(quán),并在借鑒西方書史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建立符合自身書文化特點的學說和理論體系。”
事實上,該書的中譯本因為有了何朝暉這篇高屋建瓴的《譯者前言》,在認識高度上較之原書已經(jīng)有了一個升華。原書無圖,何教授主動為中譯本選配了近50幅生動貼切的插圖,并一一予以簡明的圖注,更使該書面貌煥然一新,增加了學術性和可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