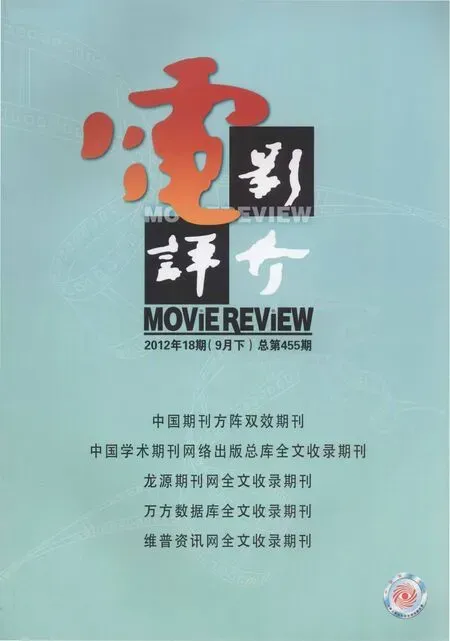論謝晉“文革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
性別意識形態關系到文本對性別的言說立場和想象方式,這里的性別是社會意義上的而非生理意義上的。生理性別是先天的,社會性別則是后天的,是“一種社會現象,它是一種文化建構”[1]。不同的文化建構不同的性別角色,每一時代都有特定的性別敘述方式與建構模式。謝晉的“文革三部曲”《天云山傳奇》、《牧馬人》、《芙蓉鎮》在性別敘事上具備典型性,三部作品的女性主人公在形象塑造上呈現出明顯的類型化特征。性別意識形態對文本的審視“不僅關心文本的內容:它講述了怎樣的故事,而且關心其形式:如何講述”[2]。通過審視文本的敘事立場,即敘事者在角色塑造背后秉持的性別立場,可以發現,謝晉的“文革”敘事不僅飽含著政治意味,同時折射出男權文化的色彩。
一、溫良賢淑的正面女性形象:地母式的道德楷模
在“文革三部曲”中,三位正面女性形象具有明顯的共性,不論是《天云山傳奇》中的馮晴嵐,還是《牧馬人》中的李秀芝、《芙蓉鎮》中的胡玉音,她們無一例外的溫柔賢淑,是勤勞善良善于持家的好妻子。
這種女性形象塑造方式可謂源遠流長,賢淑的妻子成為女性必須擔當的首要角色,女性的天職是“相夫教子”,對女性的價值判斷是以他們對家庭、對丈夫子女的付出甚至犧牲的多少為標準的。在這種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建構的經典敘事中,女性自我是缺席的,她是妻子,是母親,唯獨不是她自己。
作品中的這些女性還充當男性主人公的“避難所”,為政治劫難中身心俱疲的他提供情感的慰藉和溫情的庇護。她們是充滿母性慈愛的妻子,也就是說這類女性是地母式的。地母是中國原始宗教中的大地女神,也就是古希臘神話中的蓋婭女神,她象征大地的恩惠,親切慈愛而勤勞,孕育著萬物生靈。愛、付出、包容和犧牲是地母式女性共有的特質。
在“反右派”政治運動開始之后,接連遭遇政治打擊的“反動”分子羅群失魂落魄一貧如洗,正當他失去生活的信念的時候,馮晴嵐用母親般寬厚溫暖的懷抱接納了他。李秀芝對于“雙重棄兒”許靈均來說同樣是地母式的。幾近絕望的許靈均在堅強質樸的妻子李秀芝這里找到了身為人的溫暖,因為她認定自己“是個好人”。
巧妙的是,這里的地母式的女性形象又不同于通俗的家庭倫理劇中的賢妻良母。因為敘事年代的特殊,這里的女性被賦予了政治或者說歷史的前瞻性。她們總是以樸實的話語作出歷史必將走向光明的預言。馮晴嵐認定了羅群不是什么反動分子,他一定能夠等到撥開云霧見天日的那一天。目不識丁的李秀芝更是毫不懷疑丈夫會得到公正的對待,因為他是一個好人,一個并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好人。這種對社會前進方向的前瞻性以及對歷史走向的堅定信念是這些女性主人公和“鄉親們”共有的。他們是身處社會底層的力量,質樸善良,同時又被塑造成明智的能夠預見未來的,所以他們近乎本能地張開臂膀,為落難的男性主人公提供溫暖的庇護。
但歸根結蒂,這些女性充當的只是歷史的旁觀者、見證者,而不是“弄潮兒”。也就是說這里的女性主人公是一種非主體式的存在,她仍然是處于整個社會的政治結構最底層的邊緣人。這種敘述話語的背后傳遞的依然是以男性為主體的傳統性別觀念,女性只是客體,她的價值要通過男性主人公來體現。
二、命運多舛的反面女性形象:價值缺失的政治祭品
在謝晉的“文革”敘事中,還存在著這樣一類女性形象,在那段特殊的政治歲月里,她們或是推波助瀾或是興風作浪,是反面人物。但同時她們又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在政治的旋渦中逐漸迷失了自我,事業家庭都走向失敗,成為價值缺失的政治祭品。《芙蓉鎮》中的李國香就是其中的代表。
李國香是一個政治狂熱分子,熱衷于給人劃成分、戴帽子,動輒就開群眾大會搞批斗。她不僅熱衷于政治,充當歷次政治運動的積極分子,她也曾是政治運動的對象,被“革命小將”們批斗謾罵。更加耐人尋味的是,李國香的政治狂熱還夾雜著明顯的性別色彩。那就是一個一把年紀仍孤身一人的女性希望得到男性的價值肯定的愿望落空之后的報復,或者說出于對頗受男人喜歡的“芙蓉姐”胡玉音的嫉妒,這就使得李國香的政治行為變得“目的不純”,因而更值得批判。
除了在政治上走向錯誤的道路之外,李國香還被塑造成一個道德墮落的形象。得不到任何男性青睞的她和芙蓉鎮上的潑皮破落戶政治投機分子王秋赦有了不正當的關系。這就與胡玉音和秦書田之間的正當戀愛有了道德上的差異。這種敘述方式在“文革”敘事中并不稀奇,政治上錯誤與道德上墮落或邪惡往往是捆綁在一起的。
這樣一個女性充當的不過是政治運動的祭品,在波瀾起伏的歲月里孤獨老去,空留罵名。在作品呈現的人物圖譜中,不論是人生理想還是個人情感、家庭,她的一生是價值缺失的,還遠不如一個囿于家庭的主婦。這是否是敘事者對不安于家庭試圖與男性分庭抗禮的女性的一種象征性懲戒?
三、反思與詰問:失聲的女性群像
在謝晉的“文革三部曲”中,不論是正面的道德楷模式的賢妻良母,還是反面的充當祭品的政治女性,她們都是扁平的、次要的、非主體式的存在。
一方面,正面的女性形象承載著超乎性別以外的龐大的意義。政治災難造成的巨大鴻溝在這里被高尚的道德和豐滿的情感所填塞。地母式的女性與質樸的鄉民一起,為經受苦難的男性主人公架起了一座橋梁,讓他從艱難的此岸安全抵達充滿公平光明正義的彼岸,繼續創造歷史。如果說“文革”歲月是一場慘烈的戰斗,那么這戰斗的“敵方”在文本中的面目是模糊的,他甚至是缺席的,化作張貼在墻壁上的幾張大字報、游走在街頭的幾個“紅小將”,或是透過無知的孩子對著鏡頭喊幾句“老右”。
另一方面,試圖掌控自我命運的反面女性同樣會遭遇重重困境,不論是政治生涯還是情感與家庭,她們最終無一例外的無功而返。
這就是作品所營造的女性生存的圖景——女性要么安于家庭,做一個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婦,勤儉持家、溫良賢淑,在他需要的時候為他獻出溫暖的懷抱,給予他情感的慰藉與精神的支持,扶持他度過難關,做一個地母式的妻子;要么投身政治的洪流,在與男性分庭抗禮一爭高下的斗爭中跌跌撞撞頭破血流。
正是這種敘事所營造的進退維谷的女性生存困境折射出了敘事者所秉持的陳腐的性別觀念:男性是主體,是價值和意義的創造者。女性則是被動的,是客體,她的價值和意義要透過男性主體去體現。這恰恰印證了西蒙?波伏娃所說的“一個女人之所以是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3]。女性在故事中是被講述的,也是失聲的,被剝奪了話語權的。這失聲的女性群像佇立在藝術的長河里,期待著自我救贖的時刻早日到來。
[1]吳菁.消費時代的性別想象[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158.
[2]戴錦華.電影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190.
[3][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桑竹影,等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