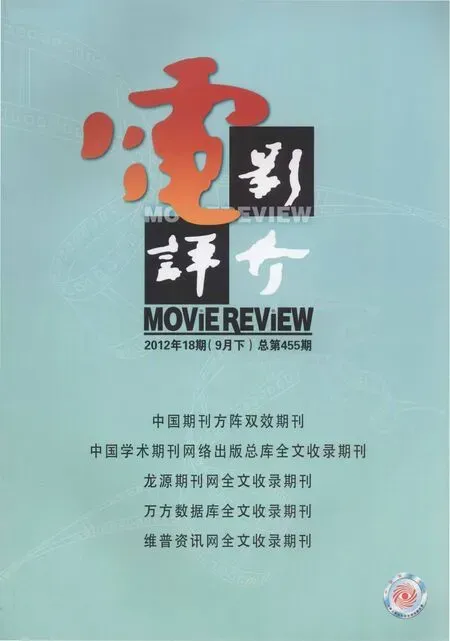《一次別離》:新現實主義電影的承襲與伊朗本土化詮釋
新現實主義在電影史范疇又稱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其在二戰后迅速發展,并掀起一波氣勢龐大、長達六年的電影新潮。新現實主義對世界電影的影響非常深遠,它與好萊塢電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新現實主義強調樸實氣質,而不是光鮮魅力;強調表現普通人,而不是達官貴人;強調紀實美學,而不是技術主義——這種傾向在伊朗導演阿斯哈?法哈蒂的影片《一次別離》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小成本伊朗電影《一次別離》自2011年在第61屆柏林國際電影節輕易斬獲金熊獎后,勢如破竹般橫掃各大電影節,共拿下含奧斯卡、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等十多個全球電影重要獎項,這在當今美國好萊塢模式大片對全球市場的覆蓋情況下是非常不易的。可以說,《一次別離》既喚起了人們對于新現實主義的回憶,也是導演法哈蒂嘗試融合伊朗本土化文化、戲劇化沖突與新現實主義而產生的一部既叫好又叫座的佳作。
一、“還我普通人”[1]與“把攝像機扛到大街上”[2]——《一次別離》對新現實主義題材的承襲與表現形式的借鑒
(一)題材與劇本立意訴求
“還我普通人”是新現實主義著名編劇柴伐蒂尼提出的,其主張題材表現普通民眾。新現實主義代表作品《偷自行車的人》、《溫別爾托?D》、《羅馬,不設防的城市》均是著力表現普通人命運的題材。與新現實主義的先驅一樣,《一次別離》的導演阿斯哈?法哈蒂也將鏡頭聚焦于伊朗人的日常生活,直面伊朗社會現狀,關注現實生活中處于道德、法律、宗教拉力中的伊朗普通百姓。影片的切入點極小——從納德與西敏的分居為切入,但這個小切入點卻深刻地扎進了伊朗社會的肌理脈絡之中:一次意外事件后各種矛盾接踵產生,逐步深入最終走向一個不可逆轉的別離結局。劇中兩個普通的伊朗家庭在法律與道德面前的矛盾展現了伊朗錯綜復雜的社會現實,也揭示了一次分離:伊朗社會凝聚力的分離。
導演用旁觀者視角貼近而不動聲色地記錄事件,同時洞悉人與人之間復雜微妙的關系,把大量日常生活的要素和情境升華為一個跌宕起伏的故事,對人性的刻畫極其深刻,在原生態的生活展現過程中反映了伊朗人真實而又頗為無奈的生活,質樸真誠地強調了新現實主義人文精神的延續。
(二)表現形式
在拍攝手法上,新現實主義還提倡“把攝像機扛到大街上”的創作口號——對拍攝手法與表現手段方面提出了一定的紀實要求。新現實主義很少布景拍攝,強調手持攝像;在光線處理上,傾向于采用自然光。《一次別離》也繼承了新現實主義這種典型的攝制方式,全片長達兩小時,多是利用自然光線手持跟拍,如一部不加修飾的記錄片;大量的主觀鏡頭干凈而克制地將觀眾帶入情境之中。無論室內室外都狹小逼仄,密閉的空間內人們心事重重;走出室外,映入眼簾的是伊朗城市的車水馬龍,又讓人覺得心緒紛亂。鏡頭之下,伊朗的風土民情雖然遙遠而陌生,但觀眾對這些城市景象卻非常熟悉,因為就如每天環繞在自己身旁的生活一隅。
在藝術表現手段上,《一次別離》也絲毫不給觀眾有出戲疏離的機會。注重運用長鏡頭,以連貫的拍攝獲取真實效果一直是新現實主義紀實美學的一個重要特征。“新現實主義電影采用的長鏡頭,是用連續攝影法拍攝的景深鏡頭,強調的是鏡頭內部的空間調度和場面調度,從而在一個統一的時空中相對完整的展現動作和事件。這樣,長鏡頭對現實的表現就具有空間的完整性、時間的連續性和影像的客觀性。”[3]而“長鏡頭紀實美學”來源于安德烈?巴贊[4],其運用的意義首先在于真實感,不作分切的一次性連續拍攝,使銀幕畫面人物活動的影像完整性與被表現的客觀現實達到高度統一。例如,《偷自行車的人》中大部分段落都是用長鏡頭描述的,如失業者圍著政府職員求職, 里西到典當鋪贖回自行車.里西和兒子在舊貨市場尋找被偷的自行車; 里西偷別人的自行車時被發現等,這些段落都沒有鏡頭的切換, 保持了人物行動和事件的連續和相對完整。另外, 長鏡頭保留了現實本身的多義性。蒙太奇強制觀眾跟著導演的意圖去被動地理解影片, 長鏡頭卻讓觀眾直接參與銀幕中的現實,由觀眾自己去作判斷解釋。
《一次別離》中,長鏡頭使用突出表現在影片的開頭與結尾:電影開篇記錄式的拍攝手法,近四分鐘一鏡到底、甚至帶有些輕微晃動的長鏡頭,直截了當地讓西敏和納德這對夫妻對簿公堂,上演了一出你來我往的家庭紛爭,有著很強的感染力。觀眾被置于法官的視野位置去審視這場糾紛的是與非。難以判斷誰是誰非的法官,最后令其簽字回家和解,不予離婚,畫面中只留下兩張空椅。此時,觀眾已被這個連續的長鏡頭帶入故事情境之中,旋即被卷入環環相扣的劇情里。而影片以一個長鏡頭開始,也是以一個長鏡頭結尾,場景仍舊是法院,不同的是二人已在等待離婚后女兒的抉擇。一氣呵成的鏡頭冷靜客觀地對著這個長廊,人來人往中,納德和西敏相向而坐,二人中間以一扇破裂的玻璃門作為分界,兩人各占據畫面的一角,茫然而又無言以對,等待女兒的決定,等著著別離。玻璃上的裂痕仿佛就是納德和西敏這個家庭之間,也是整個伊朗社會之間的裂痕與隔閡。這時,長鏡頭帶來的強烈沖擊力審問觀眾,如果是你我,當如何選擇。這兩處首尾呼應的長鏡頭耐人尋味,猶如“神來之筆”:相同的地點、不同的命運走向,掃視著劇中主人公納德與西敏對于生活的無奈,也調動了觀眾融入劇情的參與感,同時也完美地展現了導演對于新現實主義電影紀實美學的推崇。
而開放式結局也是新現實主義電影藝術表現手段的一個不可磨滅的特征。柴伐蒂尼提出“不給觀眾提供解決問題的答案” [5]——對比《偷自行車的人》影片結尾,里西與兒子一起走,沒有臺詞,沒有音樂,僅有周圍的環境聲的開放式結局,《一次別離》則通篇都只有真實的環境音,僅在影片結尾突然插入了兩段鋼琴聲,緩慢而沉重的和弦一鳴驚人。這悲愴傷感的音樂——也是本片唯一的配樂,猶如沉默中情感的噴發,讓觀眾陷入一種沉重的、難以言表的延續性思考,且直至片尾音樂結束,觀眾也沒有等到女兒特梅的最終選擇。音樂聲中,極富深意的長鏡頭已完成了影片開放式結局,這種戛然而止的開放式結局處理方式甚至比《偷自行車的人》顯得更甚一籌。
二、融合伊朗宗教文化和經典的戲劇化策略進行敘事表達——《一次別離》是對新現實主義的伊朗本土化詮釋
就題材、主題、人物形象塑造、人文精神、藝術手法與表現手段運用上而言,《一次別離》無疑是新現實主義電影的一個完美樣本。但羅伯托?羅西里尼[6]說過:“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新現實主義。”[7]伊朗作為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當局嚴苛的審查制度使電影題材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宗教文化與政治氛圍一直縈繞著伊朗電影,也因此伊朗電影在國際影壇上存在著一種有別于西方電影的神秘性與特殊性。
當伊朗導演阿巴斯?基阿羅斯塔米執導的影片《櫻桃的滋味》1997年在戛納摘下金棕櫚獎,電影界才發現新現實主義在伊朗仍興盛著。事實上,伊朗三大導演除了阿巴斯之外,莫森?瑪克瑪爾巴夫、賈法?帕納西的電影風格均帶有深刻的新現實主義美學印記。幾代伊朗導演都將新現實主義美學之根植于伊朗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表現出“對本土現實、文化和本土體驗的殷切關懷”。[8]但是伊朗過去的新現實主義電影非戲劇化的敘事雖含有詩意哲學,但劇情張力不強,電影表達只觸及了伊朗社會生活的現實表面,主題不夠深刻。
“文化離開誠實而強有力的故事便無從發展。”[9]作為第三代伊朗導演的阿斯哈?法哈蒂深深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恪守新現實主義的精神內核原則外,對伊朗本土化具有現實意義的多重問題(伊朗人民的信仰、階級、感情、法律、倫理、教育)進行了思考,交織了經典的戲劇化沖突敘事策略:嚴格按照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的邏輯線索來結構故事,將矛盾沖突與戲劇懸念埋入敘事,追求情節結構上的環環相扣。
經典的戲劇化沖突敘事策略還是《別離》好看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影片的敘事主線基本上是通過懸念來牽引的。首先“納德和西敏的婚姻最終會是什么結局,離婚還是和好?”是貫穿影片始終的一個懸念。而結尾又留下了“女兒會選擇誰?”的懸念待人深思。另外一條敘事線——納德與女傭瑞茨的糾葛段落中,也是采用了制造懸念的敘事手法,“誰偷了錢?他聽到沒有?她有沒有撒謊?他們會不會和解?他們會不會拿錢?”一個個懸念在引導著敘事迂回地深入,直至結局。如果說從原本的故事角度來看,《別離》的故事并不討好大多數觀眾,它只講述了一個簡單的家庭和社會悲劇,那么是導演法哈蒂通過嫻熟的經典敘事手法使內容具有了觀賞性。
“沖突實質上體現了電影中人物的想法、行動與社會的一種對抗性關系。”[10]縱觀全劇,多重矛盾關系或隱或顯,或大或小,構成了形態各異的沖突:社會階層之間的沖突——納德一家所代表的是中產階層,有房有車有穩定的工作;而瑞茨代表的是伊朗下層的勞動人民,家庭負債,懷孕仍要外出工作,丈夫失業。瑞茨的意外流產,使兩個家庭彼此間產生強烈的對立,階層立場不同又造成和解的困難。隨之劇情承載了第二個沖突:伊朗宗教與人性的矛盾,影片在很多情節涉及到:如瑞茨在照顧納德父親時所猶豫的宗教禁忌、家庭教師在對著《古蘭經》作偽證后又復而到法院改口供的前后變化以及最后雙方和解過程中瑞茨對教義會懲戒女兒的疑慮……暗含的強烈沖突便是宗教與人性的矛盾,在伊朗這個國度,現代化過程中宗教信仰對于人的束縛與人對束縛的掙扎都是不可回避的事實。沖突使《一次別離》的敘事形成特有的張力,它不僅激發了觀眾的觀賞興致,還在沖突中彰顯了劇中人物的個性,并生發出更富意味的敘事隱喻。
三、結語
新現實主義電影的外延在不斷變化中,但其核心仍舊是對普通民眾的關懷與紀實的本質。《一次別離》緊貼時代的脈搏,既承襲了新現實主義典型精神內核,又實現了伊朗電影對新現實主義的本土化美學延展與詮釋——將戲劇化的沖突敘事策略運用于伊朗本土主題思考進行電影敘事表達。《一次別離》走出了一條獨特的民族化電影道路,也完成了一次電影藝術的揚棄過程,這種探索值得中國現代電影人加以研究與借鑒。
[1][2]周星.影視藝術史[M].中國計劃出版社 2003(132)
[3]肖體元.試論新現實主義電影[J].重慶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1(4)
[4]安德烈?巴贊(1919--1958):法國理論家和批評家,真實美學的倡導者,法國新浪潮電影領袖.巴贊簡介轉引自(英)彼得?馬修斯,李時,譯.探究現實——安德烈?巴贊在昨天和今天[J].世界電影 2006(6)
[5]轉引自倪祥保.試論中國新現實主義電影[J].中國高教影學會教育委員會年會2009
[6]羅伯托?羅西里尼 (1906-1977),意大利導演,代表作《羅馬,不設防的城市》.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419350.htm
[7](英)羅伊? 阿米斯,沈善,譯.二十年后回顧意大利新現實主義[J].世界電影1980.4(原文摘譯自現實主義的型式: 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研究一書(1971年倫敦出版)第四章一種風格的剖析)
[8]陸紹陽.從簡單出發——與天堂的孩子有關[J].當代電影,2001(2).
[9](美)羅伯特?麥基.故事[M].周鐵東,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1年(16)
[10]葛娟.《海角七號》戲劇化敘事風格論析.電影文學,2010(6)
——以《山河故人》為例